在谈论受害者的创伤心理之前,我想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反应。
普通人是有动机回避他人的创伤的。
因为一旦你想要了解创伤,你就无可避免要面对人类的脆弱和劣根性,你见证他人的痛苦时也许也会痛苦。这是恶本来的一个衍生目的,恶就是使人厌恶、反感、回避的,我们顺应这种本能,就能让恶的目的得逞。
我们只需要什么都不做,就足以帮到加害者。
而反过来,要帮助受害者,
我们不但要看到受害者的经历,还要共情其痛苦,还要不忘记,要行动起来支援
,这使我们也加入到直面恶、挑战恶的队伍中,这个过程不愉快、不痛快,有太多使人反感和焦虑的东西。我们会发现,当一个置身事外的人至少从情绪和精神压力上无疑是好受多了的。
目击恶的每个人,包括受害者,其实都急于摆脱创伤,急于遗忘,急于得到结果,哪怕是一度曾提供帮助的人们,都带着这样强烈且不自觉的动机,我们非常希望一切赶快结束,赶快恢复日常生活,赶快让一切好像没发生一样。这也是受害者常常在无声中落败的原因,她们在被遗忘中势单力薄。

(取材自《热泪伤痕》)
加害者还会给普通人理由,让我们心安理得的置身事外。他们指责受害者说谎,讲出截然不同的故事,搬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当加害者权力越大,也就越有能力定义真相,越有能力在一开始就准备好对自己有利的局面。
普通人有充分的动机退出不明朗的局面:因为各说各的,没人知道真相,何况,别人的真相是遥远的与我无关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个人的形象如何。我如果选错了队支持错了人,结果就是我的形象受到损害,我看起来像个傻子或疯子。
于是,很多受害者在貌似公平的处境中落入败局,因为就大多数暴力而言,尤其是性侵和儿童性虐待这类暴力,从一开始双方的权力就不对等,背后的文化支持也不平等,更有权力的一方更有能力定义有利于自己的事实,
弱势者要推翻对方列举的事实且证明相反的事实,难度更大。
此外,公众对受害的情况存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预期,当受害事实低于预期,它得不到关注,当事实高于预期,会激发出猎奇与怀疑的心理——这使受害者不被信任。事实上不只受害者如此,涉及到相关的研究,超出公众预期的研究者也不被信任,人们怀疑受试者说谎,怀疑研究者有偏见地采用信息,等等。

(取材自《嘉年华》)
不得不承认的是,还存在另一个诱惑,即从加害者的角度看待性侵,会带来额外的心理优势:一方面,立足于我更有权力,我更安全,我不会沦落到受害的处境,这增加了人们的安全错觉,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且相信自己比大多数普通人更为高明,这种自利偏差增加了人们的自尊,使他们对自己感觉更好。
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都受不同的动机驱动,这使我们做出不同的反应,持不同的立场。
我想也许只有我们了解自己身上的反应,才能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这句话:
普通人也在参与受害者面临的创伤环境,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或多或少都参与了。
而无论如何,旁观者还有立场可以选择。但受害者就没那么幸运了。
社会对创伤事件的预期是“它是罕见的”,但这是一种错觉,性侵家暴对许多女性而言都并不罕见,它不是少数事件。这类暴力对个人的伤害,不在于人们粗浅认识中的人身伤害、身体伤残(这也是它们被认为应该区别于伤害罪特殊处理的原因),而在于它破坏甚至摧毁了人们对日常的适应能力,使人感到惊恐、无助、失去控制,随时感觉自己大难临头,即使在脱离创伤困境,回归日常生活之后,这些感觉仍然存在,这就是创伤心理。

(取材自《素媛》)
虽然我们日常的语境中时常会半开玩笑地提到,“你给我留下心理阴影了。”但在心理治疗领域,创伤心理也不是轻易就会有的,它跟防御系统的崩溃有关。
我们的防御系统是这样工作的:当面对威胁时,身体会激发交感神经系统,激增肾上腺素,我们会集中眼前处境并开始警戒,与此同时,我们屏蔽身体的其他感受,比如饥饿、寒冷、疼痛等,但我们会增强恐惧与愤怒的感受,这两种情绪促使我们最终做出战或逃的行为决策。这是我们正常的适应性表现。
然而,假如我们陷入的处境无法战也无法逃,假如这个处境持续激发我们的防御,却一再使我们绝望,无法战也无法逃,正常的防御系统就会崩溃,我们就难逃创伤的反应。
创伤心理也不仅仅关乎一时的痛苦,它有长远的后果。
创伤经历使身体应激、情绪、认知都受到损害,功能上不再协调,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可能会切断自己对创伤事件的情绪反应,也就是记得事件,却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我们可能会怀有强烈的情绪,但却遗忘事件的细节;我们可能总是惶恐不安暴躁警惕,但不记得为什么(尤其是在受虐儿童身上可能会存在)。
于是,我们可能会过度反应,因为相信自己一直处于高度危险的状态中,我们的身体和心智一直处于警戒状态,对最小的刺激可能都感到极大的惊吓。
我们可能会持续体验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与其他记忆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记忆我们会将其视为一种事件活动,在我们不同阶段和场合讲述它的时候,它都是以符合当下逻辑和气氛的状态呈现的,它是完整的阐述。但创伤记忆,人们体验它的方式通常以意象和身体感官为主,难以描述和呈现当时的细节,他们也许会忘记日期、几点钟、对方的脸和名字,但却可能记得床单的味道、天花板的污渍、壁纸的色彩。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创伤记忆受高浓度肾上腺素或其他压力荷尔蒙的影响,使它留存于记忆的方式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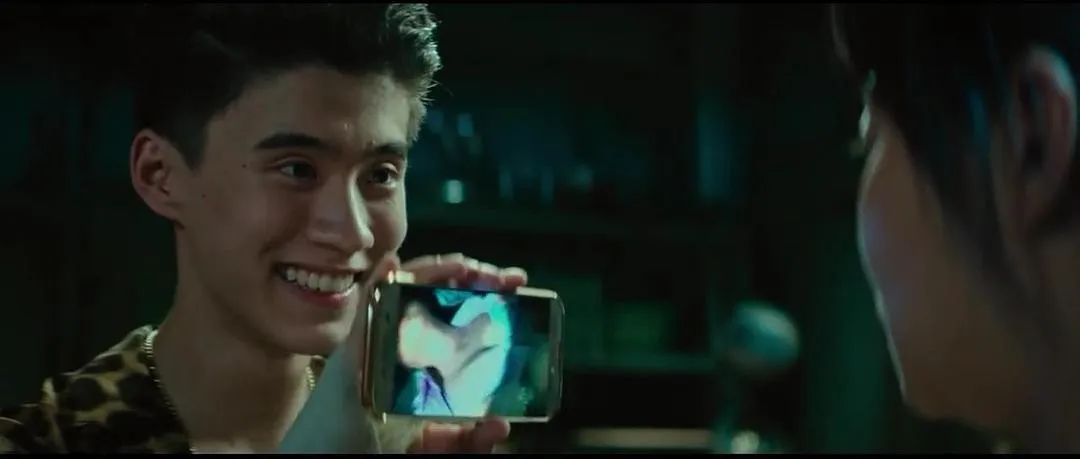
(素材取自《误杀》)
我们可能会封闭解离。在面临绝望时,我们可能会选择第三条路,像那些在车灯前被吓傻的小动物,它们僵在当场直到车轮碾上去,我们的意识也僵在当场,直到一切发生。我们封闭自己的感官,将自己的意识和情绪从身体中解离出来,告诉自己,“我不在这里”“这个人不是我”,由此来保护自己活下去。即使在危机解除后,受害者仍有可能采取这种应对策略,比如
放弃行动、增强疏离、停止警觉和判断、扭曲现实、人格解体
等等,人们通过放弃对自我的意识和建设,来隔离对痛苦的感知,通过放弃对自我的负责和麻木,来获得对放弃的控制感。
性侵/儿童性虐待受害者的额外创伤
性侵与儿童性虐待,绝大多数发生在熟人之间,较之于其他暴力,它带来更为深远的创伤后果。
与所有创伤受害者一样,她们的自我感也受到损害甚至破碎,她们额外需要建立与外界的连接,借由维系与他人的关系来重新修复自我感。

(取材自《可爱的骨头》)
但经历过熟人的性侵和性虐待,使女性尤其是儿童难以重建和他人的关系,因为本该是最值得依赖的关系,却是使自己陷入绝望的根源。人类的大脑潜意识是这样工作的,它将熟悉的视为安全的,这套经验使我们存活。对受害者而言,她的潜意识依然使她将熟悉的视为安全,但她的心智却难以信任这套系统,她必须自己时刻警觉,防备,把日常的生活都视为生存的考验,建立关系要付出太多的额外努力,而这对身体和精神也是极大的消耗。
儿性童虐待受害者会受性虐待更大的影响,尤其是加害者为其照料者时
。我们都知道,
儿童与其照料者之间的安全感是其人格发展的基石
,儿童要发展出正面的自我感和正常的自尊,照料者需要合理限制自己的权力,以免破坏儿童的自我感、自主权和自治权,在性侵发生后,这个基石被摧毁,儿童的自我感会丧失,她们如果没有在当下也会在稍后意识到,自己的自我与自主在这种性的剥夺之下,毫无意义。
这会使她们首先感到羞耻,被照料者否定自我,意味着自己毫无意义,而自己所有自我的念头和珍视就成了一种过分自爱的羞耻。她们如果接受这是爱,一种与众不同的爱,这使她们觉察到自己是同龄人中的异类,低人一等;她们如果不接受这是爱,承认自己不被爱而被伤害,她们会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才被惩罚。
这还会扭曲儿童的认知,儿童的思考模式通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己来解释处境和结果,如果得到爱,意味着自己做得对,如果没得到,说明自己做错了,她们会以此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处境会扭曲儿童对现实的认知和对自我的认知。
而随着她们长大,逐渐了解社会规范,她们又会有新的耻感,比如内化迂腐的社会观念,比如“残花败柳”“被弄脏了”“一辈子都毁了”“其他人不会接受这种女人”,为此而感觉自己不值得不配,或耻辱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一个成功的反抗者,又或是耻辱于自己曾经无知,耻辱于自己曾迎合。
我认为这也正是社群要持续声援的原因,
受害者需要对抗的不只有创伤的经历和加害者,还有整个社会文化和她们挥之不去的耻感和无力。
她们如果沉默,将持久受困于自我责备和自我批评和羞辱,而如果她们发声,迎来的是社会的批评和羞辱,那么社会就在协助加害者。
在一些情况中,如家暴和家庭内性虐待,受害者与加害者长时间处在一起,形成社会关系或事实存在上的囚禁(比如剥夺通讯、限制回家时间、剥夺经济能力)等,这种囚禁是隐蔽不被察觉,也往往不被警方承认的,家门没有锁上,窗户没有封死,但它却造就了无数的妇女儿童成为囚徒。儿童因为没有谋生能力,妇女因为经济、社会、心理、法律等因素或更直接的恐吓威胁,而成为囚徒。

(取材自《房间》)
长期的囚禁使加害者更容易在环境中建立威权统治,他成了受害者生命中最有权力的人,由此受害者的心理和认知为加害者所塑造——于是受害者表现的种种对现实的扭曲和对加害者的顺从和迎合,也就不足为其。
加害者天然具有了解自己风险的优势,这使他们的决策更有条理,一些人甚至有社群可以交流心得,恋童癖有QQ群交流,对女性精神控制(如PUA)也有自己的网站和组织。
精神控制在这类案件是常见的,它属于暴力的一种,但并未被法律所认可,事实上它比身体暴力更为常见。加害者通常将身体暴力作为最后的威慑手段,而巧妙地应用精神控制,使受害者感觉孤立、无助,破坏她们与他人的连接,使她们相信加害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甚至,诱使受害者认为自己拥有控制感——只要学会体察加害者的心情、学会顺从、学会爱加害者,自己就能恢复对生活的一些控制感,就可以做得了一些主。
我们很少看到纯洁无辜的完美受害者,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加害者通常深谙人心,也有强烈的合理化自己犯罪行为的动机,他们会把受害者拖下水。加害者会设计受害者犯错,或使她们相信自己有污点,来击溃受害者对自己的珍视,使她们厌恶自己,小的比如说谎、偷窃、迎合加害者,大的比如伤害别人,帮助加害者伤害别人,令她们相信自己并不干净,不是好人,甚至是引诱了罪恶发生的祸首(加害者通常的辩词是,我是被你引诱了的,我本来不想对你这么做的,但你暗示了我,我爱上了你),被拖下水会击溃受害者的自我感、道德信念,使她们关闭感觉和判断、思考,放弃进取(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无所谓,破罐子破摔),这也使其后她们的人格发展与行为表现更容易走向边缘化。
儿童性虐待受害者如果是长期的被侵害,人格常常会被严重侵蚀,对相关的从业治疗师来说,儿童期长期经历性虐待的受害者身上具有一些易被识别的特征,她们容易被辨别,对受害者而言,使她们多了获得治疗资源的机会,而与此同时,对其他普通人来说,这种人格上的严重侵蚀可能使她们难以被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