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小时候吃过蚕蛹、蚱蜢、蝗虫,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内格尔1974年的那篇著名论文《成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旨在说明感质在物理与心灵之间的解释鸿沟。根据内格尔的论证,物理信息(Physical information)无法让我们知道
身为一只蝙蝠的感觉是什么
,也借此推知,我们无法知道他人对于颜色、声音、气味、疼痛等等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诚如文中所言,
昆虫并不是像黑猩猩(或我们)这样的灵长类动物,那么它们是如何感知和体验这个世界的呢?我们常说,“这只猫胆小,和其他猫不一样”,但我们似乎不会说,“那只蜜蜂的性格很不同”——如果昆虫拥有个性呢?一只蟑螂能感受到痛苦吗?一只蛛网内的苍蝇会经历恐惧吗?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网站
(reducing-suffering.org)
,内容包括如何减少动物痛苦乃至昆虫苦难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当然,涉及到“昆虫能否感受到疼痛”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比如荷兰
瓦赫宁恩大学的汉斯
·
施密德(Hans
Smid)教授就认为,昆虫没有必要具备疼痛的感觉,因为神经细胞是十分耗费能量的组织。如果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么生物没有必要多发展出一套神经系统来感受疼痛。
文/
Barbara J. King
译/杨睿
校对/石炜
原文/
nautil.us/issue/47/consciousness/if-bugs-are-sentient-should-we-eat-them

Oyamel Cocina Mexicana餐厅以昆虫料理闻名
Oyamel Cocina Mexicana是华盛顿潘恩区附近的一家餐厅,这家餐厅的特色是昆虫料理。2013年6月,一个凉爽的夜晚,我和朋友斯蒂芬·伍德(Stephen Wood)沉浸在墨西哥瓦哈卡的多彩颜色和多般气味之中,来到了这家餐厅。餐厅名中的Oyamel是墨西哥中部一种冷杉树的名字。帝王蝶从美国和加拿大迁徙到墨西哥之后就栖息在这种树上,亮橙色的鳞翅是这种蝴蝶最醒目的特点。餐厅入口处的玻璃门上镶嵌有透明的蝴蝶图案,或红,或黄,或粉;还有一些蝴蝶小饰物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随风舞动。

油炸蚱蜢馅玉米饼
但我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蝴蝶。我们是闻着炸草蜢(chapulines)和油炸蚱蜢馅玉米饼的味道寻来的。点完单,女服务员还说我们运气不错:蚱蜢从墨西哥运来,要过海关,有时候就会断货,但那天晚上店里刚好有足够的蚱蜢,随时可以送上餐桌。我们真是很幸运。我们还点了其他几种昆虫小吃。服务员一上菜,菜里的昆虫肉还清晰可见。我把玉米饼拿到嘴边,一只纤弱的蚱蜢腿还掉到了桌子上。
昆虫料理不只出现在这家餐厅的菜单上:
油炸的野生蜻蜓、裹着长有玫红色绒毛的狼蛛卷、火烤大螽斯芝士三明治
(
大螽斯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鸣虫,中国北方俗称蝈蝈)
、油炸蚱蜢馅玉米饼
......如果你四下看看,你会发现,今天美国和欧洲有不计其数的食物都是用昆虫和蜘蛛制成的。昆虫餐厅的档次各有不同,有高档餐厅,也有路边摊。科学博物馆还会举办虫虫节,给游客提供昆虫美食。食虫文化正在逐渐兴起。

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方早就有吃昆虫的习惯。现在,西方国家的一些餐馆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昆虫料理加到菜单里去。
从很早之前开始,世界上就有数百万人一直在寻找昆虫,定期、有意地食用昆虫。当然,他们不会从床底下或是落满灰尘的阁楼里捉虫吃。他们会在野外寻找昆虫,给他们提供新鲜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元素,或者从传统市场上购买商家备好的昆虫或昆虫粉。
事实上,人类吃过的昆虫种类已经超过了1600多种。
自然学家大卫·劳本海默(David Raubenheimer)和人类学家杰西卡·罗斯曼(Jessica M. Rothman)指出:“从全球视野来看,西方世界对昆虫的憎恶很不寻常。西方人可能大喊大叫地要吃蜂蜜,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当他们食用蜂蜜时他们也是在吃蜜蜂反刍的产物。不过,许多国家都有意识地将各类昆虫作为餐桌上的美食。”
享受昆虫料理时,我思考了一些昆虫迷不常提起的问题:
对于昆虫的智力、个性和感觉,我们到底知道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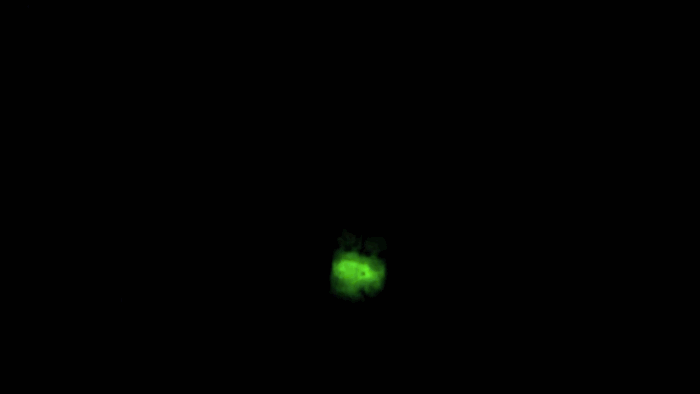
昆虫并不是像黑猩猩(或我们)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宠物。
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把它们看作体型极小的动物。我在新泽西的郊区长大。小时候我很喜欢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观察蚂蚁农场内看似匆忙、实则井井有条的劳动盛况。我俯下身去看院子里的蚂蚁窝,追踪进进出出的红蚂蚁。在某些宁静的夏夜,我还会去看萤火虫,看它们在潮湿的空气中一闪一闪,传递信号。
我不记得我是否曾把这些小生物当成独特的个体,它们都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存在于我的世界里。
哪怕是我的宠物猫“女王”和我养的狗“影子”,甚至是一家去布朗克斯动物园旅行时遇到的大象和猴子也没有得到这种待遇。
昆虫并不是像黑猩猩(或我们)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宠物。如果我们发挥我们对昆虫和蜘蛛天生的好奇心,提一提问题:它们如何在自然界中生活?在它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小生命就遭受了不公的待遇。
事实上,翻看历史记录,我们就会发现,人们一直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直到不久之前,才有人开始问有关黑猩猩(或猫和狗)的问题。
昆虫具有学习能力吗?它们如何以有智慧的方式与它们的世界进行互动?它们是否具有各自独特的个性,来体验世界?
如果我们走到户外,胡蜂可能只会给我们留下嗡嗡作响的印象;如果不小心被它们蛰伤,我们还会感到刺痛和烦躁。
但我们还有另一种方式去看待它们:把它们看作大脑活动活跃的动物。纸胡蜂(Paper wasps)的大脑不到人类大脑的0.01%,它们能认出同一个蜂巢内的同伴。
这是神经生物学家伊丽莎白·蒂比布茨(Elizabeth Tibbetts)发现的。在试验中,她用涂料更改了一些纸胡蜂的面部特征。面对这些突然“改头换面”的昨日同伴,原本和这些纸胡蜂同处一巢的纸胡蜂态度非常反常、敌对。但对于那些涂了涂料但面部特征没有变化的纸胡蜂,它们的态度又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这种敌对反应的特性表明,纸胡蜂能认出同伴的面孔,以此来判断谁是它们的同伴。
变了脸的纸胡蜂会被同伴们视为陌生蜂,受到不友好的对待。

纸胡蜂的大脑不到人类大脑的0.01%,它们却能认出同一个蜂巢内的同伴。
蒂比布茨在实验中使用的蜂种的蜂后(纸巢蜂)在“合租巢”里也能和其他蜜蜂协同合作,但蜂巢中的雌性之间会出现竞争。针对这种情况,“看脸”的特性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因为蜂后需要区分潜在的对手和潜在的盟友。蒂比布茨继续训练这些胡蜂,让它们学会区分各种图像。她和搭档艾德里安·戴尔(Adrian Dyer)写道:“最令人震惊的是,简单地从胡蜂的面部移除天线或重新排列脸部特征,能够很明显降低它们的面部识别能力。”
这个事实让她们意识到,胡蜂大脑中有专门的区域处理面孔的整体形象,就像我们人类一样。
蒂比布茨又进一步扩大了她的研究,加入了第二种长足胡蜂(Polistes metricus)。这种长足胡蜂建蜂巢时,往往只有一只蜂后,而不是一群。在这种情况下,用涂料改变了面部特征的同伴并不会立即引发蜜蜂的面部识别反应。但在这一实验中,有一点很有意思:在训练阶段,这些蜜蜂确实学会了对面孔区别对待。根据推测,这个物种在进化时并没有直接获取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潜伏在它们大脑深处,在自然条件下并不会出现。总体来说,通过胡蜂和蜜蜂的研究,蒂比布茨和戴尔得出了结论:“
在它们的迷你脑子里进行的活动,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
”
这个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昆虫?
如果我们是在谈论学习能力的话,答案是肯定的。在昆虫学中,学习能力是指获取并在大脑中呈现新信息的能力。从历史角度来看,昆虫学的理论假设都和本能、天性有关。
昆虫学中的这个等式:“简单的神经系统=本能驱动的行为”,非常直截了当,也错得一塌糊涂。
某个春晨,我伏在案上写这篇文章,推特给我推送了新消息:果蝇能作决定——当它们得到的信息不够、难以评估时,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出决定。在一个设计巧妙的实验中,首先训练果蝇避开某种强烈的气味,然后让果蝇在两种浓度不同的气味样本之间做选择。两个气味样本之间的差异越小,果蝇作出选择所需的时间就越长。神经科学家沙米科·达斯古普塔(Shamik DasGupta)和他的团队得出结论,“果蝇要积累足够的证据才会采取相应的行为”。
换句话说,这些昆虫在面对复杂的选择时,要收集到足够让它们作出合理选择的信息之后,才会作出选择。
这种根据环境变化发生变化的变量对果蝇的影响和果蝇的特定基因(FoxP)和果蝇约0.1%的神经元(约200个)相关联。

蜜蜂的摇摆舞
蜜蜂的摇摆舞也是一个说明昆虫学习能力的例子。蜜蜂相互交流,获取新信息。在黑暗的蜂巢中,觅食经验丰富的蜜蜂翩翩起舞,为年轻、幼稚的蜜蜂提供信息,让它们知道往哪个方向飞多远能找到合适的花朵采蜜。得益于科学实验的发现,我们知道,蜜蜂的舞蹈并不像GPS设备一样,会把详细的驾驶说明发送给我们,精确定位。
相反,它们传达的信息只能把蜜蜂引导到大体正确的区域。到了那里,花朵本身会提供视觉和嗅觉上的线索,蜜蜂落到这些花上,开始采蜜。
除了果蝇和蜜蜂的例子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例子可以说明:昆虫具有个体和群体学习能力。在2008年审查报告的末尾,杜鲁文·杜卡斯(Reuven Dukas)总结说:“学习能力可能是昆虫的普遍属性;昆虫依赖学习,实现所有主要的生命功能。”昆虫是聪明的,信息通过身体或社会环境进入它们的感官和大脑,它们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估。在一些情况下,它们还会思考如何对它们掌握的信息采取行动。
我吃的这些蚱蜢,它们其实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活在世界上。
2012年,我在BBC自然网站的科学新闻版块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新研究发现,蟋蟀幼年时期的经历可以影响成年后的个性。”这是生物学家尼古拉斯·迪瑞兹(Nicholas DiRienzo)和他的同事们的假设。看到这句话,我很惊讶,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现在的动物行为研究人员认为,在某些昆虫物种中将会发现一些属于昆虫个性的指标。昆虫是有个性的!
迪瑞兹在《动物行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解释说,勇敢是指个体愿意让自身冒险的程度,是不同年龄和不同情况下个别蟋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勇敢往往与侵略共存。研究人员指出:“
我们认为侵略性是该物种的个性特征,尤其是侵略性和勇气共存,形成了一种行为综合征。
”

名为Gryllus integer的蟋蟀
科学家在实验中把小蟋蟀听到的声音作为变量
(这种蟋蟀叫Gryllus integer,通常出现在美国西部)
。一开始,实验中的雄性蟋蟀还太年幼,还没有长出耳朵。蟋蟀的耳朵长在大前脚的胫节上,上面有薄膜,可以感受声音的振动。在饲养过程中,蟋蟀被分成两组:一组模拟野外环境,蟋蟀们会听到野外坏境中很多蟋蟀的叫声;另一组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沉默。
很多蟋蟀的叫声被称作“声音性信号”,因为雄性蟋蟀在争夺配偶时才会发出这样的鸣叫。那些没有
听到
声音性信号长大的雄性蟋蟀更具侵略性,也更有可能成为统治者。我对这个实验的细节很感兴趣。想象一下,研究人员目不转睛地看着蟋蟀们争相鸣叫,以此来评估它们的侵略性。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在沉默环境中长大的雄性蟋蟀会更强大,更擅长打斗。
迪瑞兹和他的搭档认为,蟋蟀利用它们听到或听不到的声音,来确定蟋蟀的密度。什么都没有听到的蟋蟀认为它们在寻找雌性伴侣时不会面临竞争,它们相应地采取行动;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它们发现了证据,表明有更多的竞争,它们就会表现出更强大的支配力和更强的侵略性。
换句话说,来自周围环境的信号会改变蟋蟀的个性。
现在,衡量蟋蟀的胆量和侵略性给我们带来的是对动物个性有限的认识。
和蟋蟀打交道,我们不太可能感觉到蟋蟀是非常有个性的物种。当我们面前的动物是鸡或者猩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一些动物在更复杂的维度上存在个性的差异,不仅仅是胆大/胆小或有无侵略性的区别,而是群聚/独立,情绪反复/冷漠,满怀恶意/脾气温和等等区别。
昆虫存在于这个世界,它们绝对不是彼此的复制品。蟋蟀鸣叫实验表明,个性不仅仅是先天遗传的问题,饲养环境在其中也会发挥作用
(对于一些科学家来说,动物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动物的习性则只受遗传的影响)
。简而言之,我吃的这些蚱蜢,它们其实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活在世界上。

柬埔寨金边某家餐厅的狼蛛料理
丹尼拉·马丁(Daniella Martin)写道,
狼蛛的味道有点像烟熏龙虾
。虽然我痴迷于昆虫和蜘蛛的生物学和进化研究,平时也会尽量不伤害这些动物
(除了一些例外,比如蚊子)
,但当我面对狼蛛料理的时候,我仍然在微微颤抖,因为我受到了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被狼蛛咬伤而丧命的真实案例。它们是巨型蛛形纲动物
(现在已知最大的狼蛛腿长12英寸,重5盎司)
,它们毛茸茸的外观还是能让人吓一大跳。
当我们所处的周边文化对它们没有太多的喜好时,狼蛛体型大小和身体特征带来的负面反应可能会更加严重。
马丁说:“我们要感谢《蟋蟀杰明尼》
(Jiminy Cricket,科普动画片)
,蟋蟀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很好的宣传。而狼蛛却截然相反。”
然而,狼蛛多毛的特征应该引人迷恋,而不是让人恐惧。因为这是狼蛛在进化过程中根据它们的生存环境和需要进化而来的:
狼蛛不会织网,但和其他蜘蛛一样,它们也主要是通过振动感受它们的世界;绒毛能帮助它们感受这些振动,帮助狼蛛捕获猎物。
我曾经线上采访过迈阿密动物园的策展人尼科尔·阿特贝里(Nicole Atteberry),了解了这些有关狼蛛的事实。阿特贝里还在继续研究区分害羞和侵略性的狼蛛,想要了解狼蛛的个性。

有感知力的蜘蛛?有研究表明,蜘蛛,如图中的红绿橙狼蛛(Greenbottle Blue Tarantula),就拥有个性。
我们如何才能在昆虫个性的问题上找到合理的位置,这才是关键。塞缪尔·马歇尔(Samuel Marshall)是一名在法属圭亚那(世界狼蛛之都)研究野生狼蛛的科学家,他对狼蛛进行了很多研究。
他警告说,由于狼蛛的基本神经系统,我们不应该在思考狼蛛认知或情感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例如,他认为狼蛛不可能和许多脊椎动物一样,变得焦虑或沮丧。然而,2004年他在接受《发现》杂志的访谈时表示,他也认为“个性”一词可以用来描述同一品种的单一群体的不同处理方式。
这些变化趋势构成了一部分潜在的复杂行为。马歇尔的学生梅利莎·瓦雷启亚(Melissa Varrecchia)和芭芭拉·瓦斯克斯(Barbara Vasquez)发现,印度狼蛛更喜欢和它们的兄弟姐妹结成同伴。马歇尔当时说,“寿命较长的巨型蜘蛛,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
在探索蜘蛛的个性时,我联系了马歇尔。他利用自己广阔的科学界人脉,把我介绍给了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的蜘蛛生物学家苏珊·里埃特(Susan Riechert)。里埃特告诉我:“蜘蛛的行为是高度可重复的,它有非常强大的遗传因素,因此我总是把蜘蛛的行为倾向作为它的习性。”她的观点表明,某物种变化多样的技能并不全都是它们学习到的复杂能力。里埃特和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发表了一篇关于蜘蛛社会组织变化的论文,阐述了
(在这种具体情况下)
这种变化对环境影响的不透明度。

栉足蛛
里埃特和琼斯研究的是栉足蛛(Anelosimus studiosus),这是一种出现在北美和南美森林中的群居蜘蛛。栉足蛛的母蛛会照顾幼蛛,这在蜘蛛中是一个非典型特征:母蛛保护它们年幼的后代,通过反刍给它们提供食物。母蛛死后,在子女中占主导地位的雌蛛通常会控制巢穴,赶走它的兄弟姐妹。美国科学家找到并锁定了两处蜘蛛群落聚居地带
(每一处都聚集了相当数量的蛛巢)
,从佛罗里达南部的大沼泽地(26°N )到田纳西州东部(36°N),每隔两个纬度为一个间隔带。需要乘船才能到达这两处蛛巢聚集地。他们发现,在所有纬度上,独巢
(一个蛛巢中只有一只雌蛛)
是最常见的类型。科学家最开始是在30°N的地方发现了多只雌蛛共处一穴的现象和不同雌蛛合作的巢穴结构,这些现象会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增加。
实地研究的结果非常有趣。里埃特和琼斯收集了四个蛛巢,两个原本处在冷水环境,两个处在温水中。他们在实验室里用这些巢穴养蜘蛛,然后把这样产生的第二代蜘蛛放回到不同纬度的野外。这样一来,原本独巢的小蜘蛛被放到了常出现多只雌蛛一巢的纬度地区,反之亦然。用科学家的话来说,无论最终所在地的温水或冷水环境如何,所有的小蜘蛛都倾向于表现父母的巢穴结构。“例如,多雌蛛巢穴被移到独巢普遍存在的田纳西州之后,就会出现新的多雌蛛巢。”即使巢穴结构
(独巢或多雌蛛巢)
与纬度相关,但某些特定的环境因素并不会导致某些特定的巢穴结构。这种蜘蛛的群居行为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没有表现出可塑性。一部分个性是由环境塑造的,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环境变化会塑造出一些个性吗?这似乎没有可能,但肯定有证据证明这些蜘蛛具有一定的习性。
想要确定它们是快乐,还是痛苦,颇具挑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