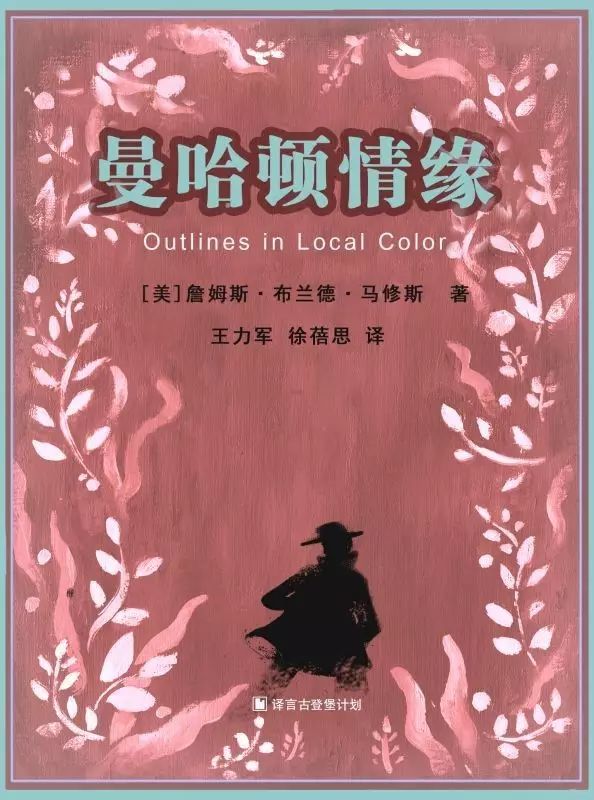
《曼哈顿情缘》一共十二篇,一年之中每月一篇,记录了以曼哈顿为背景的十二个小故事。这篇《华尔街求爱记》有着短篇小说的短小精湛,用精致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的浪漫开头。
这个故事,我们猜到了开头,也预料到了结尾,但是却没有想到,过程中充满了小小的惊喜。男女主角,一个是从西南部来的小镇青年,一个是在纽约学习生活的年轻女孩,一次聚会中相识,很快成为朋友,心照不宣的喜欢彼此,充满默契的日常对话,让一次告白变得温馨和趣味横生。
华尔街求爱记
(下)

“我们去三一教堂,怎么样?”他建议,“那里的墓地安静极了。”
“这里不够安静吗?”她问。说着他俩离开了古堡花园。
“我得承认,这里并不太吵闹,”他回答,“但是我烦透了那些高架火车,呼哧呼哧地在脑后响个不停,你不觉得烦吗?”
她怪怪地斜瞟了他一眼,然后轻声笑了。
“哦,好吧,”她回答,“如果你认为三一教堂的庭院是个好地方,那我也不介意。”
说完她的脸刷地红了,她把头扭到一边。
于是他俩穿过高架铁路下的空地,由于忙着过铁路,年轻人没有发觉她脸红。
在他俩围绕椭圆形的博灵格林公园走的时候,女孩朝一个守护小公园的灰衣警察点头致意。
“那人是谁?”小伙子问,醋意顿生,尽管警察看起来不下五十岁了。
“他是奥罗克先生,”她解释道,“是罗斯·奥罗克的父亲。罗斯两年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然后当了演员。她现在发展得很好,去年她演过伊丽莎白女王——她看起来多像女王!我敢肯定她比老女王漂亮得多。”
“但那位老女王,”他回应,“可不是雀警的女儿呀—你们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对吗?”
“我不这样称呼他们,”她回答,“我觉得说俚语很粗俗。”
“但是男孩都管公园警察叫做雀警,对吧?”他坚称。
“野小子那样说,”她回答,“但是我知道奥罗克先生不喜欢这个称呼。”
“可以理解,”他说,“如果我有伊丽莎白这样的女儿,估计我自己就想做国王了。”
“哦,”姑娘继续解释,“罗斯确实想要他父亲放弃这个职位,她说她挣的钱足够养活他,让他不用工作了。尽管她强烈要求,可她父亲就是不愿意放弃。罗斯是个很和善的姑娘,一点也不傲慢自大。去年她还来我们学校为我们表演过诗朗诵。你应该来听听她朗诵的《霄禁的铃声今晚不会响起》,跟你说,她朗诵得太棒了。”
“我不信她朗诵得比你好。”他断言。
“哦,你不信吗?”她充满真诚地回应道,“那只是因为你没有听过她朗诵。而且,她对我也很好,她还称赞过我的朗诵呢。”
“你朗诵了哪首?”他问。
“哦,我总是选一些激昂的爱国诗篇。我先朗诵了《谢里丹的骑兵队》,然后姑娘们要我再来一首,我就又朗诵了一首《老宪法号军舰》——但是我最喜欢《谢里丹的骑兵队》。罗斯·奥罗克说,在她听过的所有朗诵者当中,就数我对《谢里丹的骑兵队》理解最深。不过话说回来,她总是这样夸赞人。”
“我估计她是知道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你没有登上舞台。”爱她的人坚定地说,“你要是登台,她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没见过她,但我肯定她不像你这样好看!”
“谢谢你的夸奖,”女孩回答,“如果我们不是在百老汇这里,而是在三一教堂前,那我就向你行屈膝礼了。但要是你见过她的话,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她真美得像画一样。”
“你的意思是她像上了油彩那样鲜亮吗?”他问。
“你真刻薄,”她反讥,“但罗斯即便在舞台上也完全不需要上油彩,她有一副姣好的面容。”
“在纽约,拥有姣好面容的姑娘不只她一个。”他声明;红晕又迅速浮上她的脸蛋,继而迅速消退。
他俩来到了三一教堂门口,看到一小群男女涌进教堂参加下午的礼拜。
“你不应该对罗斯怀有偏见,”女孩说,说着他俩转身离开百老汇,开始在墓碑之间漫步,“她是我的好朋友,罗斯说如果我要走上舞台,她就帮我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