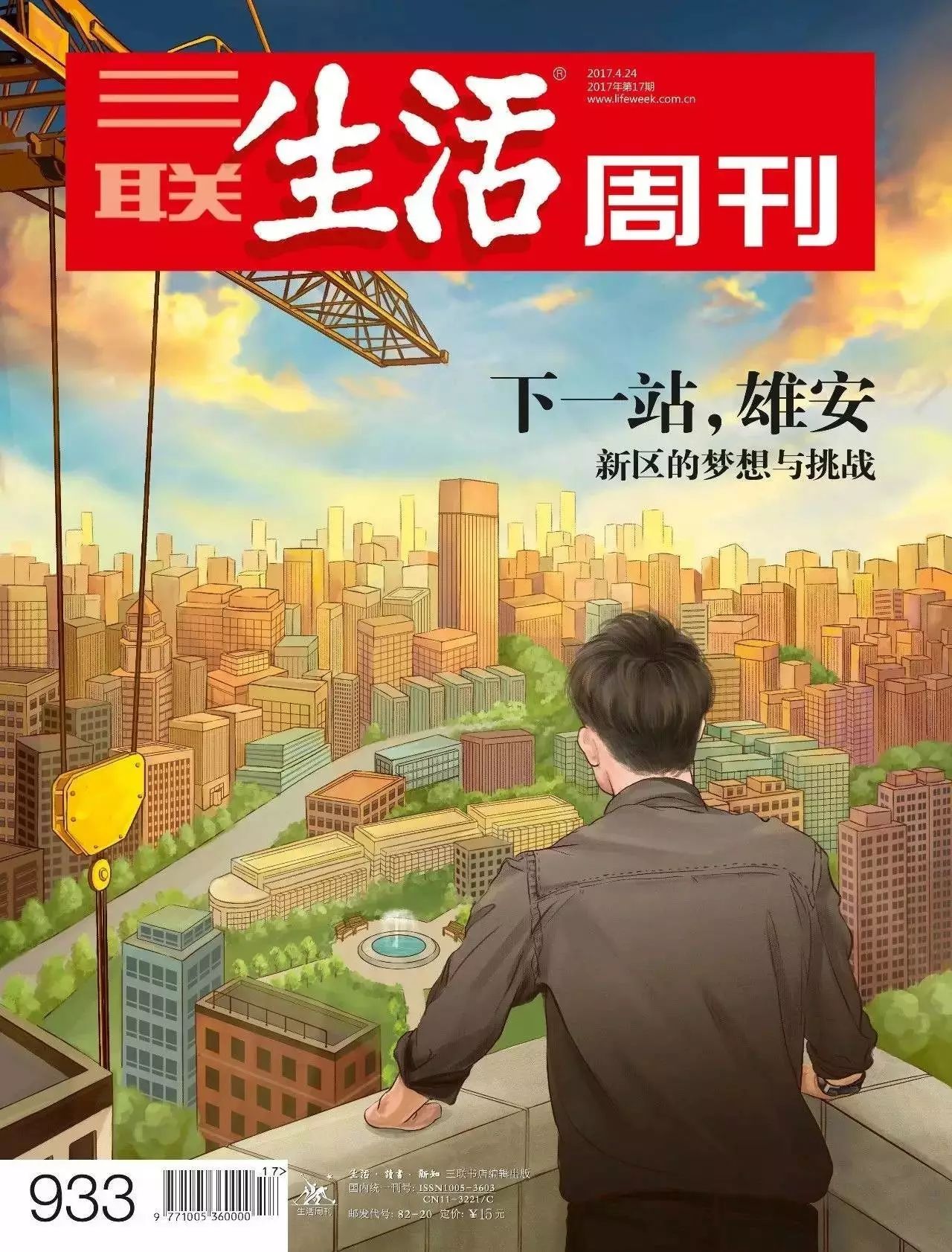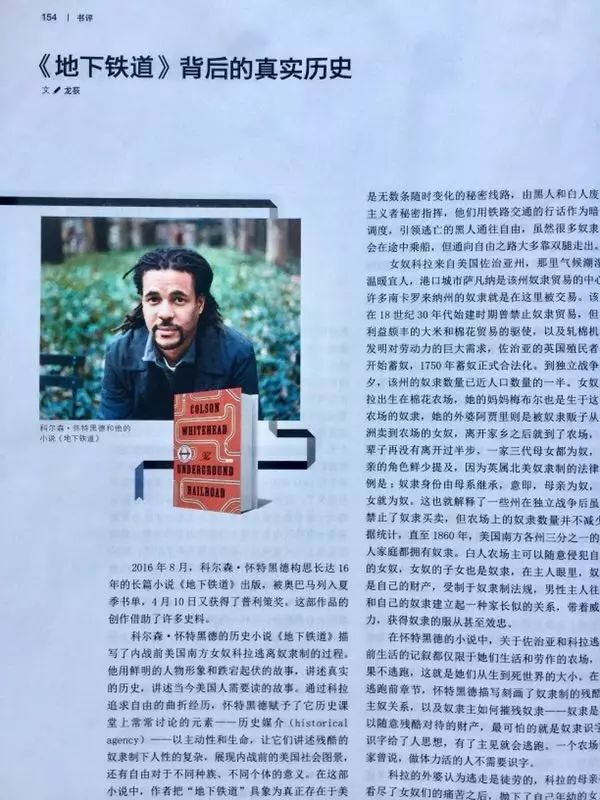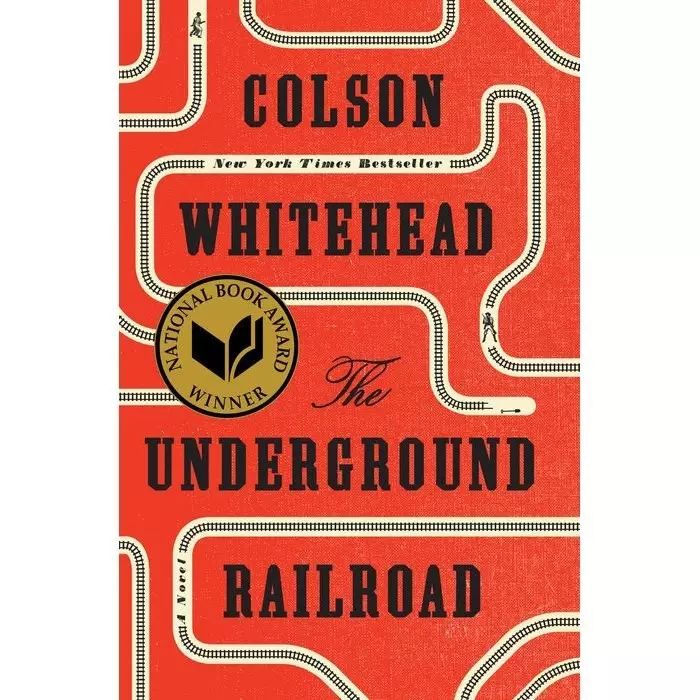
(上上周赶着看完的小说的书评,写给三联,第一次被贝小戎老师催稿。是本很符合我胃口的小说。我认为,了解美国,了解建国早期殖民地建国建制历史和了解奴隶制和内战历史同样重要,前者有通俗易懂的歌舞剧汉密尔顿讲了故事,那么奴隶制的惨痛,这本历史小说可算得上文学作品里的歌舞剧汉密尔顿了。)
科尔森
‧
怀特黑德写内战前美国南方女奴科拉逃离奴隶制的历史小说《地下铁道》,是一部极具野心的非虚构作品。他用鲜明的人物形象和跌宕起伏的故事,讲真实的历史,讲当今美国人需要读的故事。通过科拉追求自由的曲折经历,怀特黑德赋予了历史课堂上常常讨论的元素
—
历史媒介(
“historical agency”
或翻译为载体)主动性和生命,让他们讲述残酷的奴隶制下人性的复杂,展现内战前的年月美国社会图景,还有自由对于不同种族不同个体的意义。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写实化了抽象的
“
地下铁道
”
概念,变成了真正存在于美国奴隶制南方地下的通往北方和西部的通道,有铁轨,有驾驶员和调度员。史实中的
“
地下铁道
”
则是无数条随时变化的秘密线路,由黑人和白人废奴主义者秘密指挥,他们用铁路交通的行话作为暗语调度,引领逃亡的黑人通往自由,虽然很多奴隶也会在途中乘船,但通向自由之路大多靠双腿走出。
因为是虚构的故事,怀特黑德得以绕开历史学家们在写作时常遇到的问题
——
如何让历史媒介说话,如何用史料支持自己论点。基于对历史史料和历史著作的研究,怀特黑德在他富于诗意和节奏感的叙事中穿插进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不用担心有人会质疑分析论断背后的史料是否站得住脚。但只要对美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甚至美国历史的研究者,读罢便能体会到怀特黑德的小说的精巧构思中透出的野心
——
在如今的美国,这样一部讲述奴隶制对于美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未消退的创痛和影响的历史小说是非常必要的,和历史课本里反复强调的相关历史名词、事件、人物一样重要。
在小说致谢部分,怀特黑德感谢了一些对这部小说有很大帮助的人,富兰克林
‧
罗斯福
(FDR)
和他签拨款支持的联邦作家计划
(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这个计划完成于内战结束后近
70
年,最初只是为了在大萧条中增加就业而开设的公共事业振兴署(
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的分支项目,最后却成就了非凡的历史意义。这个计划通过采访还健在的前黑奴们,搜集整理口述历史资料,为保存和还原奴隶制的罪恶,记录黑奴的惨痛经历留下最紧迫也是最鲜活的资料。对于怀特黑德来说,这些史料定为创作人物经历和故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来自维基百科)

怀特黑德还致谢了黑人废奴主义者和学者弗里德里克
‧
道格拉斯
(Frederic Douglas)
,废奴主义作家哈利艾特
‧
雅各布斯,以及著名左派历史学家埃里克
‧
方纳。本身也是逃跑奴隶的弗里德里克
‧
道格拉斯的演讲以及著作节选是美国本科生大学历史课上必读内容,废奴主义者哈利艾特雅各布斯曾将自己逃离奴隶制的经历写成自传《一名女奴的人生际遇》(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
,该书节选全文也是历史课必读。在逃跑的过程中,雅各布斯曾经在阁楼上生多时,这段记叙大概启发了怀特黑德笔下科拉藏在阁楼的经历。左翼的历史学者埃里克方纳所著的历史课教材《给我自由》(《
Give Me Liberty!
》),是许多大学历史教授教授本科美国通史课的首选。在这本教材中,不同族群在美国对于公民权的追求,公民的定义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是方纳写作的主要线索,亦是方纳学术研究生涯关注的重点。方纳的学术著作《内战后重建
: 1863
至
1877
年美国未完成的革命》
(
《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
)
是历史系美国史专业的必读。除此之外,埃里克方纳前年所著的《自由之路》(
Gateway to Freedom: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
则详细记叙了
“
地下铁道
”
从美国南方沿东海岸一线经由费城纽约往北一线的历史。
女奴科拉来自美国佐治亚州,气候潮湿温暖宜人,港口城市萨凡纳是该州奴隶贸易的中心,许多南卡罗莱纳州的奴隶就是在这里买卖进口。该州在十八世纪
30
年代始建时期曾禁止奴隶贸易,
但因利益颇丰的大米和棉花贸易的驱使,以及轧棉机的发明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佐治亚的英国殖民者们开始蓄奴,
1750
年蓄奴正式合法化。到独立战争前夕,该州的奴隶数量已近人口数量的一半。女奴科拉出生在棉花农场,她的妈妈梅布尔也是生于这个农场的奴隶,她的外婆阿贾里则是被奴隶贩子从非洲卖到农场的女奴,离开家乡之后就到了农场,一辈子再没有离开过半步。一家三代母女都为奴,父亲的角色鲜少提及,因为英属北美奴隶制的法律惯例(
Partus sequitur ventrem)
是:奴隶身份由母系继承,意即,母亲为奴,子女就为奴。这也就解释了一些州在独立战争后虽然禁止了奴隶买卖,但农场上的奴隶数量并不减少。
据统计,直至
1860
年,美国南方各州三分之一的白人家庭都拥有奴隶。白人农场主可以随意侵犯自己的女奴,女奴的子女也是奴隶,在主人眼里,奴隶是自己的财产,受制于奴隶制法规,男性主人往往和自己的奴隶建立起一种家长似的关系,带着威慑力,获得奴隶的服从甚至效忠。
在怀特黑德的书中,关于佐治亚和科拉逃跑前生活的记叙都仅限于她们生活和劳作的农场,如果不逃跑,这就是她们从生到死世界的大小。在她逃跑前章节的怀特黑德描写刻画了奴隶制的残酷,主奴关系,以及奴隶制如何摧残奴隶
——
奴隶是可以随意残酷对待的财产,最可怕的就是奴隶识字,识字给了人思想,有了主见就会逃跑。一个农场管家曾说,做体力活的人不需要识字。
科拉的外婆认为逃走是徒劳的,科拉的母亲在看尽了女奴们的痛苦之后,抛下了自己年幼的女儿逃跑了,奴隶巡捕者都未能把她捉到。母亲的逃跑改变了她的命运,塑造她世界观的重要事件,也在她的心中埋下怨恨和苦涩的种子,她在逃跑中寻找过母亲未果,她想象的不是母女重逢的感人场面,而是如何侮辱和报复抛下自己独自逃走的母亲。科拉母亲成功的逃跑也一直使残酷的追捕者无法释怀,对他来说,反抗逃亡的基因一脉相承流淌在这对母女身上,也就促使他一直不放弃追捕科拉,一路带给她和帮助她的人厄运。
小说的倒数第二章,交代了科拉母亲真实的命运,借她说出奴隶制的邪恶不仅是白人对黑人施暴,同时还有这种恶也让黑奴变得邪恶,使他们互相举报和残害,他们有的人甚至对白人主子愚忠,成为加害同胞的帮凶。这也是科拉遭遇的根源,年少时被奴隶群体排挤欺凌,一进入少女时代便被奴隶们轮奸,她冒死保护救下的黑人在同她一起被惩罚之后,却不再同她说话。不同逃跑奴隶经历的曲折和不同,也呈现了黑奴逃走需要面对的重重困难危机和不确定性,他们不仅会死在追捕者的手下,也会死在路上碰到的白人手下,死于密林沼泽猛兽的威胁。
怀特黑德对历史资料的研究,赋予了科拉主动的声音。她从佐治亚越过州界线,逃到南卡罗来纳,初尝
“
自由
”
的滋味让她放松了警惕,她喜欢新生活以至于希望留下来不再一路往北。怀特黑德描述了黑人在脱离受限的环境后,学习和进入社会的认知复杂周遭的过程。这个过程使逃跑奴隶对白人社会充满了怀疑和戒备,对于复杂的白人社会的恐惧使他们不得不跳出舒适的假象,一直逃跑,直至真正获得自由。
怀特黑德的小说不仅呈现了黑奴们悲惨命运的多种形式,奴隶制对人性的折磨,同时也描绘了多面复杂的白人和其它种族人物的形象,体现奴隶制对整个美国南北社群的影响之深。如果用后世眼光评判,白人中处于道德制高点的,一定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开凿和维护地下铁道的白人废奴主义者,他们冒死保护和传送黑奴通向自由的作为是世代相传的秘密和任务。科拉在南卡罗来纳的曲折经历表明,那些对她友善,教她识字,给她工作的白人则属于另一个群体。他们不认为逃向自由的黑奴是和白人一样平等的人,他们认为黑人仍然是劣等人。黑人需要被管理,需要被教育,他们是劣等种族,他们的数量需要控制,他们甚至用黑人进行传染病学实验。这些看似友好的白人,不过是披着进步外衣的白人主义者,把种族歧视和灭绝的观念被包裹在进步的外衣下。
独具想象力的怀特黑德还描述了科拉在南卡的博物馆里的扮演黑奴的经历。博物馆展示玻璃的两侧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构建起来的对比空间,通过活生生的黑人表演黑奴来到美国的经历,加深玻璃另一侧观者对黑人是劣等性的认识。
小说中最可怕的白人角色乍看是那个身材高大,一直不择手段追捕科拉的奴隶追捕人。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追捕,让黑人向他们的命运投降,因为他们根本不配美国人的天定命运。他甚至也痛恨那些来自欧洲的穷苦白人移民,觉得他们和黑奴一样低贱,但因为肤色的不同,他们不会成为奴隶。而书中反复强调,参与追捕奴隶的,往往有许多事白人社会底层的不法之徒。书中还偶尔提到一些印第安人的命运,在科拉的世界里,印第安人几乎已经被赶尽杀绝,剩下的成为了白人的帮凶。
怀特黑德小说中描绘的白人社会最可怕的恶并不限于个别人,而是那种根植于白人社群的平庸之恶。那些举报自己父母保护黑人的小孩,那些每个周末集会庆祝,最后以对黑人行私刑将庆祝推向高潮的居民,他们正是平庸之恶的推手和执行者。行刑架就摆在城里公园里,平日是白人儿童爬上爬下玩耍的地方。在历史上,这样聚众庆祝执行私刑的活动并没有因为内战和废奴而停止,内战后吉姆克劳法的存在,一直流行到上个世纪上半叶的私刑和对黑人的欺凌,甚至如今白人警察对于黑人的不公残酷对待,似乎都是这平庸之恶的延续。处在平庸之恶的对立面的,则是黑人对白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永远留在美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奴隶制和种族问题伤痕。最近引起争议的事件是惠特尼双年展上,白人艺术家唐娜
‧
舒尔茨一幅描绘
1950
年代黑人少年艾米特
‧
提尔无辜被白人私刑致死后开棺葬礼的油画,许多反对者认为一个白人艺术家绘画这样的作品是对黑人社群的冒犯和对历史的不敬。
怀特黑德用科拉一路逃向自由的路程,也描绘美国不同区域在内战前特点。东北部海岸各州是最自由开明的避难所,纽约在内战前已是自由世界的中心,费城集中了许多废奴主义者和组织,新英格兰则是可以开始新生活的地方,虽然如此奴隶追捕者仍然可以在街头追认可疑的逃亡奴隶。
跨过边境进入加拿大,那就是没有奴隶制的乐土。西部是未开发的边疆,是奴隶制的恶还没有污染到的地方,一路往西就是探索,便是独立自主的疆界。把奴隶带向自由的地下铁道在小说里真实存在,怀特黑德不止一次提到铁道之深,范围之广,大概就是为了提醒读者,在那些黑暗和不公的年月,有多少人为了获得自由或帮助他人逃向自由付出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最后开放式的结尾,也似乎警示读者,奴隶制创痛是无法愈合的,对于自由的追寻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这篇书评发在4.24 雄安新区封面故事的三联生活周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