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微信君和译文社社科编辑室主任、
“译文纪实系列”
的策划
张吉人
老师聊天时说到:你那本
《慕尼黑的清真寺》
不大好推啊,人家一看到书名“
清真寺
”三个字,就觉得是个跟宗教搭边的书,就……
张吉人老师用他一贯的淡定口吻说:这是个
讲历史
的书啊,并不是
讲宗教
的书,不要怕么。
然后我就说,那你干脆自己出来谈一下这本书吧,咱们录个视频玩。
张老师回了一个字:
好
。
于是,经过一番努力,视频来了:
感谢实习生陆玺同学所作的视频编辑工作
张吉人老师录视频那天重感冒,所以声音比较轻
我觉得,张老师在最后的那句话非常重要,对
《慕尼黑的清真寺》
,对
张彦
在书中要表达的观点,仅仅根据一两个关键词而妄下判断是不行的,
不管怎样
“
读者们还是要先看书才能对书得出自己的认识
”。
以下分享一篇来自
《北京青年报》记者张知依
老师所写,在简体中文版
《慕尼黑的清真寺》
出版之前,对作者
张彦
所作的专访,大家可以结合
张吉人
老师在视频里陈述的观点,进一步去了解这本非常值得关注
的好书。感谢
北青报
和
张知依
老师授权允许转发。
一座清
真寺 三段争夺史
一本书讲述冷战给穆斯林带来了什么
文
|
张知依
原发于
|
北京青年报 2015 年 12 月
- 声明:感谢允许刊发,
转
载先请私
信联系
-
年初(2015 年)《查理周刊》编辑部的枪杀事件恐怖阴霾还未散去,
(2015 年)
11 月 13 日晚,法国再遭恐怖袭击。巨大的震惊点燃人们心中的悲悯与愤怒,也呼唤深入思考的理性之光。
思考,源于更多的了解,否则只能产生偏见和误解。面对世界的巨变,面对欧亚的穆斯林危机,面对极端主义在全球的兴起,甚至面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新闻提供的表象,其实知之甚少。然而在通往真知的道路上,总有人孜孜不倦前行。
2010 年,美国记者
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
,写下一本名为
《慕尼黑的清真寺》
的著作,他试图告诉人们,极端主义在欧洲并非突然涌现,西方国家对此应该反思。该书中文版有望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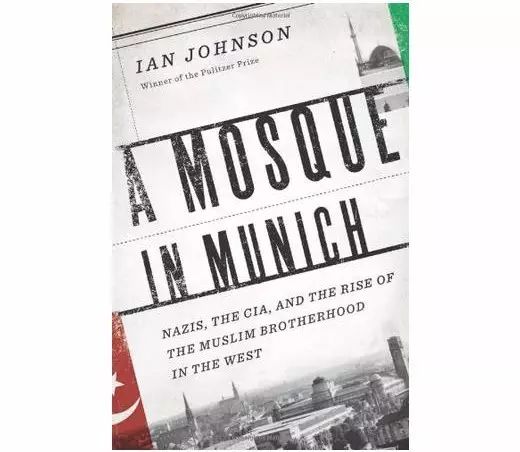
英文版
《慕尼黑的清真寺》
封面
简体中文版现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本期青阅读想与张彦探讨的,正是他试图揭示的这段特殊的历史。

Ian Johnson
,中文名
张彦
。
2001 年普利策奖获得者
,哈佛大学尼曼学者。他是《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纽约客》等多家媒体的撰稿人,也担任《亚洲研究期刊》的顾问编辑。曾任《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和德国分社社长。
为什么慕尼黑的清真寺会成为圣殿
青阅读:
当我知道您的书《慕尼黑的清真寺》即将在中国出版时,正好发生了巴黎遭遇恐怖袭击的事件。您在知道这个新闻时,感受是什么样的?
张彦:
听到这条新闻,我想到这是欧洲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在欧洲有很多伊斯兰教徒,他们中的少数人虽然在欧洲长大,但并不觉得自己是欧洲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憎恨这个社会。
青阅读:
您觉得巴黎遭遇这样的悲剧,和您在《慕尼黑的清真寺》里写到的问题有关联吗?
张彦:
这本《慕尼黑的清真寺》英文版在 2010 年出版,和巴黎的恐怖袭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是从历史性的背景讲述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欧洲的发展。
青阅读:
您从何时开始关注伊斯兰世界?为什么要写《慕尼黑的清真寺》这本书?
张彦:
可能要从“9·11”事件说起,报道显示,“9·11” 4 架飞机的驾驶员都到过德国。其中一个人到德国前已经是恐怖分子了。但另外三人只是去德国留学的普通男孩,后来却投身恐怖主义。我想知道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他们在德国期间遇到了什么?受到了什么影响?后来我发现他们碰到了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在西方大城市的势力很大。我在欧洲一些档案馆做研究,发现穆斯林兄弟会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进入欧洲,而且获得了在西方国家提供的基础支持。一些年轻人在欧洲碰到伊斯兰教,然后就变成激进分子。
2003 年,我在一家售卖伊斯兰激进主义文学作品的书店内浏览,注意到一张很特别的世界地图。在地图四周,缀饰着各地著名的清真寺——麦加大清真寺(千千万万朝觐者每年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穆罕默德登天处),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还有,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慕尼黑并不是伊斯兰的中心,那个清真寺也不是德国最大的,更别说在欧洲了。不过,它仍然是某些人心中传之万世的圣殿。我决定做些研究。后来,我发现有三类群体:纳粹思想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员和伊斯兰激进组织,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支持这座慕尼黑的清真寺。于是写了这本书。
纳粹、中情局、穆兄会对宗教的争夺和利用
青阅读:
您在书里写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纳粹、美国中情局、穆斯林兄弟会对穆斯林的利用和争夺,以及后来失控,您能简单为我们的读者梳理一下这个过程吗?
张彦:
《
慕尼黑的清真寺》,反映了三个历史阶段,不同的主体利用伊斯兰教来达到政治目的
。
第一个阶段是
二战
。纳粹俘虏了许多苏联穆斯林士兵,计划利用伊斯兰作为二战期间的政治武器。纳粹军官认为,因为苏联境内非俄罗斯裔的少数民族对苏联的怨恨,可以利用穆斯林士兵建立军队,帮助德国攻打苏联。
第二个阶段,1945 年德国战败之后,这些伊斯兰教士兵此时还留在德国。
冷战
开始,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越来越强,后来遭到纳赛尔政府的管制,很多人逃到欧洲。美国人认为虽然纳粹德国失败了,但是他们还要打苏联,因为当时美国很少有伊斯兰教徒,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在欧洲的穆斯林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阵地对付苏联,宣传西方社会的好和苏联社会的坏。西德政府认为看管这些穆斯林的“老战友”比较困难,就为他们建一个清真寺。美国人告诉他们可以把慕尼黑的清真寺作为基地。
第三个阶段是
冷战后伊斯兰激进主义对清真寺的利用
。最著名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正是穆兄会,把慕尼黑的清真寺变成了一个实现党派目标的基层政治组织。伊斯兰激进分子与传统的穆斯林信众不同,他们通过宗教、民主或暴力,来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在与伊斯兰有关的具体问题上,例如要在社会中实施伊斯兰教法,信众就会团结一致。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中隐而不宣的是对西方社会及其价值的排斥,并认为它们与伊斯兰格格不入。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更喜欢使用“政治伊斯兰”来描述这一运动。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是激进的伊斯兰教派,他们要建立一个百分之百的伊斯兰教国家。
这三段历史,都发生在这座慕尼黑的清真寺,反映了被政治化的伊斯兰教。
我的目的就是写一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就是可以用一个清真寺的例子来写这三个阶段。我的根本看法是,政治和宗教要分开,不应该让宗教成为政治性的工具,一旦把宗教变成政治工具,可能在短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但后患无穷。
青阅读:
如果把宗教和政治连在一起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张彦:
可能会带来恐怖主义。我想声明,我不是要写纳粹、美国中情局或者穆兄会让穆斯林变得极端,因为我不是一个伊斯兰教思想的专家,所以我书里面没有分析极端主义是哪儿来的,或者伊斯兰教义里面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资格写伊斯兰教分歧或者历史。我想分析西方国家给穆斯林带来了什么,以及这种利用是如何在西欧发展的。我认为,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极端主义者,就很危险。
青阅读:
您认为美国中情局在其中有什么责任?
张彦:
1950 年代,美国的机构行动协调委员会领导了在慕尼黑和伊斯兰世界中进行的绝大多数秘密宣传活动。最近解密的文件显示,在 1950 年代,美国新闻署每年在秘密行动上的花费约为五千万美元。美国每年总共要花大约五亿美元—— 1950 年代的币值——来试图影响世界舆论,这实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活动。这个时期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成果就是自由之声电台的母组织“美解委”(Amcomlib)成立。不敢说美国创造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这个极端主义是伊斯兰教国家自己创造的,但美国给在欧洲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
美国应该了解并且面对这些历史问题
青阅读:
这本书从调查到写作完成一共花了 4 年时间,其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张彦:
最困难的是我没办法看到美国中情局的所有档案。我写了很多申请给中情局,收到很多拒绝信。从中情局拿到的资料上,很多纸上只有一个单词,其余的部分都被认为是机密被涂成黑色。所以我只能看到一部分 50 年代的档案,有一些还是当时的官员离任时从办公桌上拿回家捐给档案馆的复印件。不过我自信认为这些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美国在资金上支持了穆兄会,只不过看不到具体的数字。
青阅读:
写法上,您选择用《华尔街日报》非虚构写作的方法来写一段历史,在讲述一段历史时,这样的方法有局限吗?
张彦:
写非虚构的错误是你太重视有意思的地方,而忽略了历史本身。
可能一件事情分成四个部分 ABCD,ACD 这些部分一定是最有趣的,但 B 这个部分却是最重要的,你该怎么抉择?非虚构作家会选择 ACD,但历史学家会把艰深的 B 写好。这就存在另一个问题:
在专业上有研究的人,不知道如何写一本大众能看懂的书,但作家可能又会忽略最重要的问题
。
用非虚构的这种方法来写历史会陷入两难:学术方面的人不承认你,做书评的看不懂不知道你写得对不对,不能理解你花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心血的作品。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因为非虚构写作,需要细节丰富的故事,但是在我写的这段历史里,三个主要人物中情局驻慕尼黑特工罗伯特·德雷尔、纳粹时期突厥学专家格哈德·冯门德以及穆斯林兄弟会高层领导人赛义德·拉马丹,他们三位并没有什么交集,写历史的时候你没办法碰到他,要按照档案写,但是有时候不会那么有意思,就需要做一些取舍。
当然我认为我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最重要的 B 部分没有拿到足够的资料。
青阅读:
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有什么反响?
张彦: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之后收到很多书评。但是在美国有这样的问题——每一个事件都会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工具,甚至包括气候变暖也是。大家只看到支持自己政治观点的那部分,没有看到全局。
我认为美国应该了解并且面对这些历史问题,不然很难在今天做出决策。你看最近 15 年,美国不断在犯同样的错误,包括支持逊尼派,打击什叶派等等。他们就觉得自己可以利用伊斯兰教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些是错误的。宗教是离人心很近的东西,教徒会把宗教视为宝贵的东西。可是一旦把宗教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会创造更多的灾难。
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读不懂《古兰经》
青阅读:
《慕尼黑的清真寺》您写成于 2009 年,但是今天欧洲的穆斯林问题已经演化得更为复杂和激烈,您认为这中间有什么变化?根源是什么?
张彦:
基本上没有变化,我觉得还是老问题。以前西方国家认为伊斯兰教只是一个可供我们使用的工具。到最近几年,西方国家依然没觉得这些移民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只是关注他们身上有没有极端主义的色彩。西方人觉得,这些穆斯林往往住在城市破破烂烂的郊区,他们的清真寺跟我们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今天法国的惨剧也证明了这个观点。
青阅读:
如今人们都认为 ISIS 是最大的问题,您在《慕尼黑的清真寺》中探讨的问题,能解释 ISIS 的现象吗?
张彦:
我认为 ISIS 基本上没有宗教的目的,他们带着非常悲观和黑暗的目的,他们根本不太理解他们自己的宗教。
这让我想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身上有这样的问题:他们看不懂《古兰经》,只知道《古兰经》是一种伊斯兰教的基础,用当代的视角、粗暴的解释把《古兰经》带到现代。他们不是很有学问的伊斯兰教徒,也没有什么神学的背景,对《古兰经》像教材一样,背诵它,然后利用它,太过简单地理解它。
青阅读:
今年以来,大批中东难民涌入欧洲,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如何看待德国的难民政策?
张彦:
我的家在德国,也看到很多难民出现在德国。德国的难民政策今年使 100 万难民进入德国,超过德国人口的 1%。德国大的城市现在住房条件比较紧缺。我认为短期当然要支持这些难民,但长期来看还需要其他解决办法。我并不认为恐怖分子会借机嵌入欧洲,真正的恐怖分子如果需要来,不需要借这样的机会,他们都持有法国或者比利时护照。
青阅读:
大众对伊斯兰问题的了解不多,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您认为哪些人的著作值得推荐?
张彦:
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的问题是,在很多领域有学术研究的人,写不了大部分老百姓能看得懂的东西。他们做研究是为了在学术上有成果,他们不会讲故事。刚开始写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找一本关于穆斯林兄弟会历史的优秀著作,后来我竟然没有找到这样的书,最近的一本写到 1955 年就停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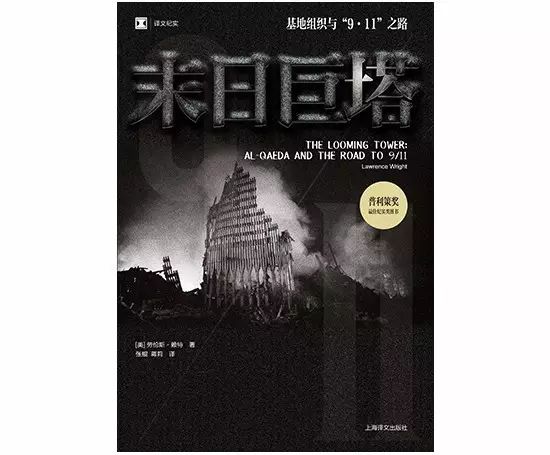
如果想了解“9·11事件”,可以看
《巨塔杀机》
(劳伦斯·赖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者注)作者是一个纽约的记者,花了很长时间写这本书。
Gilles kepel 是一名上了年纪的法国学者,他有很多研究,其中一本书翻译过来名叫《伊斯兰的郊区》。他到巴黎的郊区去研究穆斯林的生活,想看看属于他们的社会到底在发生
些什么。
(完)
相关图
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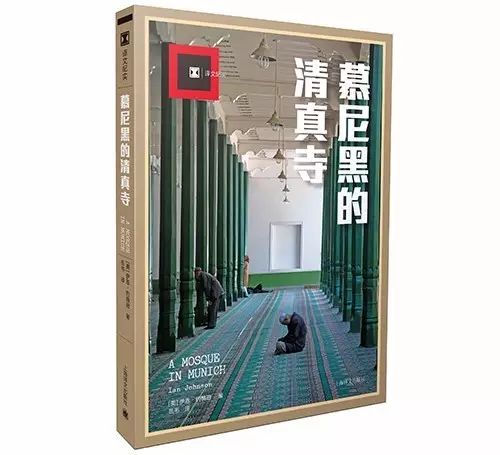
《慕尼黑的清真寺》
(译文纪实系列)
[美] 伊恩·约翰逊
|著
岳韦
|
译
慕尼黑清真寺与恐怖活动有着令人不安的联系。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美国曾试图争取穆斯林在阿富汗对抗苏联,著名的基地组织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但慕尼黑清真寺还要往前推三十年,那是冷战之初。在这里,德国,穆斯林卷入的是一场心理战,一场观念之争。
没有人能说得清西方对穆兄会既迷恋又排斥的心态。最著名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正是穆兄会,把清真寺变成了一个实现党派目标的基层政治组织。而穆兄会在西方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起源于运作慕尼黑清真寺的那一小群人。
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前德国分社社长伊恩·约翰逊,用文字追踪欧洲伊斯兰激进运动 70 年!
点击文末
阅读原文
可购买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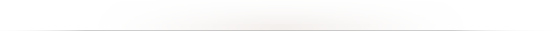
上
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
stphbooks
”添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