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20年8月30日 下午2:00-4:00
地点:北京建投书局国贸店
对谈嘉宾:作家阿乙、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罗东、维舟
本文是当时对谈的摘录
“大量的阅读使我获得了非常准确的思考功能,对所有人生经历的事情都能够理解。”
罗东:我们需不需要阅读,阅读它有没有用?有时候可能认为阅读是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想把它贴上一个“有用”的标签,或者是不需要这样一个期待,我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个私人的,不想被外界干预的。但有时候我们又觉得,私人的阅读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每个人的阅读可以综合起来变成一个公共阅读,好像它可以改变一个社会的观念。阅读对于个人来说,到底有用吗?
阿乙:如果没有阅读的话,我的写作就寸步难行。基本上是这样,我的生活非常寡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非常寡淡,但是,它内在又极其地丰富,如果你没有阅读的帮助的话,你的生活就白白过去了。残雪老师好像说过一句话,她说“如果你不写作的话,你30岁以前的生活会像一堆废羽毛一样,或像一堆废纸一样的,就会缺乏意义”。
如果不是阅读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有这么宽广,阅读这一块会让你在纵向上和横向上都获得极大的膨胀,像宇宙一样的膨胀。如果不是阅读的话,我很难想象这个人的一生会过得多么地单薄。

阿乙,作家,《人民文学》中篇奖、蒲松龄短篇奖、林斤澜短篇奖得主
我最近的写作就是这样,我突然发现我进入到40岁以后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俯视过去的人生,对过去人生里所有未解之谜、过去轻松放过的事情,都能有一番很好的思考和理解,当时,有很多事情用常理没办法解释。但是现在都非常了然。这就是因为大量的阅读使我获得了一项非常准确的或者非常深刻的思考功能,对所有人生经历的事情,都能够理解。
我会理解我的祖母,为什么她会碰到任何一个人都会去诉苦,说她的身体疾病。这个我在读余华老师的《现实一种》里面,发现俩兄弟互相残杀的时候,他们的老母亲还在那里哀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糟糕。然后这个老妇人就在哀叹中悄然地死亡了。我发现其实在农村、乡村里大都存在着这种(现象),她需要通过疾病来呼吁别人关心她。
当时,会觉得我的奶奶很啰嗦,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疾病,她要走到街上,从街头说到街尾。现在通过很多的阅读,包括一些哲学的阅读,我觉得也读得比较痛快。我就是通过这个杂乱无章的阅读,获得了很多非常不专业的知识。对于人生的很多经验,也进行了重新的一个理解。如果没有阅读的话,我觉得我写的东西就和我过去写的日记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价值。
维舟:马原说作家有两种,一种像马原自己说的,他要读很多书才能写得出来,另外一种像朱文那样,不看其他人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都是从生活当中来,但我觉得朱文也不是说他就不去认真地观察生活,他也观察生活,只是说他可能脱离了书本的知识。所以,
如果你观察生活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阅读,它只是用看书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
。
我们大家都明白,创作实际上是输出,阅读是输入。在国内有不少所谓天才式的作家,早年的时候他也许是有自己的某种天才,他有某种灵感,他不断地输出。但写着写着,他那点输出就不够了。他就发现可能仅有的那点东西输出完了以后,接下来怎么为继,这就是一个问题。可能阅读是一种输入的方式,生活也是一种输入的方式,或者去实践也是一种输入的方式。
我们可能也不需要把阅读这个概念理解得太狭隘了,阅读实际上是一个丰富我们自己的过程,只不过是说书籍是比较浓缩的人类的经验,花几十块钱就能够买到这么浓缩人类智慧的一个结晶,大概除了书以外,没有其他的知识产品能够这么廉价了。所以我觉得阅读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选项。
罗东:维舟老师做书评,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你并不是说要为了写一篇书评,而是纯粹对这个书感兴趣,或者对这个议题感兴趣去读一本书,读完之后,你并没有写书评。
维舟:当然有很多,有的书因为读完了以后,觉得它太厉害了,要怎么评?我觉得好像自己都不敢去评,文学类作品可能很多时候是要自己去感受。可能有的人也注意到,我很少写文学批评,因为我觉得文学批评是非常专门的一个领域,而我自己写的很多还是和历史社科较为相关的。
我不会勉强自己去写,因为我也不是以写作为生的,所以对我来讲,很多时候我写评论只是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有的时候甚至不一定说这本书本身很好,但是我觉得可以顺着这个话题来写我自己的一些感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什么叫好书,在我看来,好书的定义不是说你在书中得到了多少干货,得到多少知识点,而是这本书对你有什么启发,它也激发了你什么思考,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不爱拿书来看的读者,碎片化阅读好像并不总是糟糕的。”
罗东:今天很多朋友会认为,看一本书,我不是去把这本书从头看到尾,或者说选我感兴趣的章节去看,而是听,听别人的综述,听别人解说,把书浓缩成这些,这样去看一本书,好像也能get到知识点。这种方式流行的时候,大家还会提到一个词,就是知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阅读,大家把它定义为碎片化阅读,就好像碎片化阅读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不是一个真正的阅读。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什么是碎片化阅读,就是我看手机的时候,我只看个摘要、看个标题,没有看全文。或者说这篇文章本来就是一个摘编,没有包括全文,所有的方面和所有的含义,对我们来说是不是碎片化阅读?

罗东,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主持视频栏目“罗东时间”
我们的父母在朋友圈转发一篇文章,可能并没有get到那个点,得到的也是二手或者三手的信息。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碎片化阅读?这样的阅读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意义?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在想,碎片化阅读好像也并不总是糟糕的,如果对于之前不爱拿书来看的读者,不是通过书来阅读的人,今天好像有了一种新的方式,可以读到一些知识点,而对他来说,这是不是知识的增长、知识的积累?但这个阅读在热爱读书、关注阅读的人当中,大家可能会说,这不是阅读。
维舟:我的阅读有时候也会碎片,可能碎片化阅读也是当代人的一种生存的处境吧,其实大家的生活都一样,生活节奏那么快,你要寻求完整的时间段来阅读,其实是很奢侈的。这个是大家共有的处境,我觉得不需要去作道德谴责。
为什么碎片化呢?有的人因为的确是没有时间,还有一种情况是,他读得比较浅。所谓浅的意思就是,他是从书里面去摘那些点,但是读的时候好像在扫描一样,就是在找,找哪些点对自己是有用的。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问题,它会整合进自己原有的框架里面,就是哪些点对我有用我就摘出来。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把读书变成一个自己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就像跑步一样,有人可能每天不论刮风下雨都跑半马,等到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规律形成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某种生活的自律,而这种自律感一旦形成,你会觉得很愉快。
你拿起一本书来,不管哪怕是在地铁上面,还是在麦当劳里面,你都会觉得自己整个人好像进入了一个异次元空间一样,一下子就沉浸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外面的什么我都不管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训练。
“一本书读不下去的时候,就像一个关口,这是自我质疑或自我更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罗东:一本书看不看得下去,或者怎样定义你把一本书看完了,可能我把它最关键的知识点看了,结论看了,它怎么论证的我看了,但我没有一页页地翻,没有从头看到尾,没有每一章都看,我好像也会把它定义为看完了,然后我在豆瓣上打一个读过。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
维舟:读一本书读不下去怎么办?我觉得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继续读。
我看到豆瓣上面的一些评论觉得非常惊讶,他们很自信,很多评论写的是:一本烂书、好差、不喜欢,就是很多直觉式的判断。喜不喜欢,是不是烂,这是一个没办法做分析的判断。因为这是一个感受。你要么赞同,要么不赞同。但是哪些地方不赞成,我们就可以来讨论。

这是我……就不用介绍了
所以当我看一本书,如果觉得读到有点怀疑的时候,通常我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我自己没读懂,然后我要不要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又或者说这个学科里面,其他的著作是怎么样的。所以,当你慢慢积累之后,才能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判断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训练。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原来你觉得写得不对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是你自己没理解,你根本就没有进入到那个脉络,换句话说,你可能连门都没有摸到。因此,如果你讲不出一二三来,你最好还是多去看一下。
有的时候你读一本书你读不下去,或者说你读得困难,你读得不感兴趣,
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是一个关口,这是自我质疑或者自我更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
罗东:所以其实阅读时间长了以后就发现,我确实需要一个知识框架,而且这个框架在无形之中就会形成。所以带着这个知识框架再去阅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判断,只是说这个框架它可以是开放的,而不是说我一见你它就封闭,我不再接受和他们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书。
我想问阿乙老师的是,你在阅读过程当中,有没有,其实你并没有被它吸引,你中途就中断了,这样的小说给你看完的小说之间,对于你来说又有怎样的区别?
阿乙:我在27岁以前,基本上就没有读完过一本书,归根到底原因在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心浮气躁,那个时候在上班,在做公务员,然后回家翻书,翻了两页睡着了,到第二天又觉得再接下来没什么意思,就再拿起一本书。
后来就很羞愧,然后有逆反心理,就说我每读一本,我就要把它完。它是我逼着自己随时要拿起一本书,无论它好看还是不好看,都把它读完。就这样才到今天,才能够做到读到很多的书,如果不是被别人这么羞辱性的问一下,估计一辈子就这么蜻蜓点水下去了,我始终认为,从我经验角度来说,读完一本书比半途而废要好很多。这个应该是一个真理吧。就是每个人读完一本书的快感和没有读完的奥丧,是对味的。
如果我读完一本书,我就感觉好像在游戏里杀了一个敌人一样,消灭他们。然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长篇,但是它字数也不够多,这样我一周可以杀几个敌人。所以最开始阅读的时候,读的都是短篇、中篇之类的,直到最近几年,觉得中短篇它对人的帮助实在有限,所以才会去读但丁、马塞尔·普鲁斯特,读这些人类最大的经典。就这样现逐步在在读一些长篇,这么读普尔斯泰,就转到这个层面上来了。说明我在阅读上晋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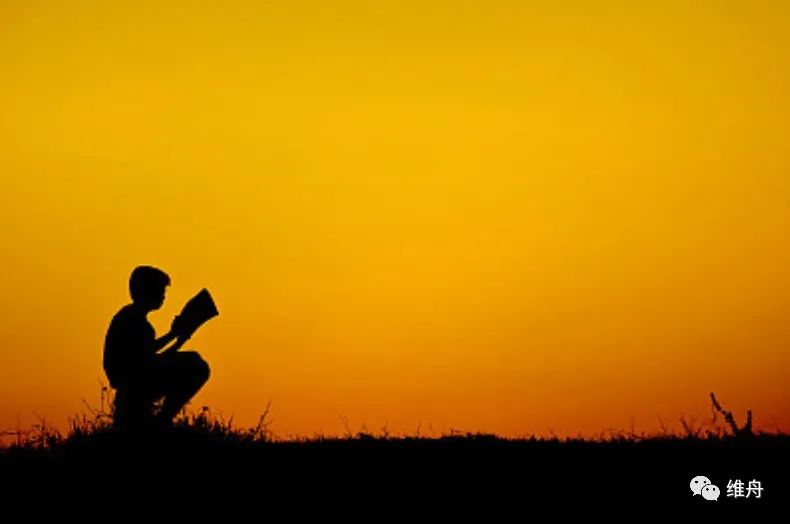
“评论者能够提供帮助的视角是,他可以把这本书给脉络化。”
罗东:我看一本书好像有一点懵懂,我需不需要去看别人的评论。别人的阅读感受和我的阅读感受是不是共通的?是不是可以交流的?我读一本书的时候,我需不需要去看别人是怎么评价,或者说,阅读需不需要书评。阿乙老师,你创作会去关注别人怎么评价你的书吗?看评论会影响你自己的创作吗?
阿乙:不但去看,还会搜索,主动的。作为一个恶习,现在已经把它给减少了,每年搜得不多。一个写作者在这个社会里,最便捷的就是看到别人的反应。古话说的双刃剑,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其实也影响到你自己原来的一些东西。它可能会摧毁你,也可能会帮助你。就看你自己当时的心态怎么样,看你厌恶这个评论还是你甘心接受它对你的指引。
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自己是一个学历非常低的一个作者,只有一个专科文凭,所以我在读书和写作的时候,比较信服那些比我水平高的人,所以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谦虚,因为比专科学历高的人大有人在,有本科、硕士、博士,然后我还挑,我一般挑博士的来指点。博士以下的我都不是很在乎。教授我最喜欢,就是子曰“无友不如己也”,在我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我读书也是这样的,我最开始在县城里头,为什么县城不是很好呢?不是一个好读书的地方。因为在县城里,当时专科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没有几个本科到县城,你在那里就是一个最牛的读书种子,你读的是王小波,你是当地非常高的读书水平了。
你到了省城以后,到了直辖市,到了北京以后,你才知道还有福柯,还有卡夫卡,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县城你能把这些名字写得完全正确的人能超过50个吗?不超过。记得去广州读书的时候,我会问在我们报社实习的一个很好的人,我请教他:“你说文学应该读什么?”他就教我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办法,叫魔幻现实主义,我是那个时候才知道,我是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有科塔萨尔,有马尔克斯,有博尔赫斯这一类的作家,有略萨,都差不多吧。还有很多很多。
我的整个系统都是别人帮我搭建的,所以我在省里面算一个水平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俯视天下,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很牛的读书人,在豆瓣上去给别人打二星、一星,我其实是让渡了自己的审判权,我尽量少地去审判别人。就不去过这个瘾。碰到有一些厉害的读者,我一般就会问他,对你影响最深的书是什么,这样我就会收获很多。
而且刚才维舟老师说的非常好,我无比赞成你说的,一本书如果是专家,如果是比你水平高的人指定的要你读,你读不下去,也要把它读下去。你只有读完了以后,你才知道这本书的益处有多大。
维舟:我觉得书评对于我们的公共智识生活还是挺有帮助的。你要知道,接下来怎么看待或者怎么解读一本原著。
我们对于书评价值的认定是什么?这其实不只是书评本身的问题,而涉及到我们怎么看待文化生活,怎么看待阅读这个问题。我们对于这些不同的文化领域,你有没有想怎么去品鉴它,还是觉得我的感觉就对了,我干嘛还要看别人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阿乙:我是一个书评阅读者,我之所以读书评,是因为有很多的作品,凭我自己的理解是搞不懂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书评人或者学者,来解释这个。用他们的灯光把那块钻石的各个侧面给我照出来。比如说海子的诗,还有顾城的诗,特别是顾城的诗,我对顾城是略微有偏见的,觉得他受教育程度不高,好像是小学毕业。他写的很多东西非常富有想象力,有一种神经质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我看过胡少卿对他的解读,从顾城本身的家庭背景,还有当时中国的背景来解读这个诗,一下就能看到很多我看不到的异相,我才知道为什么顾城这么厉害。书评人承担的使命很多,比如说追求自由,追求真理,还有一个严肃的任务,就是为像我这样的读者指明一些比较模糊,或者大家一眼放过去的那些进行一个导读,让我们这些后进分子跟上。
维舟:我觉得评论还有一个特点,可能很多读者本能的只关注这本书本身,就是这本书本身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评论者能够提供帮助的视角是,他可以把这本书给脉络化。所谓脉络化就是把这本书放到一个和其他书相关的领域,来看待这本书的价值。
英国作家吉卜林有一句话,他说“一个只了解英国的人对英国又了解多少呢”。他的意思是,如果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英国,只知道英国是这样子,那只有离开了英国,去法国、德国、印度去看看,你才知道,原来英国是这么地特别,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