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听说过一首诗:《从前慢》。
诗中有句人人皆可诵读的话: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在未曾了解作者木心的生平前,不少人都觉得,能写下这样唯美诗句的人,一定是个浪漫、纯情的翩翩公子。
可翻开木心的人生履历,却发现他这一生,过得并不如预期般顺遂。
含着金汤匙,出生在江南富庶人家的他,却在最好的年纪遭受3次无妄的牢狱之灾,断掉了三个手指,蹉跎了半生光阴。
母亲为他而死,家人为他反复呼告。
近乎20年的牢狱之灾,他终生未婚、未育。
甚至在生前,都未曾受到过太多人的敬重。
他这一生,满腹才华却漂泊流离,一身孤傲却屡遭困苦,却不曾控诉过命运的不公。
很多人都说,翻开木心这厚重的一生才知道,原来,人真的能在最难的时候站起来,原来在精神和肉体饱受双重打击之时,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木心,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1927年,木心出生在江南乌镇的孙家,原名孙璞,祖上算是名门望族,也是书香世家。
他家和茅盾是远房亲戚,早年木心读书时,每天都要经过茅盾的藏书馆,他也因此饱读诗书。
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木心从小在熟读传统典籍的同时,也接触了不少西方文化作品。
还是个孩童的时候,母亲就请了“一代词宗”夏承焘来给他上课,那时候,木心就已经显露出自己的文学天赋,他的诗词册,被老师夸赞与唐诗宋词无异。
倘若不是时代的变革,木心这位富家公子,大抵也会过上自己富裕闲适的一生。
可随着日本的入侵,乌镇被攻陷,木心的人生也随着时代创伤的出现,出现了转变。

17岁时,他离家前往杭州求学,时常穿着西装穿梭于大街小巷,学钢琴、逛书店,叫一个黄包车送自己回住处,很多人都笑他“华而不实”,木心内心不解,整个人变得消沉起来。
流言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专程赶来杭州看望他,教导他独自在外,要学会自我和解。
还鼓励他:
真的华要是先得到一“华”,再要得“实”也就不难了,从“华”变过来的“实”,才是真“实”。
母亲的话他听进去了,心中的困惑也随之消散。
他继续读书、绘画,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短短六年间,他写出了100多部中短篇小说,完成了数张山水画,艺术的底子就这样打下了。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个男孩将成为一届艺术家时。
谁曾想,29岁那年,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1956年,还在学校教书的他被人诬告,来人冲进他的房间,给他带上手铐押进了看守所。
原本的江南富家公子变成失去尊严的囚犯,那段时间,他身心饱受煎熬。
那时候他明知自己无罪,却不知该如何辩解,他忍受不了这样苦痛的生活,他的精神似乎要被压垮了。
母亲得知儿子被捕,焦灼苦闷,她强拖着病体四处奔波,为儿子求情,最终心焦离世。
监狱长像看戏一样大声告诉他这一消息,一句“你妈妈死了。”足以将他彻底击垮。
那段时间,他痛哭不已,哭得醒不过来,他知道妈妈是因为担心他绝望而死的。
被关在地下室里的他内心痛苦不堪,却也告诉自己“我会爬起来的”。
他也确实在那样的困苦中熬了出来。
半年后,因为查无实证,木心被无罪释放。
出狱后姐姐告诉他,母亲去世后,侍弄的花也枯死了,木心站在园中久久沉默。

后来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
是啊,他的母亲,在木心7岁父亲早亡后,便独自撑起了这个家。
她不仅为木心提供了富裕的物质生活,还在每一次儿子遭受低谷时,想尽办法开解他,也在他遭受无妄之灾时,拼尽全力也要救儿子出来。
人都说,年岁越大越知道,这世界上能这样为孩子奔波的,大抵只有他的父母了。
人在低谷处就知道了,无论先前自己有多高的名望,一旦跌落谷底,能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只有家人,也唯有家人。

30岁那年,木心出狱。
那时候的他也曾想过,自己人生的坎坷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谁曾想,10年后的冬天,因为画作与藏书,因为出身与生活习惯的问题,他再次被捕入狱。
这一年,他39岁,他依旧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命运就这样猝不及防的给他一记记重击。
面对这些考验,有些人熬过去了,生命从此升华,有的人倒在了这个坎上,人生就此终止。
木心属于前者,即便身处暗无天日的牢狱,即便喝的是水池的污水,吃的是变质的食物。
他不是没想过离开人间,只是在他看来,死是这人间最容易的事,活下去,活下去才有无限希望。
他会偷偷藏起交代信剩余的纸和笔,在狱中写诗,诗中没有涕泪控诉,没有抱怨不公,有的,是他这些年来对文学的思考和对生活的感悟。
那些纸张密密麻麻,细小缝隙中都是他的心血,就这样,在监狱的黑夜里,他偷偷写下了足足65万字。

后来,即便第三次被捕入狱,他也依旧乐观。
他会趁着其他人熟睡的夜晚,在白纸上画上钢琴键,在昏暗狭小的地方无声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
他还悄悄绘制了33小幅山水画,在不足巴掌大的纸片上,发散着自己的艺术因子。
画作与音乐,带给他内心的供给和情绪的宣泄。
狱中数年,他靠着文学与艺术活了下来,他在绝望中求生,也在崩溃中一次次治愈着自己。
《晚祷》中,木心这样形容他曾经的经历:
在积水的地牢里,我把破衫撕成一片片,叠起来,扎成鞋底,再做鞋面,鞋面设洞眼,可以结带……金字塔、十字架、我的鞋子,是一回事中的四个细节,都是自己要来的。
死不是退路,死是不归路,不归就不是路,人的退路是“回归内心”。
靠着这样的内心坚持,他走出了那段最阴暗的日子。
想起加缪在书中写下的一句话:
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固执地迎向幸福。
木心就是这样的人,哪怕生命接二连三的将他打倒,哪怕生活的周遭困苦将他折磨的遍体鳞伤,他依旧带着微笑,奔赴下一场岁月山河。
他是一个于绝望中给自己生路的人。

因为入狱,木心这一生所有的的文学绘画作品全部被焚毁了,那曾是他这一生的精神支柱。
很多人都说,遭受这样的坎坷,他一定被打垮了。
可出狱那天,有人前去接他,想看到他饱经沧桑佝偻的身体,却不曾想,他们迎接到的,是一个身穿暗棕色大衣、皮鞋擦的锃亮,腰板挺得笔直的男人。
他优雅地出狱,像是要奔赴一场人间盛宴。
出狱后的他带着深厚的学问,很快名声大噪,他去大学当教授,在美术家协会当秘书长,还成了主修人民大会堂的“十大设计师”。
他却不喜欢这样的虚名,而是带着四十美元前往美国求学。
临走前他对外甥说,脱尽名利心唯一的办法,是让自己有名有利,然后弃之如敝屣。
他做到了,在美国这些年,他在大学做教授,他在哈佛办画展,在《联合文学》的创刊号上发连载小说。
当他开始显露才华时,名与利接二连三向他奔涌,那时候在大洋彼岸的他,走到了大多数华人走不到的高度。
名利双收后,最终,他也履行自己的诺言,真的抛弃了这些身外虚名,回到家乡,安稳地过起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晚年时,有记者采访他:木心先生,您承受的这一切都值得吗?
木心笑着回答:不,谁愿意痛苦啊?
可当痛苦铺天盖地迎面袭来时,谁又能逃避得掉呢?
他于大半生的蹉跎中不断告诉自己:
我学过历史,也学过哲学,我是凭哲学来坚定我的心,凭历史来接受现实的考验,因此当大风大浪过来的时候我很安静,一点不乱。
我觉得只有保存自己的生命,才能够看到以后历史的变化。
所以别人很多事经不起而痛苦,而失去了生命,我还是保存了下来。
在对旁人说起那段经历时,他也能大方一笑: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很多人敬佩他的心胸,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只是,要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不仅要有宽宏的气度,还要忍常人不能忍,坚持普通人不能坚持,如此,才能成就一代名流。

《云雀叫了一整天》中,木心写过一句话:
他的人生似乎就是这样,早年求学时便名噪一时,中年却身陷囹圄,晚年人生大放异彩,只是也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靠着不断的自救与自我洗脑,靠着文学与艺术在内心的生根发芽,他终于让自己走出坎坷波折,摒弃掉内心的不甘,以84岁高龄,谢幕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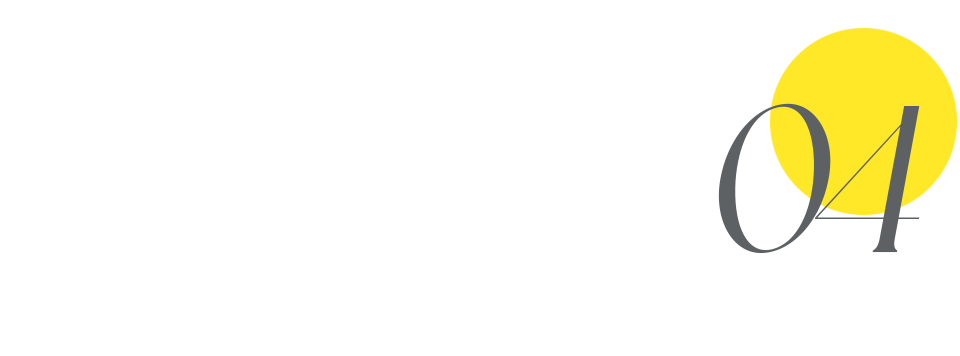
有人曾经评价木心,说他是很忤逆,却也和顺的人。
他特别有个性,一贯特立独行,从童年开始直到终老故土,他都一直很忤逆。
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是和顺的,他从不按照别人的意愿来过自己的生活,顺的是自己的心。
也正是因为此,他能于困苦中自救,于平顺中和解,能在走过半生后还能从头再来,能在声名鹊起后选择复归平静。
他身上有着坚韧的品质,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他是那个曾踏足山巅,也曾落入低谷,却始终情怀不改,初心不灭的人。
很多人都说,做人当如木心,将这周遭的困苦磨难转变为自我成长的沃土,将所有的不公愤恨经由内心生出宽容慈悲,如此,才是真正有大爱的人。
余生还长,其实历数我们的人生,也难免沟沟壑壑,荆棘遍布。
面对周遭打击的唯一之路,就是看轻别人的看法,看淡身上的重担,看清自我的内心,然后,于这最难走的泥泞中,生出自己这一朵花来。
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