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七十,一直浑浑噩噩,没有师承哪一家。这大半是由于我业无专攻的缘故。不过,三人行必有吾师;我这一辈子也确实有不少对我很有影响的师长。在已然作古的人里,至少有三位前辈老先生,在我青少年时期,对我尔后的人生道路有过很深远的影响,这是我不曾、也不应该忘记的。
——陈乐民
不应忘却的记忆
——由“师承”谈起
文|陈乐民
一次,葛剑雄君自沪来京开会,会后到我家来。葛君健谈,两三个小时痛快淋漓。其中有一半时间追忆谭其骧先生的道德文章、仪态风范。葛君是谭先生的得意门生,谨守师教而頗多建树。过去读过几篇他的回忆文章,又看了他写的几本书,深为九泉之下的谭先生感到欣慰。“名师高徒”,古之常情常理。
于是想到了我自己,年近七十,一直浑浑噩噩,没有师承哪一家。这大半是由于我业无专攻的缘故。不过,三人行必有吾师;我这一辈子也确实有不少对我很有影响的师长。在已然作古的人里,至少有三位前辈老先生,在我青少年时期,对我尔后的人生道路有过很深远的影响,这是我不曾、也不应该忘记的。
第一位是我小学时的“国文”老师黄炳臣师。他觉得课堂上的“国文”课内容太单薄,便给我们几个人“吃偏食”,在课外补习,从《孟子》开始。他说,把《孟子》读通了,再读别的就容易了。他不是逐字逐句地讲,也不理会朱注,而是让我们读孟子白文,然后点拨几处,果然就如同剪过蜡烛芯那样豁亮起来了。
我对于“老古董”的兴趣便是从此开端的。后来上大学念的是外国文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又干的是“洋务”(所谓“民间外交”),但是始终没有忘情于“老古董”,以致染上了一些“国学癖”和“历史癖”。这与黄师的启蒙之功是关系很大的。因想,今天再找这样的小学老师,怕不是很容易的了。

朱光潜先生
再一位是从未谋面的朱光潜先生。那是我上了中学的时候,偶然在表哥那里看到了一本《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一下子上了瘾,以后凡是朱先生的书和文章便找来看,几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不料我对美学、哲学的兴趣即由此萌生,而朱先生的学贯中西,尤其使我朦滕胧胧地高山仰止而心向往之。直到今天,我对中西文化的浓厚兴趣,可以说和读朱先生的书有密切的渊源。
然而,我却曾有些对不住我这位没有见过面的“老师”。这指的是,在五六十年代进行思想改造反省“小资产阶级思想”时,我竞说是受了朱先生的书的影响。真是诛心之论呵!“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移情”论,“慢慢走,欣赏吧!”怎么就是“小资情调”呢?可能是说不圆吧,当时即有同伴问我:真是这样的么?后来我在内心里也觉得自己“以时胜道”,不怎么光明坦荡。
再到后来就是“文革”以后了,有一天逛书店,发现了重印的《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急忙买了回来——我存有的朱先生的书,早在“扫四旧”时被收走了——感慨之余,在扉页用毛笔小楷工整地写了这么一段话:
朱光潜先生的《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是我少年时最喜欢的一本书,一些美学里的道理都是从这本书里学得的。解放后入团时,我趋时地批判过去的一切,连这本书和它给我的影响一起都批判了,以后每次需要写“思想总结”时,都照倒批判一番,好像如果当初没有看过这本书,我早就成为一个“无产阶缀”了似的。那种批判实在浅薄、幼稚得可以,今天想起来,仍觉得可笑。
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又在书店里发现了它,頓然感到十分亲切;好像见到了曾经被我委屈过的老朋友。(1988年9月1日)

李一氓
现在该说第三位了,那就是李一氓同志。50年代中期,我离开校门不到两年即被派到维也纳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时经常要向国内写一些报告一类,不少是先由我起草,再由他改定。他改得很快,三下五除二把繁冗拖沓的枝蔓都一概砍去,就像鲁迅说的,把小说压缩成sketch,毫不可惜。
他改后由我抄清,就在这一改一抄之间,我渐渐地悟出了一条作文之道:删繁就简难于锦上添花。写文章,我得益于他不少;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氓公予我的教益,即在于这种日常的熏陶。他兼好中西学问,雅好诗词,写得一手熔甲骨篆隶为一炉的“李体字”,又是文物收藏鉴赏家。我生性喜爱文墨,与这样的领导相处,追随左右,那种徜徉文事的氛围,自然如鱼得水,大大抵消了日常工作的枯燥乏味。
我手头存有氓公的《存在集》、《一氓题跋》;里面有些文章便是他在维也纳时酝酿或起草的,如《花间集校注跋》、《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论程砚秋》等。氓公过世几年后,我拿到了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和诗词集《击楫集》。睹物怀人,不免想到昔时他那无声的教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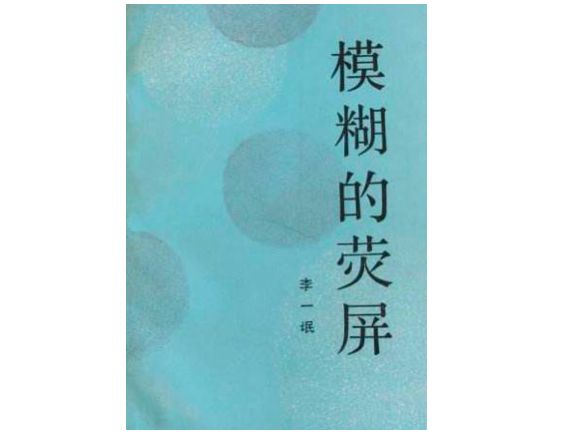
氓公回忆录《模糊的荧屏》
他从不以大道理训人,与小辈相处,谈论诗文,都持平等态度,言谈之间,惠我良多。他曾对我说过一次:为学之道,切忌眼高手低。话虽只这么一句,也只说过那么一次,于我却一生受用不尽!可惜当时我缺乏自觉,失去了不少讨教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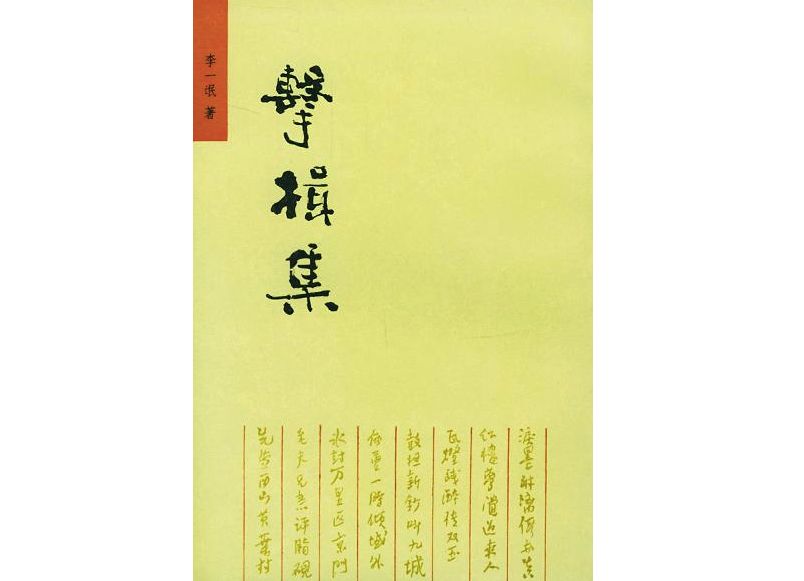
氓公诗词集《击楫集》
我依稀记得,他在维也纳时也偶写些诗词。但《击楫集》里竞付之阙如,想是散失了。《模糊的荧屏》记述维也纳期间事也过于简约。那时中苏分歧已初见苗头,尚不为外界所知;氓公观察敏锐,折冲樽俎之间,语多机锋,每每要言不烦而切中肯綮,深为辩者所折服。氓公在我心目中是既有大将豪气,又有儒家风度;许多有声有色的情景,仍如在目前;然而在《模糊的荧屏》里竞无迹可寻了。我愚顽不灵,加之当时种种禁锢,也无只字笔录,实在可惜!
写到此处,忽然发觉,后两位前辈其实都不能算是我的严格意义上的老师。但是他们确实和我的启蒙之师一样,对我的成长有抹不掉的影响。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尊之为师,不亦宜乎?
进入中年以迄老境,可称我师的自不止此;但对我人生道路起了大作用的,是这三位。这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
扯远了,拉回到引出这篇回忆的开头处,我仍是十分羡慕谭其骧——葛剑雄式的师生之谊。提倡学问,非有师承不可;最要紧的是“尊德性,道问学”的师承。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有创造才能青出于蓝,才能出大学问和大学问家。这样的“师承”,现在似乎不大多见了。所以,我非常羡慕葛君有谭先生这样的老师;同时,我虽谫陋,但在国际政治、中西文化方面总有些零星知识,然而却无后生思意分享,因此我又不免不知高低地妄自羡慕谭先生。
本文选自陈乐民作品:《临窗碎晏》
—END—
阅读更多……
资中筠唯一公众平台

每周一、四 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