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一点
在我工作的布鲁克林的那家酒吧的吧台后面,有一面镜子上贴着这样一张纸条:“规矩一点,不然就叫你吃靴子。(”吃靴子“是俚语,意为”解雇你、叫你滚蛋“。)”(为了使这句话更形象生动,纸条做成了靴子的形状。)有些顾客注意到了,指着它哈哈大笑。也有一些人没注意到。不管怎么说,它是对我们这家酒吧的氛围的很好说明——偶尔,当我感觉到有什么犯规的迹象,如果某人的行为有点越轨,我会微笑着指指那张纸条,然后大声地读出上面那句话。通常,这样就会打破酒吧里的紧张气氛。这里是一个良善、友好的地方,这家小小的酒吧位于布鲁克林一个处在士绅化进程中但仍相对朴素的地区,在绿林公墓附近的日落公园和公园坡之间的边界地带上。我们这儿不希望发生任何麻烦事。我们希望每个人--也包括你--都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大家都能轻轻松松地喝三块钱一瓶的米勒淡啤酒、三块钱一杯的“好时光”波本威士忌。
令人欣慰的事实是: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规矩。我爱我的工作。我在这家酒吧工作的四年里,只发生了极少几件令人唏嘘的惨事,那都是些极端的、反常的案例。有一次,一个神魂颠倒的疯子走了进来,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他嗑了药并且很兴奋,他的 T恤衫上汗渍斑斑,他叫了一杯威士忌,但是没有喝,而是在空荡荡的酒吧里东走西走,同时嘴里还自言自语地念念有词,好像是说有许多人在给他下套:黑鬼、瘸子、好莱坞大亨。都是背叛了他的老朋友。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接着,他又怪异地安静了一会儿,好像是找到了他自己制造的这场风波的平静中心。他直愣愣地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他是死亡天使。“我走进来的时候你的态度很好,”他说,“你会为你的好态度后悔的。”突然,我感觉像是受到了威胁。我们花了很长、很吃力的一段时间,才终于把他赶出了酒吧。不过他说错了:我并不后悔我对他的好态度。我希望每一个酒吧侍者都有好态度,我也希望每一个顾客都有好态度。
像许多酒吧侍者一样,我也会时不时受到一些令人不快的骚扰。我不止一次出面制止过男顾客纠缠对他不感兴趣的女顾客。当然,有时候我也不得不驱逐顾客,给他们吃靴子——不过,是态度友好地。
要想在酒吧里不规矩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不过大部分都是小打小闹。这关乎个人品性,也关乎对待力量与权势地位的不同态度。这些都是我每天会遇到的事,虽然看起来不值一提,但它们不断提醒我纽约人分为两种:从事服务业的,和从事非服务业的。
那么,你还干些什么呢?
我大学里有一个朋友,她爸爸在曼哈顿东区一家老派的意大利餐厅的酒吧里工作了几十年。他的许多常客都是演员,有些经常出现在约翰·卡萨维兹(约翰·卡萨维兹(John Cassavetes,1929-1989),美国电影导演。)的电影里。(也许这是不相关的事,可我就是喜欢福克(彼得·福克(Peter Falk,1927-2011),美国电影演员。)、吉扎拉(本·吉扎拉(Ben Gazzara,1930-2012),美国电影导演、演员。)和卡萨维兹。)总之,这个人,我朋友的父亲,因为在酒吧工作而过上了好日子,在新泽西一个不错的郊区买了一幢大房子,把两个孩子送入了大学。
我想大概是那些演员给小费时出手大方吧。虽然有些事情让我对此表示怀疑。不过,仅靠丰厚的小费是不足以付房贷和学费的。尽管如今酒吧侍者这个行当看上去要比以前体面多了,但我仍旧不相信这是个高收入职业。现在,酒的种类、口味变得越来越复杂,在酒吧工作也许需要更特别的技巧,这份工作似乎还带上了点文化的气息,不过我的感觉却是,以前这份工作更职业化,酒吧侍者靠工资生活,而不是小费。在酒吧当服务生以前是被视为一份真正的职业的,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不需要什么别的手段,然而现如今的侍者们大多有第二、第三职业。
我不记得以前是否有人问过我大学朋友的父亲还干些什么,或者是他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可现在,在我认识的侍者中,没被问过这些问题的人几乎屈指可数。基本上,我每个礼拜最少会被问及一次我还干些什么别的工作。在我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回到酒吧工作的那些岁月里,我在写作方面获得了好运。我的回忆录出版了。我还为一家报纸写专栏。但我听到这个问题时还是觉得很生气,在回答前也总是犹犹豫豫的。因为我觉得“你是干什么的”不是一个该在初次见面时问别人的有趣问题。也因为我自己都很吃惊,我会在另一份职业中取得成功,这对我来说并不怎么真实,对我认识的许多侍者来说也不真实,所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想法。还因为我觉得酒吧侍者本身就是一份了不起的职业,所以我很讨厌“光做这份工作是不够的”这种想法。(有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说我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我没说谎,我在 2002年被任命为宗教部长,在红十字会担任牧师的工作--尽管我几乎不把它当作我的一份工作,因为它会激起各种壮观的反应,但我常常开心地觉得在酒吧服务就像是在行使某种牧师的职责。)
我朋友苏珊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一位酒吧侍者,我喜欢看她工作、向她学习、接受她提供的服务,她也许比我干得更出色。她特别能胡诌,把别人都逗得乐不可支。“如果别人问我:'你真正的工作是什么?'我就会哈哈大笑。”我的耳边仿佛已经听见了她的笑声--那是我们躲在酒吧后面喝酒时的一大乐趣。“我会这样回答,'嘘,我是在 43街和第九大道的街角上站街的。我白天是个牧羊人。我是个修女。我还干掏阴沟的活--只是为了锻炼身体。'”
别的侍者的回答和反应基本上都和我大同小异。我在四十岁的时候做回了侍者的工作,那时我已经有整整十五年没干这一行了。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要重操旧业。不过,当我住的那个街区里新开的这家风格简练、舒适的酒吧的老板问我是否愿意去试一试时,我感觉像是听到了福音。我刚刚成为寡妇,还处在悲哀中。这种失落,再加上我丈夫得了癌症的那两年里的伤心和紧张,使我却步不前,终止了社交,把自己孤立起来。我觉得酒吧老板知道这个,于是出于好心给我送来了一份福音,给了我一个转换心情的机会,让我能够走出自己的公寓,走出我心灵深处的无尽忧伤。它并没能消除我的忧伤——除了时间,别的都不能--但它确实有助于我。至少每个礼拜有一天,我必须起床、洗澡、梳头,和别人交谈。自从弗兰克去世后,我就懒得做这些事。工作既能锻炼身体,又具有社交性--不像写作,是一份久坐案头的孤独职业--这些正是当时的我所需要的。不过,顾客们问我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他们想听这么长一篇故事。那我该如何回答呢?写一篇悼词吗?
* * *
我们之所以从事酒吧服务这一职业都有各自的理由,而有些顾客就是喜欢打听这种事。克里斯蒂原来是在波士顿从事广告业的,但她总向往着来纽约生活。“911”后,广告公司的工作变得更难找了。后来,她在翠贝卡的一家酒吧里参加了一次音乐表演,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一行。(翠贝卡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很想念那里的一家酒吧。我记得那里是一个你能坐下来静静地喝一杯的天堂,去那里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常客,大家都客客气气的,都玩得很开心。)“只有在我碰到一个糟糕的聊天对象时,我才会回想起从前--偶然飘到这里来的某个西装客或某个傲慢的工作狂,他会问我:'那么,你还干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会带给我一连串的恐慌和打击,或者造成我的自信心坍塌。每次听到这个问题都会这样。”
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因为傲慢或自以为是才使得顾客们问出这样的问题。埃文,另一个前酒吧侍者,讨厌“别人对我的生活妄加猜测--说我一定是个学生,或者是丢了一份正式的工作,说我是一个浪子”。不过他又立即补充说:“我想,他们的好奇心和出发点是好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我最近还和一个充满好奇心但本意善良的朋友为此发生过一场争执。我们当时在一起吃午饭,我们俩一致认为那位服务员很滑稽、很可爱。“我真该问问他还干些什么别的工作。”我朋友说。我对她说最好还是不要问。不管提问者是出于怎样的好意,这个问题通常都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你会问一个老师“你还干些什么别的工作”吗?或一位银行职员?或一位编辑?这个问题仅会被用于那些在别人眼里他们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不固定的,反正就是不能算拥有一份真正的工作的人。
谁说了算
酒吧里最好的一点是人人平等。对酒吧侍者来说,顾客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重要。甚至连他们会付多少小费也没你想象得那么重要。多年来,我最喜欢的几位顾客从没给过我很高的小费,但他们却对酒吧文化贡献很大——因为他们温文尔雅,因为他们顾及别人的感受,因为他们风趣幽默,因为他们能讲动听的故事,因为他们也能做个很好的聆听者。这些品格比付多少小费更重要。
到 2013年 12月,对于那些不属于工会组织、拿小费的雇员(包括酒吧和饭店的侍者)来说,现金和小费这两部分收益的最低基本工资涨到了每小时八美元,去年是七美元两角五分。这么低的工资水平势必意味着酒吧侍者的大部分收入都会来源于小费,这同时也造就了这么一种环境:顾客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凌驾于为他们端酒的侍者之上。
在我工作过的两家酒吧,培训时最先被告知的一件事都是:“当你站在吧台后面时,记住你是这里的主人。”酒吧侍者是节目主持人,是派对的东道主,是指挥秀场的人。但对有些顾客来说,权力永远是属于他们的--不管他们给多少小费。
“我有点讨厌那种傲慢的有钱人,他们总是不把你当人看,不尊重你,和你说话时不看你的眼睛,不说'请'和'谢谢'。”特丽,一位经验丰富的布鲁克林酒吧侍者对我说,“同时他们又希望你把他们当作你的老板一样来伺候。”
有一类人是绝不会这样来对待酒吧侍者的: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人们。众所周知,给酒吧侍者最多小费和最好态度的是别的地方的酒吧侍者,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贫富程度都和我们半斤八两。那种拥有权力的感觉往往来自于中上阶层的人、职场白领,就像克里斯蒂和特丽讲的故事里的那些人(他们要为我最不喜欢的一种酒吧现象--我称之为“权力的圈子”——负主要责任。这种现象就是一群西装革履的男人在酒吧中央围成一个圈子,挡住了别人去门口、去厕所、去吧台的路,哪怕酒吧里还有许多空位子,因为他们就是这么任性)。不过,酒吧里的分界线是十分模糊的。我几乎从来没碰见过别的酒吧侍者对我说,他喜欢的一些常客都是有钱人,而不喜欢的都是穷人。通常,分界线来自于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对有些人来说,从事服务业的人就是命里注定要被别人骑在头上的。
还有一个长期在酒吧工作的侍者加里,他也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他跟我说起了他在纽约的第一段工作经历,那是在很久以前的上东区的一家酒吧。“那大约是在 1978年的莱丁斯酒吧,那天酒吧里来了好几个橄榄球队员,这些家伙大多非常有趣,但给小费时都很小气。”他说,“其中有一个人,在喝了几瓶啤酒后准备离开,他把一张一美元的纸币扔进了烟灰缸里。'别这么做,马克。'我对他说。'为什么不行?'他问。'呃,把小费扔进烟灰缸里是不礼貌的,你不觉得吗?'我反驳道,然后把那张纸币从烟灰缸里拿出来,放在了吧台上。'是啊,好吧,如果你想要小费,还是让它待在那里比较好。'他说着,抓起那张纸币又把它扔进了烟灰缸。说完这句话,他转身走出了酒吧。马克既不算穷人也不算富人;在那种情况下,他就是要摆一下谱,来告诉我这里谁说了算。”
加里回忆了这个近四十年前的故事,因为那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一个极端的例子,一次令人难忘的挑衅,一次令人备感屈辱的交锋。大多数场合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站在吧台后面时都不会屈服于这么恶劣的言辞。可是,那种紧张感——谁是这里的主人?谁说了算?——在酒吧里始终存在。
酒吧侍者通常都会至少和几个常客交上朋友。有些人甚至会变得像家人一般亲密,我们会一起去度假,或者在休息日里请他们来家里尝尝我做的菜。如果在我当班的时候这些顾客有事没来,我会想他们的。常客会形成一种相互之间的责任感:顾客会问我日子过得好吗,上班顺利吗,要不要来一杯;而我会去关心他们白天过得如何,家人都好吗,假期过得是否愉快。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会照料他们的猫,反之亦然。在他们领工资的日子,我会很高兴地让他们请我喝上一杯或两杯。但我从来不会去打听他们赖以谋生的职业。我等他们自己来告诉我,不告诉我也可以。
(本文摘自约翰·弗里曼 《双城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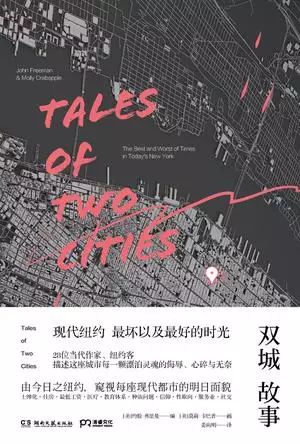
[美] 约翰·弗里曼 / 姜向明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7
这本书是28位纽约客对巨大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的有力反击;通过小说和非虚构报道,记录下生活在纽约的各行各业人士的故事。他们照亮了隐匿于黑暗处的边缘人物的生活,试图寻找这座极度分裂的城市中最后幸存的一点人性:
在这里,你能读到每夜在地道里入眠的流浪汉的命运与传说;士绅化给布鲁克林某个街区带来的沉重压力;被极度边缘化的事务所夜班助理们自娱自乐上演的闹剧;忍无可忍的房客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诸法庭的审判;亿万富翁被困在暴风雪而造成的愤怒一幕;人们走过装饰奢华的宠物店与瑜伽教室,它们讽刺般地开在廉价发廊以及戒瘾诊所旁边。
这本绝妙的、动人的纽约故事集,正是向这座危机中的城市发出的警铃,令人反思大都市的发展前景及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