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 艾哈迈德 · 扎姆罗尼
这片土地唯一执著的事情是:满足五十公里外的巨型工厂的日常需求。要喂饱这些工厂,就需要树木,更多的树木,无限的树木。于是便要滥伐森林,一片土地紧接着一片土地。
我在佩坎巴鲁短暂停留,这里是廖内省(位于印度尼西亚)的首府。
因为附近发现了石油,这座城市开始飞速发展。楼房越建越高,汽车越来越多,却因为交通堵塞,开得越来越慢。新贵们的孩子结婚时,举行的庆祝也越来越气派。某个周日,一个叫丽莉的女孩决定要与埃尔南多一起共度人生。墙上到处贴着他们两人的名字,装饰着各种色彩亮丽的图案,这一切都是用花做成的。
向这对年轻的新人表示过祝贺后,我决定去觐见一下世界最大的造纸工厂之一——英达纸业,它是亚洲浆纸业公司的子公司。
我的正式访问申请被拒绝了,于是,我决定取道西亚克河。花了三百万印尼盾(二百六十欧元)之后,我坐上了一艘六百马力的船。
水是东南亚最仁慈的神。孩子们在里面洗澡,女人们在里面洗衣服,男人们捕鱼,一路上每个人都朝着我们挥手……至于树木,它们似乎在和水流对话。虽然我们的快艇速度很快,但时间却仿佛静止,这里没有四季,因为在赤道上。雨不是刚下过,就是准备要落下。
天空中大大的云团告诉我,我们已经靠近了。这颜色和暴雨将临的天空色彩不同。
忽然,远处出现了大怪物,原来是冒着烟的工厂。紧接着,就是怪物的食物:堆积的树干,高得像个山丘。
沿着河,驳船还在卸下其他的树干,以免怪物不够吃。还有其他几堆,箱子里装满了纸浆(怪物生产的)。沿着浮桥,一列船只正排队等待着将它们运往全球各地。
●
●
●
每隔两百米的瞭望台上都有守卫在看着我们。
我很想再走一程,再看一看整个工厂,好更了解这个庞然巨物,还有它那永不满足的对树木的食欲。
这个请求被船主严词拒绝了。虽然我完全不懂印尼语,但我还是可以理解,我的所作所为不仅过火,简直是没头脑。我没有其他抗议申诉的方法,船主让我下船,我便上了一艘停满货车的渡船,车上装满了树木(经过确认,是洋槐)。
 △
保安说工厂沿岸禁止航行,除非经过允许
图/Beawiharta
△
保安说工厂沿岸禁止航行,除非经过允许
图/Beawiharta
我的脚刚落地,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就走过来。是个保安,或许是有瞭望台通知了他,他提醒我,工厂沿岸禁止航行,除非经过允许。
“你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做。”保安告诫我。
最后,一辆回佩坎巴鲁的车捎了我一程。
我的印度尼西亚之旅开始了。
●
●
●
忽然,一直平坦的路开始向上升起。路上升到一个小山口便平缓下来。从上面看下去,那视野让我无法呼吸,那一刻,我发现了苏门答腊的新主角:油棕榈。占据这大片平原的相似的树,该有几百万棵呢?
这条路让我理解了,在植物的世界中,谁大权在握。其他植被在这里都往后缓。我又看了一眼,几十辆卡车恭敬得仿佛朝臣般运输着这岛上的珍宝,应该是棕榈树的果实,类似凤梨,同样凹凸不平,但更大,更圆,更偏棕色。
为了缓解一下旅途的疲劳,我决定暂时下车,去这片野生丛林中走一走,前面提到的棕榈树让这片森林得以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我们刚走上一条保养很好的路,就遇到了一个简易的野营地。一下子有二十多个人围住了我们,看起来很野蛮,手边拿着大刀。
我们转身就跑,沿原路折回。
“他们是谁?”刚脱离危险,我就问道。
“走私的,走私树木和动物。”
“离大路那么近?”
“只有在小国家才会有高效的警察。”
我们又驶上了无尽的公路,村庄隔着城市交替出现。
然后夜幕降临,一场真正的俄罗斯轮盘玩命游戏开始了。
汽车停下来时,我对到达任何地方早就已经不抱希望了。
我的导游,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当地代表阿菲哈骄傲地宣布:“林布圭亚那,砍伐森林的世界首都!”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论证无懈可击,在印度尼西亚每年生产的七百万吨纸浆中,86%来自苏门答腊岛。1988年,自然森林占这座大岛屿表面积的58%(两千五百万亩)。如今,这部分森林只占不到29%(一千两百万亩)。一个巨大的蝴蝶似乎贴在玻璃窗上听我们讲话。它一直在敲打自己的翅膀,以至于弄伤了右边的翅膀。
“砍伐森林的世界首都”就像是亚洲现代版的美国远西地区,只是清真寺取代了教堂,机车取代了马匹,手机店取代了马蹄铁匠铺。
整齐漂亮的房屋面朝着美丽的花园。车库里停着一辆车,有时是两辆。十来岁的孩子们骑着小摩托放学回来。鹅群、成双的鸭子、拴在木桩上的山羊想要改善伙食……
随处可见的巨大抛物面天线都在告诉人们,这里有高质量的电视设备。
这些村庄的财富从何而来?这里的居民们从砍伐森林中获利了吗?我们的司机阿菲哈为我们揭示了富裕背后的秘密——三叶橡胶树。
为了筹备小说,我在亚马孙待过几周,非常了解这些“哭泣的树木”,这些细长的灰色树干中流出的树脂被做成橡胶制品。
我在一些地方看到过这种植物,但我以为它们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油棕榈。虽然它们在19世纪70年代末来到亚洲时,已经毁了马瑙斯和巴西的整个北部地区,但我还是很高兴看到它们让苏门答腊的人们过上安逸的生活,这里的人既慷慨又好客,充满欢乐又勇敢坚强。
我们离开关丹海滩市已经一个小时了,与其说是开车,更像是在坐船。我们的四驱越野车俯冲、攀越、左右摇晃,像是和凶猛海浪搏斗的船只。虽然我很坚忍,但最后还是对这悲惨不堪的路况感到惊讶。
“运送砍下的树木的卡车走的是哪条路?不可能是这条路吧!”
面对我毫不掩饰的责备,阿菲哈淡然地笑出了声,“去问亚洲浆纸!一个月前开始,他们就禁止自己公司以外的人进入他们的领地。”
“我们可以偷偷去?”
“你还有别的方法吗?”
“要是我被抓了怎么办?”
这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代表看看我,眼神里带着嘲讽,“就当是给你的书做了一次很好的广告,还不错吧?”
身为前任法官、一直严守法规的我,还是没能坚持很久,没能抵挡住孩子气的冲动。与此同时,我们的汽车也停了下来,一条河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仔细地准备着接下去的会面。我们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真正的坏人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漂绿”要求每个企业都仔细地把自己刷成绿色。
●
●
●
亚洲浆纸业公司是金光集团的子公司,属于维查耶家族名下,该家族在印度尼西亚最富有的家族中排名第二或第三。
在造纸行业中,他是全球最大的企业之一。从纸浆到卫生纸,各种产品的全球年产量达到一千五百万吨,销往六十五个国家。2000年时,因为一些清偿方面的过错而从纽约和新加坡的股市中退出。近期又和美国司法部门有新的争议,被判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支付一亿美元。
“亚洲浆纸”在中国拥有一些工厂,但主要生产基地还是在印度尼西亚,在这座苏门答腊岛的中心区域——廖内省和占碑省。这里的动植物多样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大象、老虎、猩猩这些濒临灭绝的物种都在这里共同生活。
二十年里,“亚洲纸浆”滥伐树木。自1984年以来,他们将一百多万亩树林变成了纸浆。在这片开垦越来越广的地方,他们假装也在重新植树造林。按他们的说法,纸浆大部分出自新种的树木。
“谎言”,印尼的环保战士们这样回应。他们在工厂入口处设卡,检查所有进入的车辆,很容易就能从混合热带硬木林中出产的混合木(断面呈红色,原木尺寸也不规则)中分辨桉树的树干和洋槐的树干(新种的树木)。
世界自然基金会最近的计算结果是:在亚洲浆纸工厂中捣碎的树干里,70%来自自然森林。然而,亚洲浆纸还是经常做出承诺:今后他们将只使用100%的人造林树木。但这一约定一拖再拖,从2004年到2007年,再到2009年,现在推到了2015年。根据他们过去的作为,以及他们的产量,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亚洲浆纸也不会遵守这个新的誓言。
亚洲浆纸为什么只伐不种呢?因为,虽然桉树和洋槐生长得很快(五到七年),但砍伐老树则完全不用等。
和绝大多数竞争对手不同,亚洲浆纸是唯一一家持续否认滥伐森林是个问题的企业。因而也拒绝签署保护“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契约。并始终都保持封闭,禁止一切公司以外的人进入他们的领地。
●
●
●
他们的领地就从那里开始,就在河对岸。有人走了过来,他们似乎是在等我们。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这位代表为我准备了惊喜。他告诉我,这些村民一直在和亚洲浆纸斗争。我们握手,微笑,我还以为自己到了拉丁美洲。
他们中有一个人似乎特别有权威。我后来才知道原因,他们这样介绍这个人:“邦德里,他知道所有与土地有关的冲突。”
他们想要带我走。有人指了指他的机车后座,我来不及思考,机车就又开上了一座搭出来的桥——几块有些腐烂的木板摇摇晃晃,从中间的缝隙还能看到下面流淌的栗色的河水。
我徒劳地祈祷他们好好看路,这条沙石小路上到处潜伏着危险的沟沟坎坎,司机还不停地回头看我。我对印尼语一无所知,发动机又不断爆发出噪声,我们的交流很有限,且危机四伏。
每次我们经过一棵树,他就会稍加评论,赞赏之情溢于言表。看到三叶橡胶树竖起大拇指,“好”;看到最近新种下的桉树大拇指向下,“不好”;看到洋槐也一样,“不好”。做这动作的时候,真恐怖,他的右手放开了把手!而我不住地点头,附和着他的“好”和“不好”,表情中也尽力堆满坚定的信心。
此时,他放缓了速度,然后停了下来。我稍稍感到一丝轻松,但并没有持续太久。我的朋友们直挺挺地站着,一言不发,就这么看着。
他不是随便来到这里。他就是要独自来到这里,为他的战斗重新注入信心,或是流下眼泪。
在这山顶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切。
悲剧在延伸,冷酷地径直地发展到悲惨的结局。
第一幕,现在:恐怖,在我们脚下约三百亩的土地上,所有的植被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满目疮痍的红色土地,以及矗立着的惨白的木桩。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棵树孤独地高耸入天空,像是一根毛,很下流。我看到了战场,如同在贵妇小径的战场上。我知道如何分辨出死神的存在。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里。
在这片荒芜的山丘下,应该还有水在流淌。谋杀者们还留下了狭长的一条树林带,让人想起战斗之前的状态。或许那里的坡度太陡,开采、砍伐、运输树干不太容易……
第二幕,未来:在天边外,整齐地排列着绿色的小球,成千上万,都是油棕榈,别无二致,一个独裁者的梦想:将既多样又复杂的植物公司,变为整齐又相似的军队。
我想起了诗人维克多·谢阁兰的预言,弗朗索瓦·密特朗担任法国总统时,我为他起草演讲,并让他说过三次:“多样性在减少。这将是土地面临的巨大危险,我们要为此奋战,即使因此死去。”
在这个噩梦背后,那片在天边刺破雾霭的高地是布吉蒂加普鲁国家自然公园的范围。它们多少次抵挡住亚洲浆纸业公司的欲念?
我所在的这片区域,被划分为“走廊”,也就是说,这片保护区是供大型动物从一片森林去往另一片的,这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保障。他们告诉我一些客观的数字。在整座岛屿上,只剩下145头犀牛、250只老虎。而我们的近亲猩猩的数量在二十年中减少了50%,现在剩下的不超过5000只。
村民们拿出望远镜。他们在监视三百米外两台黄色推土机的一举一动,它们的机械臂末端装着钳子。它们从地上抓起树干,每次可以抓十几根,然后放到某种类似雪橇的滑板上,等卡车来运走。
村民们越来越烦躁不安。
“藏好!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
我觉得好笑,便问:“我们会有什么危险?”
“坐七个月牢,你要是想知道……”
我难以平息看到如此蹂躏与愚蠢的行为后的愤懑,谁能让我相信,我们无法为一片千年的森林找到更好的价值,而只能将它们变为一堆生产卫生纸的纸浆?
此时,我的一个同伴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他指着天空大喊:“直升机!”
瞬间,我们跳上机车,开足马力,逃离前线。
●
●
●
在这一区域,亚洲浆纸拥有一万九千亩林地,而当地村民希望其中保留三千亩供他们耕作。亚洲浆纸丝毫不肯退让,他们辩护说自己有政府的许可,而村民们虽然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却无法提供任何文件证明这是他们的地产。经常会遇到这样难以解决的对立情况,双方都具有合法的权利:一方来自法律,一方来自传统。
“亚洲纸浆”增加了威胁的人力,吓跑那些死守着自己小片土地的人。村民们也相应地予以反击,他们会袭击推土机,放火烧木棚。
我终于知道了邦德里的故事。
在一次交火时,他被警察逮捕。警察总是站在亚洲浆纸一边。
一直沉默的邦德里终于开口了:“或许你可以为我解释这件奇怪的事?我们的总理誓言要和国家的祸害、腐败作斗争。于是,时不时会有部长或是政府官员被问责,尤其是对领地征税的人,他们有些甚至被判入狱。但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领地被取消?为什么从来没有获益公司为此担忧?”
邦德里笑了笑。直到傍晚,他都听由他的同伴们激烈交谈,自己一言不发。只是我离开的时候,他补充了一句:“我知道你是作家,该你说说了。我们不反对纸,但也应该尊重森林。我们还会继续战斗。”
我希望我在表达对他们热情款待的感谢的同时,也隐藏了我对于他们的斗争的疑虑。亲爱而又可怜的机车啊!怎么才能让他们拥有更多权力呢?
我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于是又跳上了车。节奏很慢,声音明显断断续续,让我想起了关于越南的电影。我想我又认出来了。我想装作内行,尤其是在邦德里面前。
“又是直升机!”
我将终生感谢这些村民们没有笑我。他们指给我看,在河岸上,在桥的上游,有一些小屋和一顶蓝色的帐篷。他们只对我说了两句话:“发动机,是个泵。”“那里那种,是用来寻金的。”
我又没忍住犯傻:“不合法吧?”
我的朋友们还是看看别处。
第二天,我又受邀去了另两片领地。因为正式的入口禁止通行,我们又只好“借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路。
第一片领地有五万亩,属于瓦纳穆克提维塞萨有限公司,到处都可以看到巨大的牌子上用白底蓝字骄傲地标示着。我要是他们,就不会这么炫耀。
这些人砍伐森林的目的是要种植三叶橡胶树,他们对砍下的树的经济价值没有直接的兴趣。他们没有卖给造纸厂,那些树木被他们堆在地上挖的洞里烧掉。但火不一定能烧干净,这些被烧得焦黑的树干堆还会继续存在。
较远处的是莱斯塔里阿斯里查亚有限公司的领地,占地七万亩。
这片土地唯一执著的事情是:满足五十公里外的巨型工厂的日常需求。要喂饱这些工厂,就需要树木,更多的树木,无限的树木。于是便要滥伐森林,一片土地紧接着一片土地。因为这些人的目的很明确,所以界限也很明确。我们可能就走在边界上。
右手边,什么都没有,只剩下红色,就像我昨晚看到的满目疮痍,十亩、二十亩或一百亩光秃秃的土地。
这片森林中曾经有动物生活。它们现在只能选择逃跑,以免推土机连同它们一起碾碎。世界自然基金会安装了红外线摄像头用以计算老虎的数量。一号土地曾经有12只,现在全部消失了。

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存。他们被称作奥朗兰巴,意思是“丛林中的人”。
这些人,他们也不得不撤退。和动物们一样,他们也逃跑了。日复一日,他们的领土越来越少。
今天,我们试图和这些族群中的一族接触,但是很难找到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迁徙。从前,他们迁徙是为了找寻新的狩猎场所,如今,是为了避免被挖斗机的巨铲清走。
一个年轻的奥朗兰巴为我带路。他在现实面前妥协,选择去城市生活。但他每周都回来,骑机车五个小时,带回些蛋糕,还有香烟。
他站在卡车的平台上,我找到了他,他正在找能表示自己的部落存在的证据。最后他给我看了一些要晒干的衣服:一条长裤,一件衬衫,一副小号胸罩。
只要沿着小路就能找到。一家人看着我们到来:三个女人,两个男人,十几个小孩,一起坐在他们的帐篷,也就是一块悬挂在树木之间的塑料篷布下。远处是一座简陋的房子,在我看来只是几片随便拼凑的木板,这应该是下大雨时他们躲雨的地方。
●
●
●
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两个小孩,忽然问我:“你是从公路上来的?”
奥朗帮我翻译。我回答是,但我错了,我大错特错,真不该又说这路有多美,有多笔直,又铺着碎石,可以让交流更便利。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女人愤怒的样子。
奥朗只告诉了我一些只言片语,“这条路,诅咒它!它就是那根杀死我们的箭!那些卡车,它们是死神的士兵。一片真正的森林不需要公路,每条公路都是一条伤口……”
这条路,这条伤口,就是一条通往纸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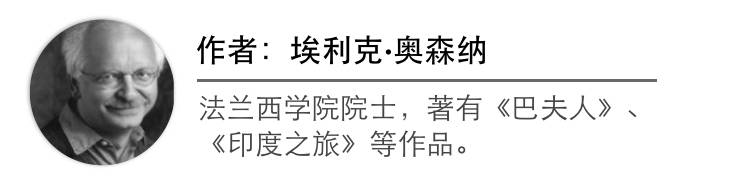

本文选自三辉图书《一张纸铺开的人类文明史》,译者:林盛,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email protected],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网易非虚构写作平台
只为真的好故事
活 | 在 | 尘 | 世
|
看 | 见 | 人 | 间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回复以下「
关键词
」,查看往期内容:
祭毒 |
窥探 | 南航 | 津爆 | 工厂 | 体制 | 马场的暗夜
抢尸 | 形婚 | 鬼妻 | 外孙 | 诺奖 | 子宫 | 飞不起来了
荷塘 | 声音 | 女神 | 农民 | 非洲 | 何黛 | 切尔诺贝利
毕节 | 反诗 | 木匠 | 微商 | 告别 | 弟弟 | 最后的游牧
行脚僧 | 北京地铁 | 高山下的花环 | “下只角”的哀怨
华莱士 | 创业领袖 | 天台上的冷风 | 中国站街女之死
褚时健 | 十年浩劫 | 张海超托孤 | 我怀中的安乐死
林徽因 | 口水军团 | 北京零点后 | 卖内衣的小镇翻译

▼
更多“人间”文章请点击下方“
阅读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