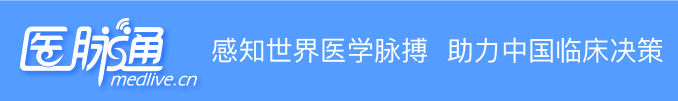
3月28日,南方乳腺癌诊疗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本次大会由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中心主任黄韬教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普外科主任刘强教授、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欧阳取长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乳腺癌单病种首席专家王树森教授
担任主席,各位与会大咖共聚一堂,围绕HER2阳性乳腺癌各阶段治疗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精彩讨论与观点分享。
(专家名称以姓氏拼音排列)
借此次高峰论坛之际,医脉通有幸采访到了
黄韬教授
,以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综合肿瘤科主任熊慧华教授
,
就“HER2阳性乳腺癌的治疗进展”进行分享。以下将本次专访和大会部分精彩学术内容进行分享。
黄韬教授: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辅助治疗的应用与进展

医脉通:并非所有的乳腺癌分子亚型都适合新辅助治疗,而根据CSCO指南推荐,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是可选择术前新辅助药物治疗的。对于这类患者,新辅助治疗有何意义?您在临床中通常会如何选择新辅助治疗方案?这些方案的疗效如何?
黄韬教授:
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临床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让本来不可手术的乳腺癌,通过降期以后变为可手术乳腺癌;第二,让原本不可保乳或者保乳有困难的患者,通过新辅助降期以后变成可保乳或者获得保乳的机会;第三,新辅助治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药敏试验,让我们对患者、对肿瘤、对药物的敏感性有一个直观的评价。
此前,HER2阳性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主要采用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而近年来,已有临床试验证明,相较于曲妥珠单抗单靶治疗,曲帕双靶治疗能够大幅度地提高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pCR率。如在NeoSphere研究中,曲帕双靶治疗组的pCR率达45.8%,而单靶治疗组pCR率只有29%(P=0.014)
1
。我们中国的临床试验也证明经曲帕双靶治疗后的pCR率明显高于单靶
2
。
因此,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我们首选的新辅助治疗方案是曲帕双靶联合化疗。
医脉通:新辅助治疗后,仍有40%-60%的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未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non-pCR)。此类患者远期生存较差,后续是否有方案可以改善预后?
黄韬教授:
基于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对于HER2阳性的乳腺癌,如果在新辅助治疗阶段未获pCR,可通过后续的强化治疗进一步降低其死亡率。强化治疗手段包括使用T-DM1。KATHERINE研究证实,与曲妥珠单抗相比,使用T-DM1进行强化辅助治疗,non-PCR患者的复发或死亡风险相对下降50%
3
。因此,对于HER2阳性新辅助治疗后non-pCR乳腺癌患者,指南推荐首选T-DM1作为强化辅助治疗的方案。
医脉通:在辅助治疗阶段,哪些患者是曲帕双靶治疗的适宜人群?对于有高危复发风险的腋窝淋巴结阴性的患者,您认为曲帕双靶是否具有应用价值?
黄韬教授:
具有高死亡和复发风险的患者,都是曲帕双靶辅助治疗的适宜人群。
对于腋窝淋巴结阴性,但有其它高危因素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我们在选择治疗方案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比如受体的状态、肿瘤的大小、有无脉管侵犯、有无癌栓等。对于其中一部分患者,我们依然会选择曲帕双靶。
医脉通: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主要治疗目标是什么?您能否介绍一下当前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一线标准治疗策略?
熊慧华教授:
晚期乳腺癌的治疗目标是延长患者生存,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前对于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国内外指南均推荐采用曲帕双靶+紫杉类药物作为一线标准治疗。这一推荐基于CLEOPATRA试验,该试验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Ⅲ期试验。受试者被分配至曲帕双靶+紫杉类药物组或曲妥珠单抗+紫杉类药物组。最终,双靶治疗的8年OS率达到了37%,双靶治疗组较单靶治疗组中位OS从40.8个月延长至57.1个月
4
。57.1个月的中位OS使患者有了长期生存的可能,所以国际指南将曲帕双靶作为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的标准方案。
而我国研究团队设计的一项桥接CLEOPATRA研究——PUFFIN研究
5
, 将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按1:1随机分配至曲帕双靶+多西他赛组或安慰剂+曲妥珠单抗+多西他赛组。结果显示,双靶治疗组较单靶治疗组中位PFS从12.4个月延长至14.5个月,与全球性CLEOPATRA研究的HR值相同,均为0.69。提示双靶治疗在中国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疗效与全球人群一致,奠定了曲帕双靶方案在我国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中的一线标准地位。
医脉通:对于早期使用过曲妥珠单抗的患者,曲帕双靶是否有应用的价值?在您的临床工作中,是如何选择曲妥珠单抗的再使用人群的?
熊慧华教授:
至今曲妥珠单抗的应用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所以在辅助治疗阶段,大部分患者可能已经使用过曲妥珠单抗。那么如果患者出现复发,曲帕双靶是否仍有应用价值呢?2020年CSCO指南提示,对于这部分人群,依然可以使用曲帕双靶联合紫杉类药物。
符合曲妥珠单抗再使用的人群大致有三类:第一,在既往新辅助治疗阶段,曲妥珠单抗治疗有效的患者;第二,在辅助阶段使用曲妥珠单抗,停药超过12个月以后出现复发的患者;第三,晚期阶段使用过曲妥珠单抗且有效,但因某种原因停药的患者。
近期在2021年的St. Gallen会议上,马飞教授团队发表了一项meta分析的结果,检索了PubMed、ClinicalTrial、Embase等数据库,共纳入5项包括CLEOPATRA在内的随机对照研究数据。结果显示,即使是对于既往使用过曲妥珠单抗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曲帕双靶仍可延长PFS(HR=0.80)和OS(HR=0.76)
6
。因此,对于一部分既往使用过曲妥珠单抗的患者,曲帕双靶依旧是有效治疗手段。
医脉通:对于一线治疗后进展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二线治疗应如何选择?是否有使患者进一步生存获益的方案?
熊慧华教授:
对于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在抗HER2的这条路上,尽管一线治疗遇到了困难,二线继续抗HER2依旧是我们的目标。国内外对于抗HER2一线治疗失败的患者,二线治疗的选择方案有所不同。国外推荐采用T-DM1,而T-DM1的二线适应证在我国尚未获批,所以国内更多的是使用TKI药物联合化疗。徐兵河教授主导的PHOEBE研究,将既往接受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分为两组,一组采用吡咯替尼+卡培他滨治疗,另一组采用拉帕替尼+卡培他滨治疗。结果显示,吡咯替尼+卡培他滨治疗组的中位PFS达12.5个月,而拉帕替尼+卡培他滨治疗组的中位PFS只有6.8个月
7
。
基于EMILIA研究的结果,国外已批准T-DM1作为抗HER2二线治疗的标准方案。该研究将既往接受过紫杉类药物联合曲妥珠单抗治疗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分为两组,一组使用T-DM1治疗,另一组使用拉帕替尼+卡培他滨治疗。结果显示,T-DM1组的中位PFS是9.6个月,拉帕替尼+卡培他滨组为6.4个月(HR=0.65,P<0.001)。这项研究与PHOEBE研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截止目前,PHOEBE研究的OS数据尚未成熟,但是EMILIA研究的中位OS已达到,其中T-DM1组为30.9个月,拉帕替尼+卡培他滨组为25.1个月(HR=0.68,P<0.001)
8
。
我们期待T-DM1二线治疗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适应证能够尽早在我国获批,为我国乳腺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愈她•拨云见日——
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之道
会上,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姚峰教授
探讨了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有待厘清的3个重点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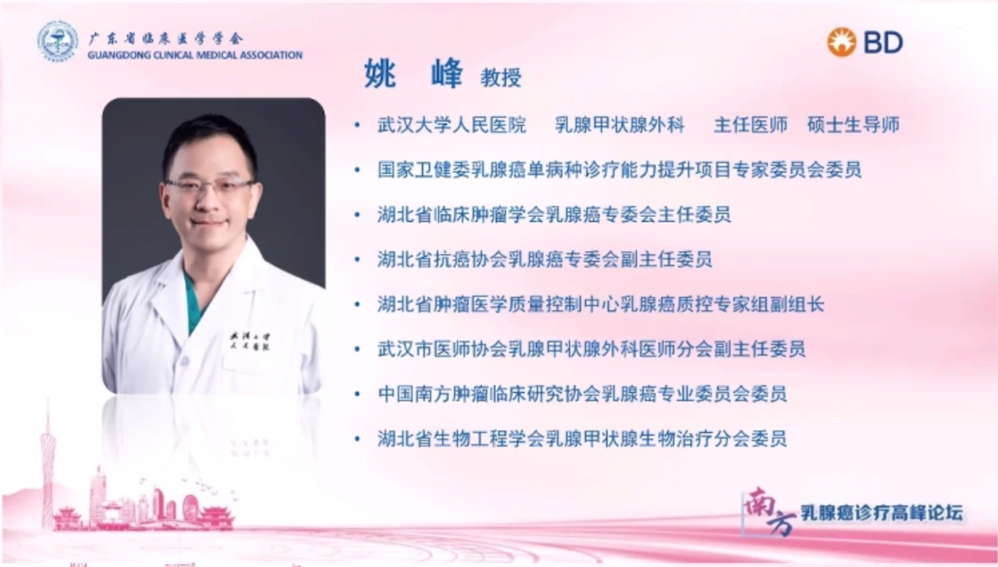
姚峰教授指出,新辅助治疗应以治愈目的为导向,不再仅仅服务于手术。新辅助治疗的适应证不再仅仅依据临床分期,而应结合肿瘤分子分型、临床分期及患者意愿个体化确定。2020年CSCO指南指出,HER2阳性、三阴性乳腺癌(TNBC)为术前新辅助治疗适应证,且仅以HER2阳性或三阴性作为乳腺术前新辅助药物治疗选择的标准时,肿瘤应>2cm;而2021 NCCN指南将cT1cN0纳入新辅助治疗人群,2021 ASCO指南推荐高危HER2阳性或TNBC患者应进行新辅助系统治疗。
姚峰教授认为,
对于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若有一定肿瘤负荷或“降阶梯”手术需求,可选择新辅助治疗。
姚峰教授认为,
HER2阳性乳腺癌初始新辅助“最强”方案为曲帕双靶(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联合化疗。
新辅助治疗应采用可获得更高病理完全缓解(pCR)率的方案,让本来敏感的患者得到更有效的治疗,让本来不敏感的患者变敏感,最终达到治愈的目的。MD Anderson回顾分析、PEONY研究提示,曲帕双靶新辅助治疗较单靶治疗可获得更高的pCR率;而TRAIN-2研究提示,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在曲帕双靶的基础上联合或不联合蒽环对pCR和无事件生存(EFS)并无影响。
姚峰教授解读了大型Ⅲ期研究KATHERINE,研究显示,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病理完全缓解(non-pCR)的患者,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能使其生存获益。他指出,KATHERINE研究提示, non-pCR患者体内有耐药株的存在,需要辅助强化治疗,而辅助强化治疗的成功,源于增加治疗或逆转耐药。根据最新NCCN指南,
对于HER2阳性患者,无论HR状态如何,若新辅助治疗残存病灶,推荐T-DM1单独治疗14个周期。
姚峰教授建议,对于新辅助治疗有效的患者,应完成足疗程(至少6疗程):若患者达到pCR,则辅助曲帕双靶满1年;对于non-pCR患者,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可辅助T-DM1强化。而对于疗效不佳的患者,需考虑尽早手术,术后辅助EC方案(阿霉素类+环磷酰胺)等。
愈她•乘胜追击——
淋巴结阴性、HER2阳性乳腺癌的辅助治疗
广东省中医院陈前军教授
在会上探讨了淋巴结阴性、HER2阳性乳腺癌术后辅助治疗是否有必要使用曲帕双靶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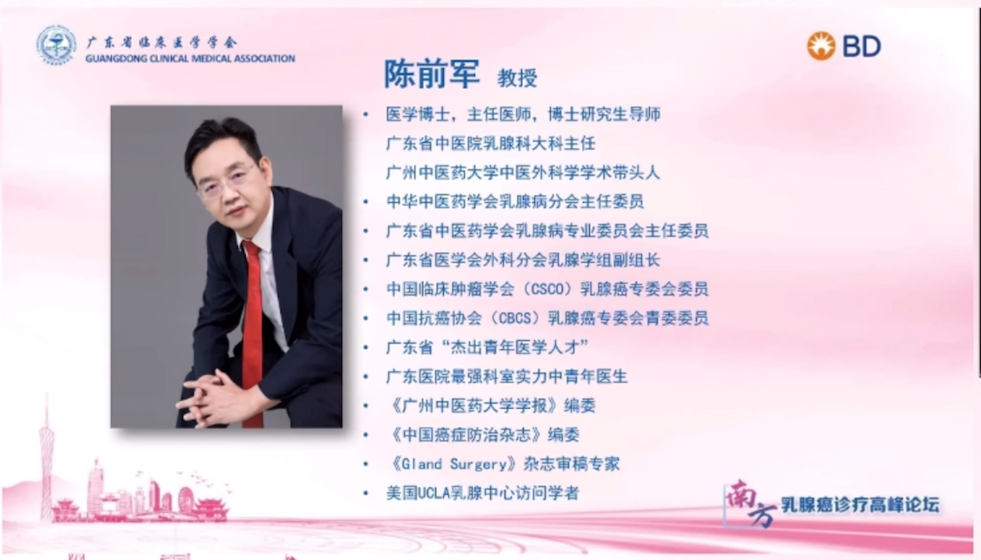
陈前军教授首先指出, APHINITY研究的6年iDFS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曲帕双靶辅助治疗使淋巴结阳性患者的6年DFS率提高了4.5%,而淋巴结阴性患者的6年DFS率绝对提高几乎为0%。针对这一结果,他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过多较低危人群的纳入“稀释”了淋巴结阴性患者的获益。陈前军教授认为,并非所有淋巴结阴性、HER2阳性乳腺癌均不需要曲帕双靶。随后,针对这一观点,陈前军教授分别从治疗获益与治疗损害角度,对以下3个问题展开了论述。
陈前军教授表示,曲妥珠单抗治疗老年乳腺癌(年龄>66岁)患者的分析显示,药物相关心脏毒性与高龄(年龄>80岁)、心血管疾病、曲妥珠单抗每周疗法有关,但与淋巴结状态无关;APHINITY研究显示,曲帕双靶并未显著增加心脏安全问题。因此,陈前军教授认为,淋巴结阴性并
不影响
抗HER2治疗的药物毒性。
陈前军教授指出,
曲帕双靶治疗敏感性取决于分子生物学行为,而与淋巴结状态关系不大。
曲妥珠单抗单靶治疗后,淋巴结阴性患者的复发风险如何?
陈前军教授指出,B31/N9831研究10年数据显示,淋巴结阴性、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经1年曲妥珠单抗治疗后,10年DFS累积风险均超过10%(HR+:10.94%;HR-:24.94%),意味着这部分患者单用曲妥珠单抗仍存在较高复发风险,可能需要曲帕双靶治疗。
陈前军教授总结道,对于
淋巴结阴性、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若存在较高复发风险,仍有必要使用曲帕双靶辅助治疗。
而如何运用传统预后指标鉴别出高风险人群,值得进一步探究。
愈她•持之以恒
——
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治疗进展和决策布局
熊慧华教授
在会中以“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治疗进展和决策布局”为主题分享了她的观点。
熊慧华教授指出,在晚期乳腺癌的治疗当中,OS改善是权威指南推荐的重要疗效考量标准;基于OS获益,
NCCN指南和ABC4指南推荐帕妥珠单抗+曲妥珠单抗+紫杉类作为HER阳性晚期乳腺癌的一线方案。
CLEOPATRA是验证曲帕双靶成为晚期一线新标准方案的关键研究,8年随访结果显示,曲妥珠单抗单靶组中位OS为40.8个月,而曲帕双靶组中位OS达到了57.1个月,且心脏毒性并未明显增加。PUFFIN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曲帕双靶在中国人群中同样具有有效性。基于CLEOPATRA和PUFFIN研究,
曲帕双靶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一线的首选治疗方案。
此外,CLEOPATRA亚组分析显示,对于既往经曲妥珠单抗早期治疗的患者(治疗后无病间期>12个月),曲帕双靶组较单靶治疗疾病进展风险降低38%,死亡风险降低32%。2021 St.Gallen会议上一项meta分析证实,对于既往接受过曲妥珠单抗治疗的患者,晚期一线接受曲帕双靶治疗PFS和OS均显著获益。
熊慧华教授表示,由于T-DM1二线治疗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的适应证尚未在我国获批,中西方在二线治疗的选择中有所差异。
根据EMILIA研究,
T-DM1较拉帕替尼+卡培他滨(LX)显著延长HER2阳性二线患者PFS和OS,且从LX治疗转为T-DM1治疗的交叉治疗患者也可从T-DM1中获得OS改善,而亚组人群的PFS与OS获益同样显著
;此外,T-DM1二线治疗对脑转移患者同样具有疗效,EMILIA研究显示T-DM1较LX显著延长脑转移患者的OS,降低死亡风险62%。PERNETTA研究与TDM1RM研究提示,
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无论一线接受曲帕双靶联合化疗或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进展后均可从T-DM1治疗中获益。
熊慧华教授认为,动物模型显示,在曲妥珠单抗基础上加用帕妥珠单抗后肿瘤再次回缩,证实异源二聚体是曲妥珠单抗的耐药机制之一;
对于一线治疗未使用过帕妥珠单抗的患者,曲帕双靶联合化疗可作为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二线可选方案。
参考文献:
1. GIANNI L, et al. The Lancet Oncology, 2016, 17 (6) : 791-800.
2. SHAO Z, et al. JAMA oncology, 2019, 13(1):25-32.
3. von Minckwitz G, et al. N Engl J Med. 2019 Feb 14;380(7):617-628.
4. Garcia JM, et al. Annals of Oncology (2020) 31 (suppl_4): S348-S395.
5. Binghe Xu, et al. 2019 ASCO. Abstract 1026.
6. Chen S, et al. Poster presentation at St. Gallen International Breast Cancer Conference; March 17-21, 2021. Abstract P059.
7. Xu BH, et al. 2020 ASCO, abstract 1003.
8. Baselga J, et al. N Engl J Med. 2012 Jan 12;366(2):1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