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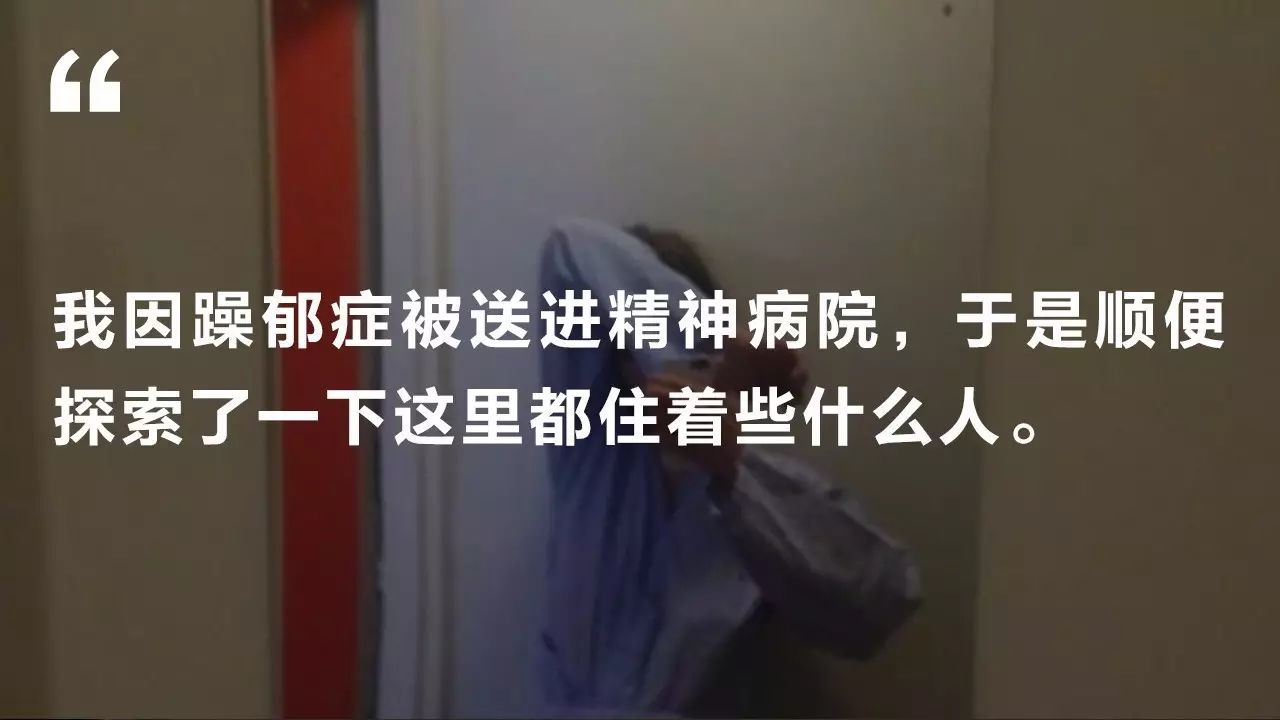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来的医院了。我只记得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房间里,穿着一身不属于自己的睡衣。
几分钟后,我走进公共休息室。一个男正在自言自语地往墙上贴海报。随后我发现,那些海报其实都是信件 —— 寄给上帝、法国总统和蝴蝶。他往电视屏幕上也贴了一张,但正在看电视的医患们好像没太受影响。这里的人没一个穿鞋的,他们要么只穿了袜子,要么光着脚。
一个女人走向我,问我能不能帮她剪一个像我这样的发型。“我一直都想要剪出刘海,” 她说道。
几个人眼睛都直直地盯着电视,但没人真正注意电视节目在讲什么。我听到有人在讨论新出的 MV —— 基本上全是关于法国新晋说唱歌手 Kaaris 的。
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我身边的病友中,有一些人看起来和正常人并无二异。比方说23岁的帕特里克*(Patrick),他因为和警察起冲突,两周前被强行送入了这儿。他长着一头金发,大多数时候都很安静。他的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报纸,而除此之外的其余时间在试图逃离病房。
去年十月的时候,因患有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我几度狂躁症发作,在某个周二的凌晨三点半被送往了巴黎圣安妮中心医院。进去的头两天,我一直昏睡不醒。后来我又磕了瓦利姆镇定药,再后来我决定走出房间来一次冒险,看看精神病院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法国,有大约1200万人承受着心理疾病的困扰 —— 差不多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在4500万法国成年人中,有18.5%被确诊患有某些病理精神病症。2013年,在25岁到34岁之间的法国人当中,有31%遭受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影响。在美国,任何一年,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存在某种精神健康问题。
 活动室里的某种棋牌游戏
活动室里的某种棋牌游戏
精神病院里,一切都遵从严格的时间安排。下午7点10分开晚饭 —— 如果你7点20才到,那就太迟了。我吃的第一餐和后面吃的每一餐都没啥可说的,“咖喱火鸡” 就是汤上漂着很惨的一片火鸡肉。
顺带一提,新来的是不能在餐厅吃饭的。根据医院的规定,如果你刚入院,你就必须要待在自己的单间里,护士会给你拿托盘送食物进来。来的头天晚上,我正吃着,有个女人进到我的房间里,她说:“你要不把饼干给我,我就哭给你看。” 我眼都不眨就把饼干递了过去。
第二天,我穿着蓝色睡衣,除了在走廊里漫不经心走来走去也没干点啥。睡衣是必须要穿的 —— 无疑是为了让我们更难越狱。下楼只能坐电梯,因为通往楼梯的门堵住了。但电梯很吓人 —— 地板上有一摊看起来像血的红色污渍。“我觉得应该是谁把草莓派掉地上了,” 帕特里克这么宽慰我道。
 病人们在看电视
病人们在看电视
每天都要进行各种检测 —— 血液、血压、尿液。镇静剂一般用点滴注射,这样你就不能把药片藏到舌头下面了。工作人员们都很照顾人也很可爱,会听我们叨叨。
我还交到了一个朋友 —— 安托万*(Antoine),27岁,他和我一样患有躁郁症。他坐在我旁边,语气严肃地对我说:“这地方有点像监狱,所以我会罩着你,告诉你哪些人可以一起混,哪些不行。” 我们相处得不错,一起抽烟,玩西洋双陆棋,他还会给我读他自个儿写的诗,他坚信自己是当代的普鲁斯特 —— 而这些都发生在他思路清晰的时候,此刻,他玳瑁色眼镜后的双眼中空无一物。
安托万和我,再加上帕特里克,T* 和索菲安尼*(Sofiane)组了个不错的小圈子。安托万和帕特里克两人都绅士派头十足,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时,他们俩总是会争谁借外套给我披上,也经常逗我笑。我们都曾死里逃生,有时候我甚至恍惚以为,自己只是和两三个好友来夏令营或是度假的。我喜欢这里的一点就是,即使是病得最厉害的患者,也是被当做人而不是怪胎来对待的。
 作者住院时的房间
作者住院时的房间
对安托万的了解越深入,我就越发注意到他的病症所在。他最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一种最对症的治疗方案,然而事实证明他正处于躁狂的最严重阶段。有一次晚饭后,他和我说有 “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我,我最好做好心理准备。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灵媒,能够与灵魂和树木沟通。他还声称自己能变形,成为某种动物。显然他还是耶稣基督的一位门徒,而这位耶稣刚以病房中另一位年轻病患亚伯*(Abel)的身体重返人间。
一开始我觉得他只是在开开玩笑而已,后来我意识到,他确确实实相信自己所说的这番话。我试图劝说他,让他知道他可不是这里唯一一个认为自己能直接与上帝对话的人,而且如果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从这里被放出去,那么对于他自己这一套理论还是想想就得了 —— 当然,他不听。
亚伯,就是被安托万坚信是耶稣转世的那位小男孩,既可爱又古怪。在被说服成功相信自己是二次转世后,他宣称自己能掷骰子杀人。而且据他所说,手掌的那个胎记就是前世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
有一天,他用头猛撞墙,我问他怎么了,他答道:“愤怒。” 由于药物作用,他只能蹦几个词,而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向我吐露了他是艾滋病毒阳性。在他当时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下,医院对采取的治疗手段非常极端,这导致他思维滞缓,产生幻觉。
这里的人们会向别人讲述自己最隐秘的故事 —— 我猜这儿也确实没啥别的可干了。一位年过50的女性告诉我,在过去22年中她都与妻子疯狂地相恋。“我会爱她到永远,” 她说。只要她一出去,她俩就会 “环游世界,正着来,再反着来”。她给我看她们20岁时的照片 —— 两个大美人。
 在医院吃午饭
在医院吃午饭
另一位差不多年纪的女性也常来和我聊天,但她的谈话让我很不舒服,我只好在走廊躲着她走。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她的痛楚。据她所说,她是个女色情狂,因为跟踪某人被送进这里。她告诉我,她 “病态地爱上了” 一个几乎没任何了解的男人 —— 她曾去到对方的工作地点骚扰他,每天都给他写几十封信,还打算一被放出去就立刻去找他。她说如果不和那个男的睡,她就好不了,所以她得知道这个男的每时每刻正在干嘛、在哪、和谁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