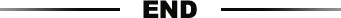我的父亲是一位乡野屠夫,已过四十不惑之年,也曾带着佩剑闯过江湖。父亲下过粤南,闯过浙东,去过内蒙,铩羽归来丢了佩剑也没成佛,却拿起了屠刀专杀牛和猪。
壹
我记得大概是2008年,父亲从浙江回来的时候穿着一双白皮鞋,西装革履,双手插兜倚在家门口的摩托车上和左右邻里讲述着他的江湖风流事,那时我刚好上六年级。
听着他和别人谈笑风生,我猜想父亲兜里应该装了不少人民币。虽然一直到后来我都没见过多少毛爷爷,但到现在却依旧能看见他额头上的那条"蜈蚣"。
这条"蜈蚣"好像是父亲在车间工作钢片断裂时砸在额头上所致,一道伤疤就刚好不偏不倚地留在了父亲的眉心之上,再斜几个角度或许于父亲而言又是另外一种人生。
老板好像并没有给父亲多少赔偿,父亲也便就此远离了江湖之地回到了岳阳的老家。从此,父亲的专职是屠夫,本事是杀猪,武器是屠刀,而猪圈则成了他的江湖。
他偶尔也会杀牛,虽不如庖丁那般"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神乎其技,但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淀后也自成规律和体系。
其实,在父亲回到湖南准备开屠铺的时候,手里应该是有十来万的储蓄,包括舅舅寄存在父亲那里的四万。但钱是一种不安分的东西,又或者说时代的躁动加之凡人本性里面的那种贪婪催化使钱生了手脚,跨过了寒门之槛,最终打了水漂。
2008年,地下六合彩像飓风一样席卷着这个湘北小镇,本分的乡下人突然都发疯似得希望人民币能够一兑四十、百兑千、千兑万,万兑千千万。而其中的种种奇闻趣事又令人啼笑皆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人为了偿还"庄主"的欠款,将银行十万块的存款在五年定期即将当期的前一天全部取出而不带丝毫可惜。
而父亲,偏偏也是其中的之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这十万在短短时间内全部成为了他人的囊中财物。十万不多不少,力度刚好足够扇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像父亲这样的落水者不在少数,即便是幡然悔悟,失去的钱财也不会自己走路回来。因为现实就是这样,有人挖坑,也总有人愿意往坑里跳。换句熟悉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而此时,政府的威信丧失一地也无力控制,于是"难民"们便三五成群地前往"庄主"家逼迫其退还钱款,不退就搬家具,不还就打砸怒骂,一时之间成了当地的舆论风口。
我能回想起来的情节不多,我的记忆之中,大概是很多"庄主"都携妻带子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所以父亲最后也只追回来了四万左右。
前几年我还记得母亲提起过,说那一年的大年初一做午饭的时候,蒸了一锅生饭。按照老一辈的讲法,这是凶兆。不过凶吉也罢,愚昧了的思想神也无力挽回。
父亲结婚的房子是爷爷做的,是306省道旁边的一个小门面。后来,父亲还偶尔感慨说,要是当年不这么沉迷,新房子也早就做起来了。按照当年的物价工价,这点钱在农村做个安居的小屋也八九不离十。
可实际是,父亲在外漂泊十来年,甚至差点陪上命挣来的辛苦钱一下子全部白搭了,不仅做不起房子,还欠了舅舅四万。
近十年过去后,地下六合彩依旧在布衣百姓中盛行,只是当年的疯狂不再,而父亲的那十万却成了后来他那屠刀下的一滴又一滴的猪血。按照每次收取村民一百元的屠宰费来看,父亲要杀一千头猪才能完全挽回曾经的十万房本。
贰
窘境接二连三,高一那年,家里下了一场冰雹,爷爷家的老宅被压垮,所以房子不得不重建。于是2013年的时候,父亲便和大伯一起建了新房。
大伯家当年就搬进了新家,但我们家是旧债未还新账又来。加之肩上还背负我和我弟两个"书生",于是父亲不得不比以前更拼命。
高中放月假的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一般他会提前给我打个电话说要我到伯母家吃饭,我当然不曾也不敢有过任何怨言。因为只要哪里有生意,他就在哪里。
这几年父亲基本上不再卖猪肉,因为卖猪肉一天挣不了几十块钱,而杀一头猪能拿一百的工钱。家乡有杀年猪的风俗,所以一到年底父亲就特别忙也特别拼命。
一到寒假,每次听到他和别人谈起他一天能屠宰6头猪的时候,语气之中都会流露出一股春风得意之感。
刚回家的那段时间,父亲凌晨两三点就会出门,中午也不会回来,可能是觉得回来一趟浪费时间,忙起来的时候接电话也是寥寥几句。忙忙碌碌一直到天黑回到家,一身油腻,衣服上经常有血渍,高筒靴上也总有脱落的猪毛。
这几年至于父亲杀了多少头猪走了多少地方无可计量,我只知道是他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熬过了一个黑夜又忙过了一个白昼。也就是这样一头猪一头猪的,新家的装修也慢慢有了起色。
房子刚刚做起来的时候只有门窗,房间里还堆着水泥和细沙。去年初春开始粉了墙面,贴了瓷砖,装了水电,但还差不少家电,父亲说慢慢来。从春转夏进而至秋,秋再入冬,猪便出圈。
一个寒冬过去,不知道父亲耗费了多少力气杀了多少条猪,但显然父亲手头已经开始活络,于是又开始置办新的家具。最开始只为我添置了新的书桌和床,挂了一幅简便的窗帘,几乎算得上是家徒四壁。
后来又开始新的采购,大概今年夏天父亲就能在新家里和左邻右舍谈天说地。但二楼并没有装修,没钱也没精力,父亲说得等到我结婚。当然那还是非常遥远的事......
3月27日那天,母亲在微信上发来短信说,家里又花了6890元买了一台空气能热水器和50寸液晶电视。大概所有的努力与幸运,都是从点滴之处着手的吧。从当年的北上南下意气风发,到后来的铩羽而归醉于江湖,以及最后的屠刀刚鬣聚少成多,父亲一波三折终于建起了新的宅子。
农村建房几乎不能照着城里人的样子分期贷款,只能这样一头猪一笔钱的积攒着。有时候我坐在父亲的摩托车后座上,突然觉得也不知道是岁月还是房子最终压弯了父亲那挺直的脊背,一丝丝白发以岁月不及之势从头皮上不断地破茧出来,大概也就是那一刻真实地领悟到了"光阴里的人生"。
叁
3月25日早上醒来,我打开微信看到"凤凰读书"推送的征稿启示,看到几位编辑们都在一线帝都打拼,但也依旧为高昂的北京房价所困惑,于是便开始写下我父亲和房子的故事。
在文中看到主编严彬说,2013年他在北京南六环边花了四十万买了一套毛坯旧房。可此刻,南六环的房价大概即将接近或者已经进入4万+时代。照这么换算的话,我父亲要杀4万头猪才能在南六环买下一套100平米的立足之地。
对于世代为农的乡下人来讲,得一亩三分地造一栋乡村小楼房便就是生活。我不能去说父亲和北漂们谁更幸运谁更不幸,因为生活赋予每个人的历练虽不尽相同但终归有命运里的共同。
千人千般苦,苦苦不相同,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每个人的存在都如蝼蚁一样微不足道秒如尘埃。看着父亲为了一栋房子如此拼命操劳,我时常会愧疚十分,大概我的努力永远都难以及父亲的十分之一。
在平淡无常的日子努力地去转变自己命运的轨道,心怀向往并积极改变,不管是谁,大概都会让人永远感动。
写到最后,我想起了贾平凹在《废都》中的一句话:"房子。谷子。票子。妻子。儿子。孙子。庄子。老子。孔子。活了这一辈子,留下一把胡子。"房子重要也不重要,只能说努力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纵使不是任何一次努力都会获得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夹杂在整个过程之中的酸甜苦辣永远都值得我们去回味,这也许就是生活最真实的味道。
责编:笑笑
本文版权归属有故事的人,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阅读更多故事,请关注有故事的人,ID:ifeng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