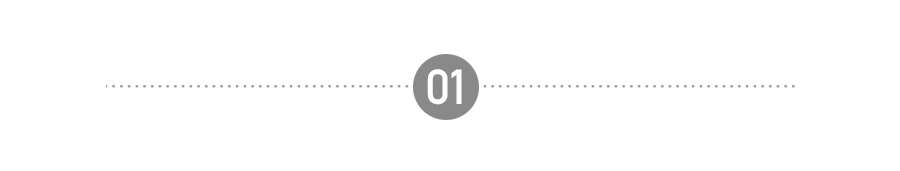
时代的舞台
曹斐是一位蜚声国际的中国艺术家。她先后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当代艺术中心(MoMa PS1)、伦敦蛇形美术馆等地举办个展,接受过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和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重要委约,也曾多次参加威尼斯、莫斯科等地的双年展。
但直到2021年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举办曹斐的个展“时代舞台”时,她的作品才系统且全面地与中国观众交流。2024年年中,曹斐最大规模的个展“潮汐宙合”揭幕,展期从五个月延长至八个月,这也是浦东美术馆开馆以来的首个女性艺术家个展以及首个影像和媒体艺术大展。
如今,当评论者系统性回顾曹斐的作品时,她在家乡广东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被视为整体,UCCA称之为“南方游戏”,浦东美术馆则直接将这个展区命名为“珠三角”。曹斐自称在广州受到的文化滋养犹如自助餐,中餐西餐日韩餐,应有尽有,评论者则这样总结她的创作起点:“曹斐生于广州,成长于广州——这里远离中原,长久以来与外界交流不断,一直是中国最为开放和充满活力的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借助于毗邻港澳的先天优势,广州及其周边的珠三角地区成为加速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前沿和‘特殊的现代化实验室’,这样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条件成为曹斐艺术生涯的起点。”
曹斐1978年生于广州,成长于广州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广美”)的大院,但更吸引她的是大院外的生活。因为父母都是教师,家中的门总是敞开,学生们不断走进家中,曹斐则不断跑出大院,不想再体验美院里经典、雅致的创作。她用“生猛”形容自己的青春,这在广东话中意味着鲜活、充满生命力。
“在广州的青春就是很生猛的,因为四季都可以出门。我觉得热带的衣着、热带的水果,还有活蹦乱跳的海鲜,都很有劲儿,有种即使被压得很低、依然能蹦起来的劲儿。”曹斐说,“我好像天生就很喜欢接地气的对象,美院外形形色色、瞬息万变的人和城市更能刺激到我。”
1999年春节,大学生曹斐拍了个名为《失调257》(“257”是广美昌岗校区的门牌号)的短片,剧本是“飞页”(指在拍电视剧或电影时没有具体的剧本,一边拍摄一边写剧本),演员是留校同学,设备是从她兼职的广告公司借来的索尼掌中宝。那时候她受《阳光灿烂的日子》影响,《失调257》也想表达自我。剪辑上没什么章法,就是体现艺术院校的疯狂生活,比如男女共用一个厕所、在油画室里练气功等等。
这部作品入围了香港艺术中心的大学生影像展,影评人罗卡是为数不多赞赏这部作品的评委之一,他认为《失调257》非常自由,最有生命力。这个小小的大学生电影节,成为曹斐创作的重要出发点。
在曹斐的作品名录中,《失调257》排在第三个,前两个分别是中学时期的表演记录《星星之火II》和在广美时排演的戏剧《校园狂想曲之二》——在无厘头且充满戏谑的剧情中,展露对新兴事物的开放态度和无视所有戒条的前卫姿态。当时,美院教师、广州博尔赫斯书店创办人和“午夜文丛”的策划人陈侗对《校园狂想曲之二》非常感兴趣,看得很认真,完全没有当作一个闹剧一笑置之。也因此,曹斐很想与陈侗分享《失调257》。陈侗看完后,决定为曹斐在博尔赫斯书店办一次放映讨论会,还印刷了小宣传单。1999年底,陈侗把《失调257》拿给了策展人侯瀚如,侯瀚如在次年把这件作品带去了西班牙马德里的摄影展“Photo Espana”。从马德里回来后,曹斐拍了一个另类且充满诡谲气氛的短片《链》,画面参考医学科普电视节目,却传递着令人不安甚至反感的情绪。
在曹斐看来,千禧年前后的广州文化圈充满活力,“广州很自在,四川也是,这样的地方能滋养艺术家。”
“你当时会感觉自己在当代艺术的边缘吗?”
“一点都没有。”曹斐回答得很快,“我没毕业的时候,《失调257》就去了西班牙,后来《角色》只在国内展了一次就被拿到纽约去展出了,《人民城寨》则是直接在国外展出,上了《纽约时报》。”
“但现在回望过去,这也是运气,时代的快车让我越过了一些东西。”曹斐接着说,“当时世界都想了解中国,世界想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会得到额外的关注。”

▲《角色》,浦东美术馆 图/何沛芸
近30年过去,曹斐以“潮汐宙合”作为自己创作生涯的中期回顾。在展览前言中,“潮汐宙合”被解释为不断自我完善和更新的宇宙体系,暗合曹斐开放、包容且持续演进的世界观。曹斐总结了自己的两条创作线索:其一是对虚拟世界、技术、人类在未来状况下的可能性的想象,其二则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交织,人们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节点上,或幽默或残酷或梦幻地去呈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潮汐宙合在浦东美术馆镜厅,摘录曹斐自述 图/谢抒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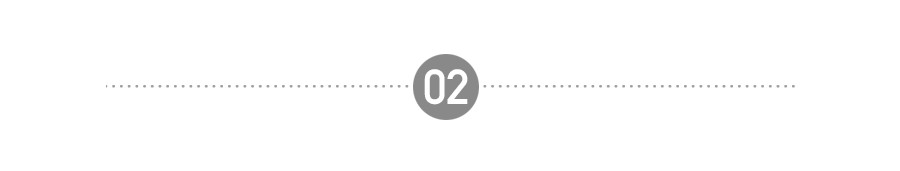
情感
2024年11月28日,曹斐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欢迎登陆》,展览中有一部关于她的大姐曹小耘的纪录片首映。大姐是画家,早年移居澳洲,两年前因病去世。离世前一个月,曹斐对姐姐做了一个长采访,以此为基础,结合姐姐的作品、照片、文献,剪成了30分钟的片子,关于移民的离散和处境。“我剪辑时哭得不行,那么鲜活的一个人。”曹斐说,“但就像所谓咏叹人生无常,其实跟我的其他作品一致,都是处理历史与个体的交织。”
她在展厅里为姐姐设置了一个小房间作为展中展,正中是家庭电视机,循环播放影片,周围环绕着姐姐的画作。这个作品触动了许多观众。
曹斐极少处理这种高度个人化、非社会议题的项目,但她着迷于这其中的浓烈情感。对曹斐而言,艺术就是塑造情感,这些情感或是关联过去,或是连接未来。
“但对当代艺术来说,它的目标不是感动人。感动人是一个很经典的需求,在当代艺术中不是必需的。当代艺术处理的问题更广,可以仅仅是我面前这个对象,也可以是提出问题,是人的处境,是人类的未来。”曹斐说。
《红霞献曲》是曹斐近期情感浓度最高的作品。2023年下半年,北京酒仙桥红霞社区整体拆迁。拆迁间隙,在破败的舞台上,一位身着蓝大褂工人服的歌者拉奏手风琴,献曲《八九点钟的太阳》。悲伤混合着一种开阔的浪漫,情感随着手风琴声扩散开来,裹挟着创作者对一个时代、一群人的温柔。
“我觉得人就是要站在影院的废墟上,我最后就是要留下这个。”曹斐说。
整个“红霞”项目以科幻长片《新星》、纪录片《红霞》以及一本研究文献《HX》为主体,并囊括一件VR作品和一件AR作品、多部纪录短片以及一系列装置艺术。项目始于2015年,曹斐因为旧工作室拆迁,在机缘巧合中租下了北京东北四环外一处年久失修的停止营业的电影院——红霞影剧院作为临时工作室,由此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1950年代中后期,北京东郊在苏联的援助下兴建了718、738 和 774 等军工厂。酒仙桥承载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一度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核心地带。各地年轻人来到酒仙桥工作、定居,工厂也在此建设了工人生活区,催生了红霞影剧院、红霞舞厅等娱乐场所。红霞影剧院由北京有线电厂的员工食堂改建而来,依托社区运营,主要观众都是持有福利电影票的职工家庭,它也因此而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落寞。

▲《红霞献曲》,浦东美术馆 图/何沛芸
解构空间或是再造空间贯穿在曹斐过去20年的创作中,这是她切入中国当代现实的一种方法。2003年,欧宁和曹斐接到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委托创作。十几人举起DV在广州三元里以地毯扫描的方式拍了半年,影片也定名为《三元里》。三元里诞生过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三元里抗英斗争,但在1990年代治安较差,城中村里经常发生各种刑事案件。在曹斐看来,当时这个敏感又混合着历史的空间,正在面对疾速加剧的城市化,城市乡村互相碰撞、传统宗族观念分崩离析。同年,曹斐以《嘻哈:广州》开启了自己的“嘻哈”系列,两年后又完成了戏剧《珠三角枭雄传》。
也是在这一时期,基于海外参展经历,以及侯瀚如在广州做的“三角洲实验室”(D-Lab)项目不断邀请国际知名策展人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后来担任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的设计师)来广东美术馆做讲座,曹斐感觉自己的创作理念被打开了。“很多项目都与建筑、城市规划产生交集,并将研究作为我作品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那时候已经定下来的调性。”曹斐说,“可能我在珠三角的创作原本主要是直觉式的,但库哈斯他们团队进入珠三角做的那本《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让我意识到原来可以这么去理解一个现场,可以这么去理解高速发展的我的故乡,为我后来做《谁的乌托邦》以及《珠三角枭雄传》打下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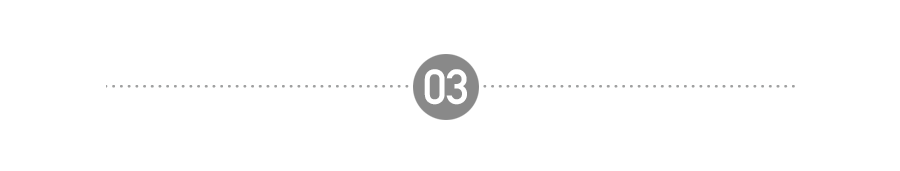
变化时刻
《谁的乌托邦》是曹斐早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2005年底,接到西门子艺术计划的委托,曹斐选择了他们收购的子公司广州欧司朗灯泡厂驻地创作。她在工厂待了半年,发问卷、做采访,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比如上班前会听的歌曲、选择一首歌来代表流水线上的自己、工人们的梦想等等。曹斐从500份问卷中选出了30个工人,在工厂中邀请他们搞艺术、表演文艺。最终,曹斐的镜头注视着在仓库中跳孔雀舞的女工、在机器旁打太极的老工人,以及周而复始、富有效率的流水线,现代化机械与工人的梦想在作品中交替出现。
曹斐注重调研,也重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个人感受。在《谁的乌托邦》结尾,她给了每个工人的面容一个长镜头。“我觉得这个注视很重要。工人生产其实没有太多的尊严,很多工人的纪录片就是要暴露全球化里个人作为螺丝钉的状况。但是每个人五六秒甚至十秒的定格,你就是看着他疲倦的容貌、他的眼神,也是对每一个观众的提问。”

▲《谁的乌托邦》,浦东美术馆 图/谢抒豪
20年后,当曹斐与《南方人物周刊》再次聊到这个作品时,提及一个有趣的现象:她在近几年听到了一些观众对这个作品的批评,认为这个凝视令人不适,仿佛是自上而下的审视。
“当我做《谁的乌托邦》时,社会新闻大多关注工人的问题和制造业的问题,没有人关注工人的脸。过了20年后,这种注视被认为是一种傲慢的凝视。20年后再看这个作品时,是在此时此刻的价值和道德观下看,时间被拉平了。我倒不需要再去解释这个作品,我觉得这就是留下了时代的面容。”
进入工厂的前一年,曹斐在MoMa PS1看到了道格·阿提肯的一个四屏影像作品,展现不同地区不同人的生存状态,屏幕里的人有各样的真实时刻,没有剧情只有状态,她一个人坐在展厅里看哭了。“我觉得人本身就很打动我,我希望我未来的作品也有这样的东西。不是为了打动别人,而是我所表达的是真正打动我的。”
她从阿提肯的作品中领悟到捕捉当代人的现实状态的重要性,也希望与真实的群体产生连接。回到广州后,她完成了《角色》的系列创作,观察了在广州不同场域中的Cosplayers(角色扮装的扮演者),他们做白日梦、打游戏,在城市空间里奔跑行走,最后归家。“我觉得这是最动人和柔软的部分。”曹斐说,“我从那时候真正找到了一种自己很肯定的感觉,对自己的创作语言得心应手起来。”
后来,评论者这样描述《角色》:曹斐探讨了现实与虚拟、社会与个人角色的转变,以及世纪初都市生活急速变化带来的不安。

▲《亚洲一号》,浦东美术馆 图/谢抒豪
如果说创作《谁的乌托邦》始于机缘巧合,那么曹斐2018年完成的《亚洲一号》和《11.11》则完全是她的个人意愿:她感到自己在这个时代必须做这件事。她在京东物流位于上海和昆山的“亚洲一号”仓库和无人分拣中心,虚构了一个物流爱情故事《亚洲一号》:在一座大型的自动化物流基地内,一名女工、一名男工和一个AI机器人共同生活工作。她在其中穿插了一个带有科幻感或者幽默感的爱情故事,以表达哪怕没有人存在了,人类还是需要情感、需要爱。《11.11》则聚焦“双十一”购物节前后,互联网购物背后的运作链条,观察物流和互联网如何支配着快递员渗透进北京的脉络。
“如果说晚两年才拍摄京东物流,其实已经不是对的时间点了。做《谁的乌托邦》也在一个(刚好合适的)时间点,后来我就有意识要抓住时代的转折点,并且把它变成一个长期关注其动态变化的东西。”

▲《11.11》,浦东美术馆 图/何沛芸
曹斐的父亲是雕塑家曹崇恩,创作过许多名人塑像,如《邓小平》《孙中山》《鲁迅》等。2005年,曹崇恩在广西百色创作邓小平纪念雕塑时,曹斐给他拍了一部纪录片《父亲》,观察了体制如何运作以及纪念性艺术工程如何出台。曹斐说,外界一度偏好比较她与父亲的不同,她则更喜欢描述她与父亲的相似:“我们都在处理大时代的东西。我父亲从创作伟人到后来创作社会榜样,比如1980年代在广州与犯罪分子搏斗不幸牺牲的安珂,还有后来创作的抗击非典英雄,也有运动员、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人等等。我觉得我们都对时代性感兴趣,他对时代节点的大人物感兴趣,我对时代的变化感兴趣。或许他是一个主流叙述,我就是一个民间版本。”
曹斐曾以为红霞影剧院被拆迁时,自己一定会很悲伤,一定会哭。但直面红霞被推平时,她很坦然。开启“红霞”项目时,她就知道红霞会消失,她在心中上演了很多次红霞的死亡,无数次想象丢失红霞,想着想着就哭起来,“我在过去经历未来。我当下所做的,都是为了未来。我的未来,就是在过去实现的。”曹斐所做的一切——收集文献、老物件,走访前738厂和774厂的退休职工、红霞影剧院经理、工人后代等等,制作红霞的建筑模型,做VR、AR……都是为了记住红霞、重现红霞,为红霞存档。
或许因为处理了红霞这个庞大的历史项目,也或许因为年长了些,曹斐确切感受到人类在宽广历史中的渺小,艺术家所能处理的就是这几十年的事情。“所有对红霞的表达,我都留下来了,就没有遗憾了。”曹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