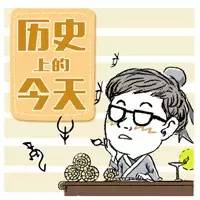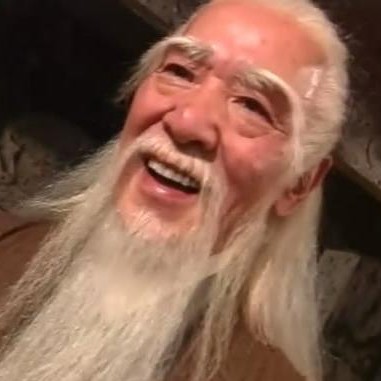我们怎么去对待历史,
未来就会怎么对待我们。
江湖人称老爷子
一头白发的孙冕,
眼看就是奔70的人了,
可笑起来还是那么放肆,
天真得就像个小孩子。
他干起事情来的热血劲儿,
恐怕要甩年轻人一大截。

从《新周刊》背后的大佬,
到登顶珠峰、两创世界纪录的,
极限达人,再到为抗战老兵,
四处奔走、筹捐善款的赤子,
孙冕人生中每次身份的转变,
都是他对内心的一次凝视。
办杂志,是为了实现心愿,
登山是为了救赎自我,
发起“抗战老兵救助行动”,
是身为一个社会人的良知。

1953年,孙冕出生于广东,
15岁,他就完成了一个壮举,
至今还被汕头人奉为美谈。
同乡伙伴去海南岛兵团,
他跟同学一起去送行,
结果船开走了,他忽然说:
“不行,这么送行太不爷们了!”
身边一同学问:“那怎么送?”
只见孙冕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大家跟在船后,游了半天才发现,
潮水已经退了,想回去没路了!
大热天,5个人,什么东西也没吃,
3个人还抽了筋。最后一只泊船离开前,
他们拼命求救,才捡回了一条命。
这事儿听起来虽然莽撞,
但足以看出孙冕的“豪气”。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州,
在《南国戏剧》杂志做编辑,
20多岁就开始了媒体生涯。
1988年,嗅觉敏锐的孙冕,
成功策划了一个广告作品:
《三九胃泰·李默然篇》。
广告中,电影明星李默然,
成为内地首个代言商品的明星。
借着这次打响了名号的机会,
他和导演孙周成立广告公司,
短短几年间,就赚了几百万。

可孙冕并不知足。
他一直都有一个情结,
办一份影响力大的报刊。
改革开放后,全国掀起办报热,
1983年和1987年,
他曾任《百花园》《新舞台》副主编,
因为充满娱乐和话题性,
发行量一度高达百万份。
然而因为太具话题效应,
刊物内容频频被点名批评,
没过几年就被停刊了。
有了数百万的资产之后,
孙冕办报的心就活了过来,
孙周说:“你想办那就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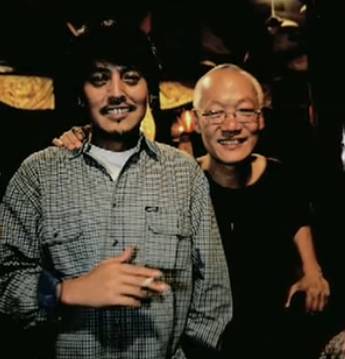
孙冕与孙周
1992年,他和暨南大学,
新闻系合办了《晨报》。
可没有国家刊号,很快被停刊。
1995年,他办周刊《七天华讯》,
办了才七期就没有了下文。
这时候,300万打水漂了。
孙周都劝他:“你这屡战屡败,
还是别搞了,回来拍广告吧。”
孙冕不甘心,听说省新闻出版局,
有一本新杂志,名叫《新周刊》,
刚刚出版正在寻找承办人,
他就天天跑到局里去磨,
磨了大半年,终于,1996年6月,
孙冕拿下了《新周刊》主办权。
当时一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
只能在酒店租房当编辑室,
每天都是花钱如流水。

封新城
通过窦文涛,
孙冕找到了封新城。
这个后来《新周刊》的总编,
是帮孙冕打天下的头号功臣。
从单位出来后,封新城壮志满满,
也真想和孙冕一起把《新周刊》,
办成《时代》那样的巨头杂志。
可1年不到,封新城才发现,
原来孙冕手上根本没什么钱了。
1997年,《新周刊》推出香港回归特辑,
在整个媒体业内引起巨大轰动。
可当时没几个人知道,
《新周刊》已经到了绝望边缘。
那天在办公室里,孙冕和孙周,
当着封新城的面痛哭流涕。
孙周连连摇头说:“我们不是没才,
不是没有人,是裤子口袋太浅了,
我求你停了它,把它卖了吧!”
可最后,孙冕咬牙站了起来:
“不行,杂志已经有影响力了,
不能就这么让它没了。”

香港回归特辑
孙冕能留住封新城,
让他将20年献给《新周刊》,
靠的是交心,是自己的真性情。
当时的版面设计和摄影师,
在《新周刊》拿的是上万月薪。
封新城看到杂志社没钱,
一个月3000块工资也就认了。
封新城之所以这么死心塌地,
是看中了孙冕的人格和品性,
再者,《新周刊》给了发挥空间,
可以让他甩开膀子大胆去干。
尤其是碰到一些重大决策,
孙冕都让封新城自己拿主意:
“我呀,只是个搭舞台的,
戏要怎么唱,你来安排。”
孙冕不止一次当着朋友说:
“一看到封新城做出来的东西,
我就知道没我什么事儿了,
还不如全盘交给他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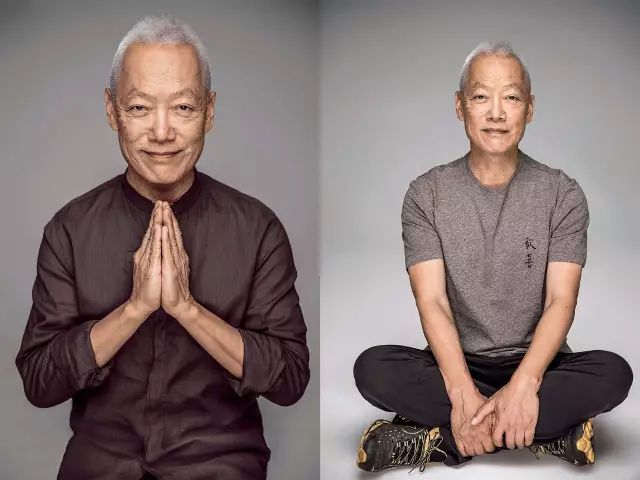
1997年8月,
三九集团为《新周刊》,
注资900万元。同年,
改版的杂志单期发行量,
一度超过了30万份。
2000年,广告收益已达2000万。
弹指之间,20年过去了,
《新周刊》成为国内期刊市场上,
风格最为独特的杂志之一,
凭着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专题,
被传媒界称为“观点供应商”。
无论从封面还是内容设计,
每一期都叫人耳目一新。
即便是面对电子媒体冲击,
仍旧保持着独立姿态,
丰富着读者们的心灵。
很多人问孙冕:
“碰到最困难的时候,
为什么你还会走下去?”
孙冕说
:“你总是要活着,
生下来这一天你就知道要死,
难道你会因为知道你要死,
就选择不去活着了吗?”

《新周刊》奠定地位后,
孙冕直接把它甩给了封新城,
开始琢磨自己的人生之道。
2003年,《新周刊》在哈巴雪山,
举办了一次攀峰活动,
社长孙冕无意中去凑了个热闹,
正巧和王石住在一个帐篷里。
王石酷爱登山,他就特别不理解:
一个大老板,干嘛非执迷于这个?
让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
从5396米的哈巴雪山下来后,
孙冕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之后的孙冕,疯了魔一样,
先后攀登了一系列的高峰,
简直是停都停不下来。
全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
他已经麻利地登了个遍。
尤其是在2010年5月17日,
孙冕挑战从北坡登顶珠峰。
珠峰北坡和南坡相比,
路线长、岩石多、风更大更急,
连飞鸟想过去都没那么容易。
英国人曾用17年都未能登顶成功,
但是57岁的孙冕做到了!
因此还创下两项世界纪录:
全球从北侧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华人!
全球杂志创始人中,
唯一把自己杂志旗帜,
插上珠峰之巅的人!


每一次登山,
都是一次心灵之旅。
其中的困难、危险,
让孙冕感受良多,他说:
“登山其实就是一条心路,
有很多的痛苦,不是腿走不动,
而是你的心跨越不过去。”
这个年纪的他,一改往日装扮,
花白的头发,登山服、登山鞋,
笑容不羁、随兴起舞、逍遥自在,
他说:“要让我去一个地方,
花没人摘,酒无人劝,醉无人管,
那就是我最喜欢的状态。
每一次我走险峰上下来时,
都觉得自己宛如新生,
我要更爱我的朋友和亲人,
用最认真的态度对待生活。”
圈里人都管他叫“老爷子”,
62岁,面对《人物》采访,
被问及自己有什么心愿,
孙冕说:
“我不想老,也不想死,
这就是我最真实的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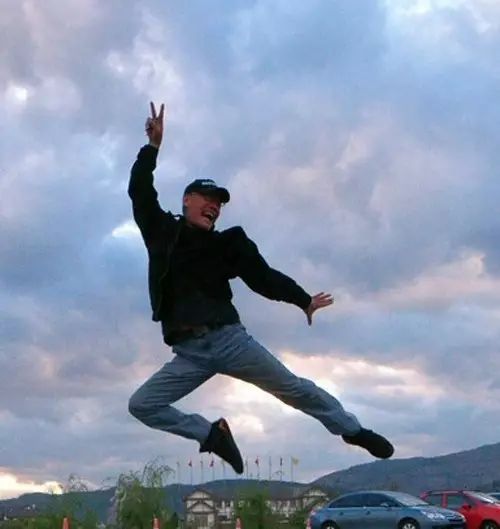
这样的生活没多久,
孙冕的全部注意力,
都被一个特殊的群体占据了,
他们就是“国民党抗战老兵”。
早年,他曾听过一个故事:
一位90多岁的远征军战士,
每月可以领到50或100块钱救助,
有一次,他去领救助金的时候,
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钱没有了,
老人回到孙子家里,孙子见没钱,
当即指着老人破口大骂:
“你这个老不死,
还有脸回家?”
最终,在孙子的辱骂之下,
老人换上了最干净的衣服,
服毒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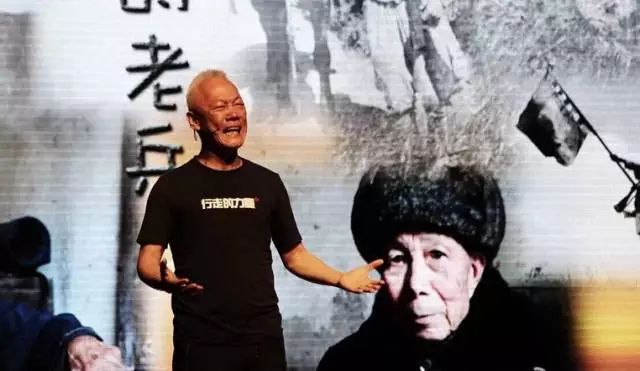
孙冕的父亲是名军人,
曾考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
出于对军人身份的共鸣,
孙冕开始关注“老兵”群体。
2011年底,他联系到一位远征军人,
老人在成都,两个儿子拒绝抚养,
一个女儿又没有抚养的能力。
孙冕便出钱,给老人租房、找保姆。
半年后,老人家去世了,
女儿打电话给孙冕说:
“谢谢你,让我父亲多活了半年,
在生命最后的时间得到做人的尊严。”
就这么一句话,彻底刺痛了孙冕。
此后,他踏上寻访老兵之路,
多方联系志愿者和救助组织,
一脚踏进去,就再也没出来。

在这条救助路上,
孙冕震惊地发现,
这些曾上战场和日本人拼刺刀,
在炮火和流弹中侥幸活下来,
为这个民族奋勇杀敌的一些战士们,
晚年竟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
95岁的卿上先,1937年入伍,
担任重机枪手,用战友尸体当掩护,
和日本人在开封展开血战,
然而20年来无儿无女,
独居在道观中,眼睛被香火熏坏。
92岁的吕先德,黄埔抗战老兵,
战斗中多处受伤,行动不便,
只能借住在一户农家的厨房里。
87岁的杨耀胜,杀死无数日本鬼子,
却在覆满灰尘的窝棚里住了7年,
房子没有窗户,水电不通,
非但如此,他还遭受儿子记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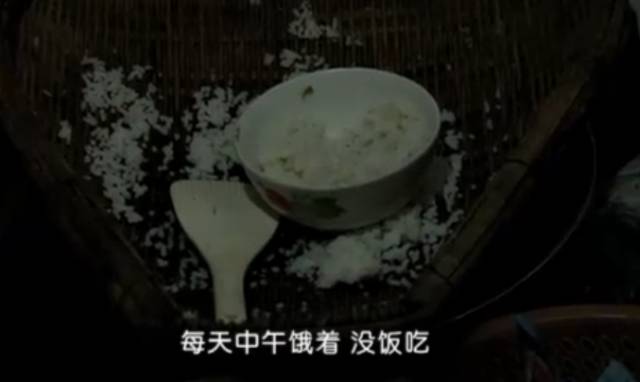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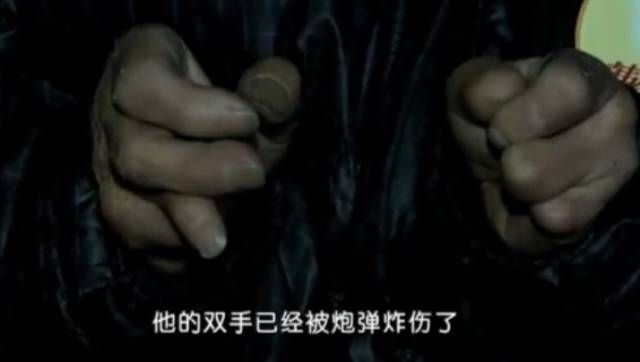
 老人自己挖的水槽,就喝这里的水
老人自己挖的水槽,就喝这里的水
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些老兵们的晚年生活,
可以说惨不忍睹。
有些老兵住在羊圈里面,
一间破草房,没有门窗,
人进去一趟再出来,
浑身都是跳蚤咬的疙瘩。
还有一位98岁的老兵,
自己用石头垒灶烧柴做饭,
残破不堪的家被熏得漆黑,
连床褥、枕头、水杯是黑的。
更有老兵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
自己在门口挖一个大水槽,
靠下雨时积下的污水度日。
这些老兵最年轻的84岁,
最老已经超过了98岁。
因为上战场杀敌,大多负伤,
到这个岁数失去了自理能力,
许多老兵一辈子无儿无女,
即便有了儿女,也因历史原因,
不少人遭受儿女极大的记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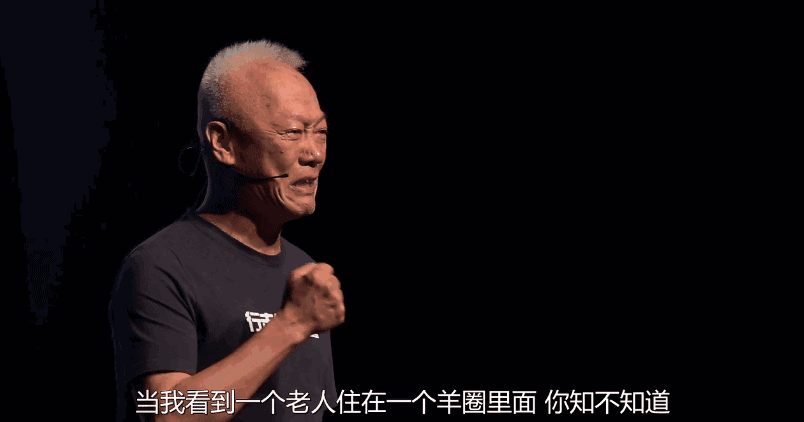
物质上的痛苦,
也许还能默默忍受,
最大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很多老人这一辈子都在等的,
并不是要拿到多少钱,
而是希望能得到一个承认:
“我们当年是去抗日的!
是为了这个民族打仗!”


为了救助这些老兵,
孙冕和志愿者多方呼吁,
他不但自己捐了许多钱,
还拉上明星朋友和圈内人,
积极发动更多人捐款。
这些年,陈坤、韩红等人,
都已多次参与救助行动,
亲自到老兵家中探望慰问。
而每个参与行动的人,
无一不是哭着走完这条路的。
这些老人手脚负伤,行动困难,
多半时候一口热饭都吃不上,
几十年孤独一人生活下来,
精神上从没得到过抚慰。
更残忍的是,志愿者的救助速度,
远远赶不上发现老兵的速度,
更赶不上他们死去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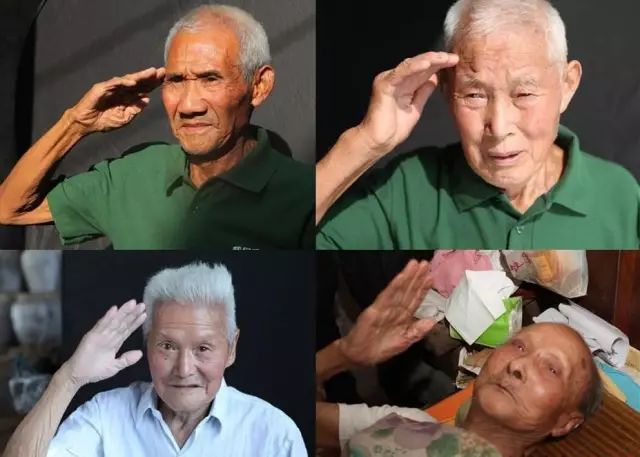
自有登记以来,
2008年走了2个老兵,
2009年走了17个,
2010年走了81个,
2011年走了87个,
2012年走了271个,
2013年走了378个…
孙冕准确地记得这每一个数字,
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
都是一个老兵的生命…
70多年前,国难当头之时,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
我们不该将他们遗忘。
他们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