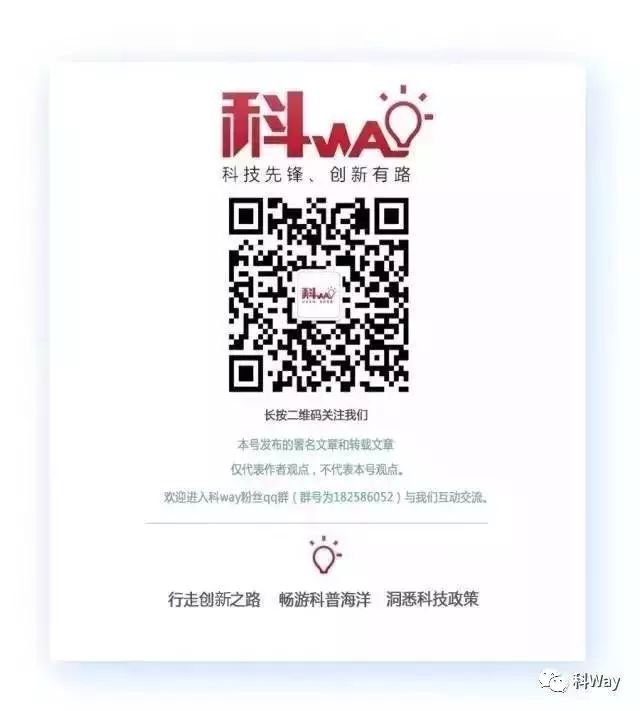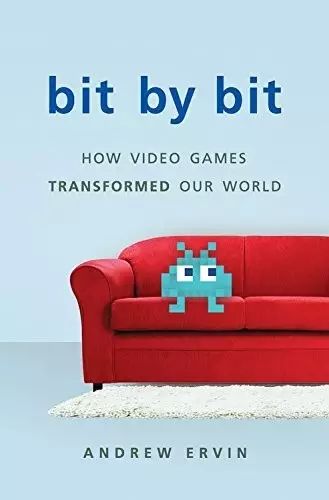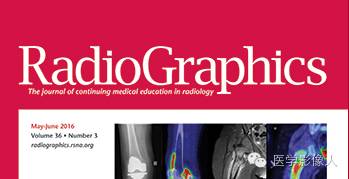文字 |
金婉霞
美编 | 毛毛大徒弟

华东理工大学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里,李辉教授正指导着学生在一个一个仪器前模拟土壤中的分层以及各种元素分布,观察它们遇到各种药剂时的反应。
他们的研究样本来自上海某片老工业园区。
作为上海的化工工业区,该区域内曾经诞生了享誉全国的工业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繁盛时期。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严重破坏,
当地居民说,走过化工区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酸味,每天下班回家污水横流,地上连草都不长。

▲
李辉,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
中国环保产业市场潜力巨大,然而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浮上水面: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老工业企业搬迁、土地置换,历经多次产业转移,我国土壤污染存在新老污染物并存、多种污染物复合污染的特征。
由于历史上的落后工艺和管理不善,其中一些土地很可能已经受到重金属或有机物的污染,危及周边居民的健康,怎么办?
“夏天的时候,我们去现场探测,发现问题非常严重:原工业区的地块已经全被平整了,各个区块的土壤污染很复杂,混杂在一起,原来橡胶厂的土壤、染料厂污染物与土壤被混合后往往难以分辨其本来的元素,现场测量监测会出现测不准的问题。”李辉说。
针对这种情况,李辉和项目组成员发明了有机物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无扰动采集测定方法,可以准确测定污染情况。捕捉所有可疑点,采样移交实验室检测,同时找当地人进行访谈,了解历史情况,在这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才有了初步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其核心区域内,污染土壤类型涵盖了重金属、半挥发性及挥发性有机污染,具有污染类型复杂、污染种类较多等特征。
“这是上海目前最大的区域性棕地治理项目。每个地块的污染特征不同造就了该项目成为近年来国内首个多工艺呈现的污染治理工程。”李辉说。这非常具有我国工业土地修复的典型性。

▲在实验室里,李辉针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修复做了大量的应用基础研究。
上海大规模对土壤进行修复的案例可以追溯到世博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世博园区开展了土壤修复。参与者、现任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付融冰曾回忆:“2002年申博成功后,上海市决定搬迁世博园区内所有企业。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的滨江地带,是上海的老工业基地,也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世博园区确立时,里面有大大小小几十家企业,有的企业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像江南造船厂是李鸿章那个年代建的。在这样一个工业场地里,我们要举办世博会,土壤环境安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外对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2005年起到2008年底,我院会同许多单位进行修复工程,共处置30多万方污染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土壤修复工程,开创了中国城市土地可持续发展的新纪元。”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壤污染和土壤修复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据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在北京、江苏、辽宁、广东、重庆、浙江等地的污染企业搬迁达数千家,已置换相当规模的工业用地,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污染企业搬迁后遗留场地存在着挥发性有机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和农药、重金属污染等污染物不同程度的污染。
重污染场地土壤的修复,就技术层面来说,早已不是问题。
为了解决我国化工场地普遍存在的复杂性问题,李辉和同事们历时10多年,研发出了“化工场地高危害有机物复合污染的风险识别与修复新技术”:针对场地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种类多、测不准的问题,发明了样品无扰动采集和测定技术;针对场地中的高浓度有机物污染,发明了抽出吹脱、高级氧化和尾气催化降解一体化处理技术。对低浓度的有机残留物,或者是用植物、微生物的联合力量来降解,或者是把微生物、活性炭和化学药品制成的降解反应柱插在土壤里,对污染物进行原位降解。这套新技术不仅部分成果被选入相关行业标准,还成功应用到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多个化工场地的有机物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及修复项目中。
李辉说,“虽然我国土壤修复的总体思路依旧沿用国外经验,但修复技术上,我们已经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相信再有一二十年就能赶上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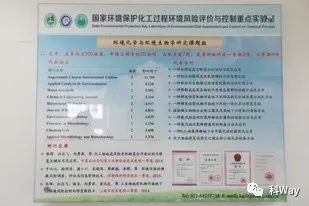
▲李辉实验室专利及获奖情况
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成本。
在《新民周刊》对北京化工二厂项目土壤污染修复案例的调查中显示,虽然该项目披露的总耗资达9.86亿人民币,但因为该项目的地下水环境修复,又曾花费2亿元,所以总花费近12亿元!有媒体评论认为——“这个项目的耗资不仅创下中国目前现有污染场地治理费用之最,在世界上也排名前列。”
2013年5月,世博A片区推出6块地皮,起价是45.6亿元。付融冰认为,当初的付出使得如今的这片土地物有所值。这也隐隐暗示着它的修复成本。
李辉团队探索出一套低成本长期运行的原位修复技术,为在役污染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提供了技术和装备,目前的修复成本已经低于美国。尽管如此,
李辉仍不满足,他认为这套技术的总费用仍偏高。他说:“即使是不严重的污染,每立方米土壤或地下水的修复成本大约仍然需要几千元,根据上海的土层特点,一亩地的修复成本甚至高达数百万元。”
针对上述工业区,李辉课题组首先在实验室中模拟了土壤分部结构,在微观环境中观测污染物是如何分配的,进而从分子水平进一步分析,为药剂的调配提供理论依据。“我们研发了生物表面活剂,它能够促进有机物溶解在孔隙水中,促进其与降解菌的结合。”李辉说,“发明了纳米零价铁核壳结构修复材料,能够把污染物吸附过来,并有效发挥降解作用。”
现在,该工业区域已经拆迁,诺大的场地上几十台高压泵同时往土壤中注入药剂,另一边修复大棚正在进行现场操作,浅层受污土壤在大棚内使用脱毒药剂修复,随后作为路基材料再进行回填。
这里将成为一个示范样本。
自然形成1厘米土壤,需要200年;形成1厘米耕作层土壤,需要200年至400年;形成20厘米耕作层土壤,需要更长时间。土壤一旦污染就是天长地久。而这一切,都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需要产学研携手技术创新,互利共赢,这将成为环保产业的重要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