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杰出的管理学大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亨利·明茨伯格所著的《社会再平衡》一书里提出了社会再平衡这个问题: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严重失衡并且需要根本的革新,核心在于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需要维护好公共、私营和社会三大部门的平衡关系。
个人尤其是私营机构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代表社会力量的社群领域是重构社会平衡的关键。
这可能是一种“冷门”观点,但也不妨一看,社群型企业靠谱吗?
作者 |【美】亨利明茨伯格
编辑 | 郭伟玲
来源 | 正和岛(ID:zhenghedao)
在全球管理界享有盛誉的管理学大师明茨伯格认为,有效的民主能平衡个人、公共与集体的需求,然而我们许多最具影响力的民主照顾的却是个人的需求,包括作为法人的企业的需求。要求政府不能干涉商业事务而商业却插手政府事务是一种扭曲和降格我们社会的虚伪。没有人,更不用说是所谓的企业“法人”,有道义上的权力运用私有财富去影响公共政策。
▌ 不要期待“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奇迹
对于现今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的一些诚实做法,我鼓掌欢迎。但是我发现由一些企业去解决另外一些企业造成的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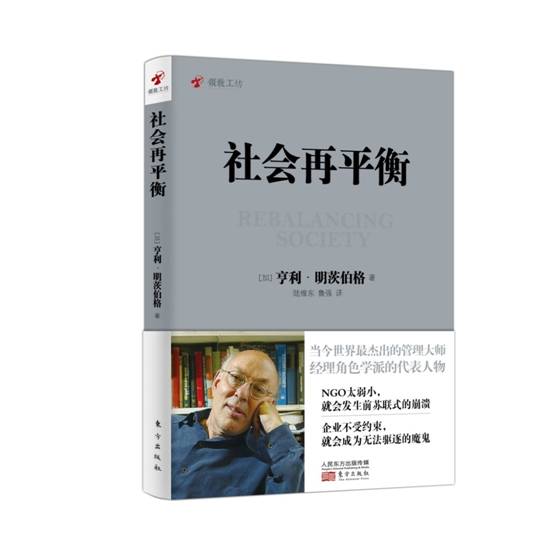
▲ 本文摘编自东方出版社《社会再平衡》,亨利明茨伯格著,2015年9月出版
绿色零售业不能弥补贪婪的污染,就像企业社会责任不能抵消我们触目所及的所有的企业社会不负责任。交易和游说都发生在密室里,而不是企业决策者发表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声明之中。
同样的,让我们鼓掌欢迎那些“做有益的生意又赚钱”的企业,例如安装风力发电机和推销健康食品。但是,我们不要假设通过这些举措就能够以某种双赢的幻境的形式涤荡整个企业界。我们不能允许这些期望将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由纯粹剥削而积累的财富上偏移开去。太多企业通过干坏事来挣钱,也有一些企业干得不错而只是遵守法律条款。
只要没有违法就可以接受(因为政府监管者已竭尽全力追堵,或是因为游说者已经确保他们没有违法),这样的说法也太狭隘了,也会给各种合法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商业可以为了服务于经济市场而存在,而不是去追求社会目标,但他们的确必须为其行为的社会后果担负起道德上的责任。
这可以从游说开始,对于任何真正关注社会责任的高管,我想说:先让你的公司离我们的政府远一点。要求政府不能干涉商业事务而商业却插手政府事务是一种扭曲和降格我们社会的虚伪。在任何一个希望自称民主的国家,没有人,更不用说是所谓的企业“法人”,有道义上的权力运用私有财富去影响公共政策。
▌ 社群领域的运动与行动
如果既不是属于公共部门的政府也不是属于私营部分的企业,那又是什么呢?我相信根本的革新将最先开始于社群领域之中,并通过社会运动与社会行动而落到实处。在这些社区里,人们有意向和独立精神去迎头处理困难的问题。在2013年谈到关于全球变暖会谈的屡次失败的时候,有人问前联合国秘书长科非·安南,“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在需要领导力的时候,如果政府不愿意领头,那么人民就必须站出来。我们需要一场世界范围的草根运动来应对全球变暖及其后果”。
在这里讨论一下根本的革新的三个方面:首先是即刻的反转,运用社会运动以及其他一些形式的挑战去阻止那些不能再忍受的现状;其次是广泛的重建,许多由关切的公民组成的群体来参与社会行动以发展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然后就是当积极响应的政府与负责任的企业意识到需要对结构进行根本调整的时候所进行的后续的改革。
▌ 即刻的反转
在我们通往可持续的平衡的道路上并没有什么权宜之计。与此同时,在它们淹没我们之前,我们必须扭转当下这种非平衡的最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即使不是被洪水淹没,也会是被社会动乱所淹没。
举例来说,我们究竟有多少时间用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50年?20年?10年?从两个方面来说,这是一个有缺陷的问题。第一,它使不作为合理化。假如没人确定具体时间,那我为什么现在就要放弃特权呢?第二,这个问题的提出暗示它似乎会有一个答案,并且我们能够预先知晓。
实际上,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答案,其中有一些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对于那些被前所未有的风暴袭击丧命的人,或者那些生活被无情的裁员摧毁的人来说,答案是没有时间了——现在已经太迟。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答案可能是明年或者几年之后。别指望本世纪中期的宇宙大爆炸,有的只是一路上许多小型的爆炸——但对于受其影响的人来说却是剧烈的,这些是真实的时刻。
很多人将不得不将自己的力量融入那些非政府组织(NGO)当中,它们已经奋斗了多年去监督那些破坏与攫取的权力。它们做得很出色,但问题却变得更糟。它们的努力将不得不依靠一场由众多本地运动组成的大规模的全球性社会运动的支持。
这些努力必须集中并设计巧妙,远非只是提升问题意识。占领了前街然而密室里的交易却依然进行,这有什么用呢?针对特定做法的集中式的行动是需要的。圣雄甘地并未领导一场反对英国殖民印度的运动,而是通过领导了一场反对英国盐税的运动调动了印度人民。
研究一下简单巧妙的策略如何能够战胜庞然大物是很有趣的。
大卫用一个弹弓就拿下了巨人歌利亚。拉尔夫·纳德用一本书《任何速度都是不安全的》将通用汽车公司的考威尔车拉下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受够了公共事业公司,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的市民就每人多付了一美分,这就让那家公司束手无策了。从当地的学校操场到全球市场,一个出乎意料的策略就能令人惊讶地轻松打翻一个大恶霸。因此,除了消极抵制以外,还有聪明的抵抗,特别是当要吸引那些否则不愿意参与的人。
索尔·阿林斯基是发明这种策略来抗衡权威的天才,在他的书《激进分子的起床号》中,他声称自由主义者只是说,而激进分子通过力量和“火热的激情”去行动。他写道,“对手总是比你要强大,所以你必须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制衡他,如果善加激励与指导,现状会是你最好的盟友”。
阿林斯基和纳德的后继者如今在哪里呢?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占领运动,我们同样需要弹弓式的运动,从三个前沿发起挑战:具有明显破坏性的行为、这些行为背后的特权,以及用来合理化这些行为的教条。
▌ 广泛的重建
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发展的不仅仅是它的经济,还包括公民小团体发起的提高生活、强化自由和保护环境等社会行动。
参与到当今的世界大势中去,你会为这些正在开展的社会行动的数量与多样性惊叹。保罗·霍肯的书《神圣的不安》中描述了一场由100多万个参与不同行动的协会汇集成的“运动”。这场运动不“符合标准的模式”。它是分散的、未完成的和极其独立的。这场运动既没有宣言也没有学说,没有高高在上的权威的监督……这是由各处的普通公民推动的一项大规模事业”。这本书长达112页的附录里列举了几百项这种行动计划,包括生物多样性、文化、教育、财产权、宗教等方方面面。但与我们的需求相比较,100万个行动还只是刚刚开始。
只要一点点融入人类智谋的想法,以及打破不可接受的现状的勇气,就可以开始一项社会行动。接着会迎来一个聚焦于学习的阶段,在那期间各种各样新奇的想法被测试是否奏效。正如我和阿泽韦杜曾经在一篇论文中写道,“社会行动……本质上来说是土生土长的:它通过人们集体的参与从内部产生,再向外扩散。他们更多地考虑解决自己共同的问题,而非解决世界的问题,但他们最终发现他们自己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
当然,私营部分在经济类行动上声名卓著,也有许多产生了建设性的社会效应,比如在新型可持续能源领域。同样,不管是社群与私营部分、社群与公共部分,还是社群公共私营三个部分之间,跨部分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只要没有一个“伙伴”控制了这些关系。
霍肯把社会行动的运动大潮描绘成分散的,这个或许是必要的,让百花齐放。但是根本的革新需要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凝聚的力量以达到“集体的冲击力”,将他们联合起来变成一股在各个国家乃至横跨全球的合力。毕竟商业也是分散的,但他们在当地有商会,全球有国际性协会,这样通过联合起来他们就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我心里,最终社会行动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何将许多社会行动整合成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来重新平衡这个世界。并不奇怪,少量的社会行动很难延缓这个世界向非平衡的进发。在许多人推动的所有微观的善行与正在发生的有益少数人的广大的破坏之间存在着鸿沟。
我必须再次指出,我并没有幻想所有这些社会运动与社会行动都是具有建设性的。最好的那些让我们开放并提升,最坏的那些让我们封闭而堕落。但至少前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向前的道路,可以超越许多现存机构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价值。这些由社区和其他协会推动的国际互联的负责任的社会运动与社会行动是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取得再平衡的最大希望。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内容。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