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只知道自己爱唱歌,却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喜欢唱。
有人说过,不要把自己爱好变成职业——我曾在赶去唱歌的路上,无数次想到这句话。
并非厌恶,只是疲惫。所有和艺术相关的事情,在我看来,都需要掏心挖肺,不然会觉得亵渎。我不知道在大理,那一万个酒吧歌手是怎么唱歌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和歌合二为一,不管我今天多么的没有情绪,没有感觉。
也不管,台下是坐满了人,还是一个人都没有。
三场,就是三十首歌,与每首歌合二为一,当然很累很累。可是,与歌分离,或许轻松,但减轻的那一部分,是作为一个歌手的尊严。
因为,无论是一看就很懂音乐的,还是路边卖水果的阿娘,他们看向我的眼神里,我读懂一件事:没有人是聋子,也没有人是傻子。
好听的歌的创作,最基础的因素,都必是由心出发,用感情来凝练。所以想唱得好听,也必须用心。
嗓子可以偶尔沙哑,高音可以偶尔破音,甚至偶尔走音……这些都没有人会责怪,但不用心,哦,也没有人会责怪,他们只会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不管你唱得多卖力,他们会漠然地从你身边走过,像路过一块没有灵魂的石头。
想起21岁在北京的一个酒吧唱歌,那时我咳嗽很严重,睡着会咳醒,醒着会没有间断。
唱歌前惴惴不安,但工作机会难得,只得咬着牙硬上。
神奇的事出现了,在演唱的那半个小时内,一声都没咳。
那天薪水不高,但我背着吉他在回家的路上,边咳嗽边笑,好像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那就是:原来信念,真的可以完成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候唱歌,怕还是有很大的功利心,最大的梦想是在红磡体育场开演唱会,在万人瞩目中成就一生最光彩的岁月。
但现在35岁,深知如此机会实在是渺茫了,留在心中的,只剩纯纯的喜欢了。
现在的客人会说:你唱得很纯粹。

有一天,唱了半小时,酒馆一个人都没有进来。说不心灰意冷是骗人的,这时,我想到了曾淑勤。
这个台湾老牌女歌手,《鲁冰花》的原唱,年轻时唱歌,写歌,也参加央视的青歌赛,但,都没能有大成就。
在她的微博上,我看见她拿着吉他,仍在酒吧里轻轻诉唱,那首歌是《致青春》。
她还在唱歌。
我曾一直笃定地说,唱歌对女人来说,永远是青春饭。或者,一个女人过了三十,还在酒吧驻唱,怎么听都有点凄凉。
但是看见曾淑勤那优游自在的状态,动情的声音,真是看得我羞愧难当。
也是一种警醒:原来,再向往自由的人,都会不知不觉活到自己设置的标签里。
那天,酒吧没有一个客人,街上也没有人,来来回回走得最多的,竟是背着吉他匆匆赶场的年轻人。
想了想,振作了一下,把那颓丧的心拉了回来,拉到了歌里,当我睁开眼睛,台下已静静地坐下了一个人,看着我,听着歌。
曾淑勤在中年时唱的是《致青春》,可她年轻时,唱过一首更好听的《写给年轻》。
其中有一句歌词:
若你来大理,走在人民路上,你会发现,那是一片歌声的海洋。
而我们,就是一条条名不见经传的鱼。

我是想游到深处的那条。
我为什么喜欢唱歌?
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就像你不会去问:鱼为什么喜欢游泳?
那些歌,我曾无比钟情的好听的歌,当每首都唱过100遍,还会有最初的感动吗?
高四那年,有人在讲桌上放了一小盆含羞草,所有苦中作乐的贱人们走过路过,都会拨弄一下,人家含羞草好不容易放开胸怀,还没有享受全然的放松,就被一次又一次吓得合起来。
后来,无论人们怎么拨弄,那含羞草都不会再合起来了。
再好听的歌,听上一百遍,那心弦也不会再震动了吧。
更何况是唱。
台下的游客,每天都是第一次听我唱歌。
可对我来说,我的职业,很像是那株被迫每次都得合给他们看的含羞草。
直到有一天,我唱了那首《一江水》。
这首王洛宾填词的歌,第一次听是一个吉他手推荐给我的,我还记得他说:
他说,多好多好的词啊。
当时我的关注点在“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上,也不管其他词是怎么写的,对这首歌的主观感受,就是乐观的,飞扬的。
可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刚唱了第一句“风雨带走黑夜”,就猝不及防地哽咽了。
这首歌唱了至少也有十年了,却在那一刻,突然真的懂了它的意思。
也自以为懂了王洛宾当时的心境。
当我还没有踏入自己的人生时,路上漆黑一团,没有方向,往往这时,还会时不常来段凄风厉雨,人又迷茫,又冰冷,传说中“风雨之后是彩虹”,那陷在无处可去又无处可藏的感受中时,会产生一种明知很渺茫,但又很执着的希冀里。
因为那是彼时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所以,“风雨带走黑夜”,就是我经历过的,那种不是极度绝望中,就无法诞生的希望。
我跟客人们说:有一首歌,是我认为最适合大理的歌。
是三毛的《梦田》。
初来大理,认识了一些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人。他们的日子里,写满了实实在在的惬意。而也是他们让我明白,惬意并不是不做事,而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付出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所以,他们惬意的质量很高。
有一天工作11个小时的甜点师,有连着两天不睡觉画画的小姑娘,有没日没夜在家练习跳舞的单亲妈……
当然,也有真的种田的。
大理,似乎给了大家一个心田不必荒芜的机会。
我有几个外地朋友,建了一个群。前两天她们说想听我唱歌,我就说我们集体视频吧。
我问她们想听什么歌,她们说都行。
我把手机视频打开,放在铺架上,在酒馆里假公济私地一首一首唱着,她们躺在床上笑意盈盈地听着。
唱了有四首,手机快没电了,我看着她们说: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给我心爱的朋友唱什么呢?
想起闺蜜甲最近婚姻的不顺,工作的压抑;闺蜜乙的抑郁症…地现实的痛苦真枪实弹的打在她们身上,天天说想来大理找我,却日复一日的活在勉强能自圆其说的生活里。
好朋友啊,我唱的这首《梦田》怕也是你们的心声吧?
你们懂我的心意吧?
一般演出结束时,我会唱《送别》,开始时,唱的是《Donna donna》。
这首歌第一次听,是韩国情爱片《密爱》的片尾曲,由于英文很烂,一时听不懂什么意思,但却觉得很悲伤,很愁苦。
当知道这歌的深意后,心中了然,就学了起来。当时的男朋友是个英文老师,他不喜欢听我唱这首歌,说不吉利,问我是不是要离开他,寻找自由?
我无法回答。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潜意识”,很确定的是,彼时的潜意识,远比显现出来的要不羁地多。
追求爱情的年轻女孩,到底追求的是爱情,还是追求自由去爱的权利?
如今说这些时,我也是个有着温馨家庭的中年女人了,那些“追求“的究竟,已好久没再追究了。
但想给自己找一个有意义的开场歌曲时,除了这首歌,再想不起别的了。
这回,我的潜意识想表达什么呢?
不,这次不是潜意识,而是我明明白白的知道,我想表达什么。
像是在目前完美的生活中撕了一个五分钟的时空黑洞出来,从里往外看,常常漆黑,偶尔能恍见微茫的星光。
不光是唱歌的这五分钟,还有写作,跳舞,画画......我让自己在短暂的时刻里尽情纵横在那个时空中,在那里,连自己都找不到。
不管给你多少自由,你只要还有自我,就不可能真的绝对自由。
所以,忘我永远是最高的境界,也是顶级的享受。
只有五分钟,我试着把这个口子撕得更大些,于是每天都在第一首唱它。
这首歌,要下半场唱。因为第一句永远是:我觉得有点累。
唱累了的时候,唱起这句可以理直气壮地带满倦意。

年轻时唱酒吧,最爱这一首。那是寂寞芳心无人慰藉,幻想自己是个深情的歌者,在聚光灯下享受着孤独的舞台,午夜梦回身畔无人,掌声消弭后,看着众人离去的背影,心中一片冰冷的寂寥。
不必在乎我是谁,爱我就好——这句说得不能再多余了,还谈在不在乎呢?根本没人知道我是谁。
我几乎像个隐形人一样度过了理应最好的青春年华。
现在呢,一样的歌声,一样的人,却越来越多人想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是谁。身边也有爱我的人,常常觉得枕头芯里都装满了春风,再唱这首歌,别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感觉到了那种尘埃落定的感喟。
从唱着自己,到纯纯地送给别的渴望爱的女孩。
但是私心把其中一句,终究扣了下来,留给了自己:
以前有个咖啡馆,12点要打烊时,就循环播放张艾嘉的《爱的代价》,到最后,恋恋不舍的客人们,只听见一遍又一遍的“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以致于我每次听别人的店里放这首歌,都会有坐不住的感觉。
轮到我们开咖啡馆时,才知道那些不愿回家的夜归人是多么让人头疼。
我们另一个老板更恶毒,放的是马友友的大提琴。
别说客人了,连我们店里的人都昏昏欲睡。
现在我要唱到夜里11点,每次结束前,我都会很有仪式感地说:下面最后一首歌,是我每晚必唱的ending曲,感谢和你们度过的这个愉快的夜晚。
大家多数很好奇,不知道是什么歌。
我一开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每个人都恍然大悟一般的微笑起来,本能地和我一起唱。
连外面路过的人,哪怕不往酒馆里看,都会下意识地跟着唱。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很有成就感。
酒馆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柔和温馨,像给喧嚣的夜唱摇篮曲一般,一切都逐渐安静了下来。
昨天,大家玩得太高兴,一直让多唱一首。我很动情地唱了客人点的《你的样子》,还没唱完,对面的楼上就响起一阵破口大骂。
实在太尴尬了,我们都还在自我陶醉呢,直接像一盆凉水泼了下来。
我唱歌好听吗?
看对谁了。
对被我们这些酒馆酒吧搞得不胜其扰的本地居民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噪音。
老板连连道歉,把对外的音响关掉了。
我看大家还没有尽兴,就坚持小声地唱完了《送别》。
大家也都小声地跟我一起唱……
场面温馨之余,有点诡异……
唱完了以后,我说:你看咱们像不像地下党?
一首民国味道很重的歌,一首所有人小声且坚定地集体唱完的意味深长的歌……
简直像地下党秘密聚会后在唱国际歌。
来自全国各地的“地下党”们哄地一声笑翻了,大喊着,“像!太像了!”
老板忧心忡忡地望着我们,再望着对面的楼,坐立不安。
我之所以选《送别》,是因为很多客人在大理都是短暂的停驻,往往第二天就要返回家乡。一场又一场的送别,每天都在发生,我感激他们坐下聆听我的声音,时常收获鲜花和掌声,却觉得无以为报。
只有很庄重温柔地唱起这首歌,遥遥相送,一茶一会的际遇谁都逃不过去,转眼,你忘了我,我也忘了你。
再见面,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否还会相认。
都是漫长人生,属于彼此的时刻,也不过短短几首歌而已。
怎么送别,其实都不为过。
也许不记得都有过谁,但,有过这些人的每一个今宵,梦都不会寒冷。
希望我歌声,不管怎样,好歹也是一壶浊酒。
以前写过《性空山》,那是在悄悄纪念一个可能隐隐互相期盼过的朋友。
后来在酒馆里,来了一对小情侣,只要他们在,就一定要让我唱《性空山》——结果,他们几乎每天都来……
所以我对这首歌感情非常复杂,不愿意麻木地唱,所以,经常在想,我该调动什么情绪去唱呢?
首先,这是一首离别的歌。
这也是一首用很多堂而皇之的好听话去掩饰感伤的歌。
最后,这更是一首既看透得过早,但又到死都不愿意承受这看透后的结果的歌。
我用这首歌,送别过很多个离开大理的、挚爱的朋友。
有个弟弟走的时候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留下的人,比走的人难受?
是的,我是那个总被他们留下的人。
我是那个总在难受的人。
可是成年以后,发现难受归难受,眼泪归眼泪。
真不知道,这时因为觉得眼泪更值钱了,还是觉得更不值钱了?
昨儿个,上班前,有个每天都会在酒馆前驻足听我唱一会儿的客人,微信问我:要走了,可否斗胆点首《我要你》?
我很慷慨的说:没问题,还想听什么?
他说:小娟的《爱的路上千万里》。
我说,好。
但这首歌我没有唱过,只能现学现卖。
上班时,不多久屋里坐满了人,他来的时候,只能如常站在门口的花前。
我唱了《我要你》,他走进来,给我递了一根烟,说时间到了,要走了。
我说,《爱的路上千万里》还没唱呢,唱完再走好不好?
不想让爱听我唱歌的人觉得遗憾。他们都是我心里的大宝贝。
因为现学的,唱得并不好,但不重要。
他听完后,对我遥遥作了一个揖,转身急急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本能地唱起了《性空山》。
“送君千里直至峻岭变平川——”
猝不及防的,眼泪瞬间盈满了眼眶。我跟这个陌生人,没有时间“惜别伤离临请饮酒三两三”。
所有离别的场景,像同时进站的几百辆火车,撞进了脑海里,有拥抱的,有接吻的,有哭喊的,有打骂的,有决绝的,有一步三回头的,有泪奔的,有老死不相往来的……
眼泪不受控的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声音到最后一句,已是一阵难堪的哽咽。
店里的客人不约而同的,没有看我,低着头把掌鼓得很温柔,很体贴。
我给他发:给你送别的歌,你听见了吗?
他说:听见了,一念之差,没有回头拥抱你。
我们认识不超过四天,说话不超过五句,在那一瞬间,我们像一别千里遥遥的老朋友、老同学。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第一万次站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在茫茫大雪中,等着远行的火车。
回头,身后没有人送我。

在梦里,我很伤心地哭了,记得自己喃喃地说:我拿《性空山》来送你们,你们唱什么来送我?
谁说走的人,没有留下的人难受?
编辑 | 龚晗倩
点击图片,即可查看相关内容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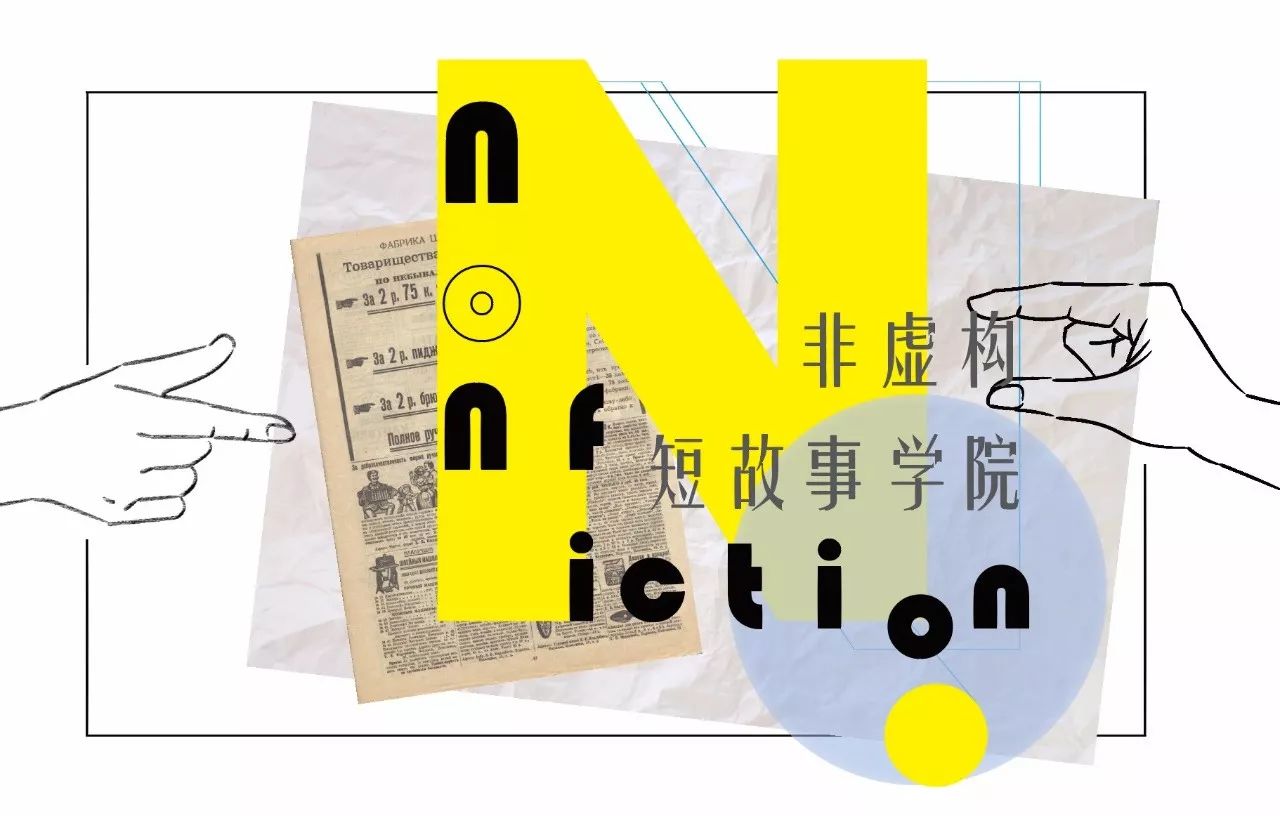
/ 三明治非虚构短故事学院 /
“七日书”的全面改版升级
在这十二天学习写作的过程中,你将拥有一位尽职的“编辑”、“老师”的陪伴
一对一地和你保持沟通,提供修改意见
快来报名,开始提笔写下你的故事
点击图片,了解详情

/ 来三明治杂货铺子,为你的灵感屯书/
三明治微店在年底全新改版
现在下单购买人大创意写作系列丛书,可以享受八折好礼优惠
还有三明治原创布包、T恤可以购买喔
点击图片,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