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闻报道纪录片《看见台湾》台湾导演齐柏林因飞机失事遇难,深感震惊和难过。2014年,齐柏林先生来大陆放映《看见台湾》,我有幸采访过他。现把当年采访的文章发出来,以示怀念。愿齐柏林先生天堂安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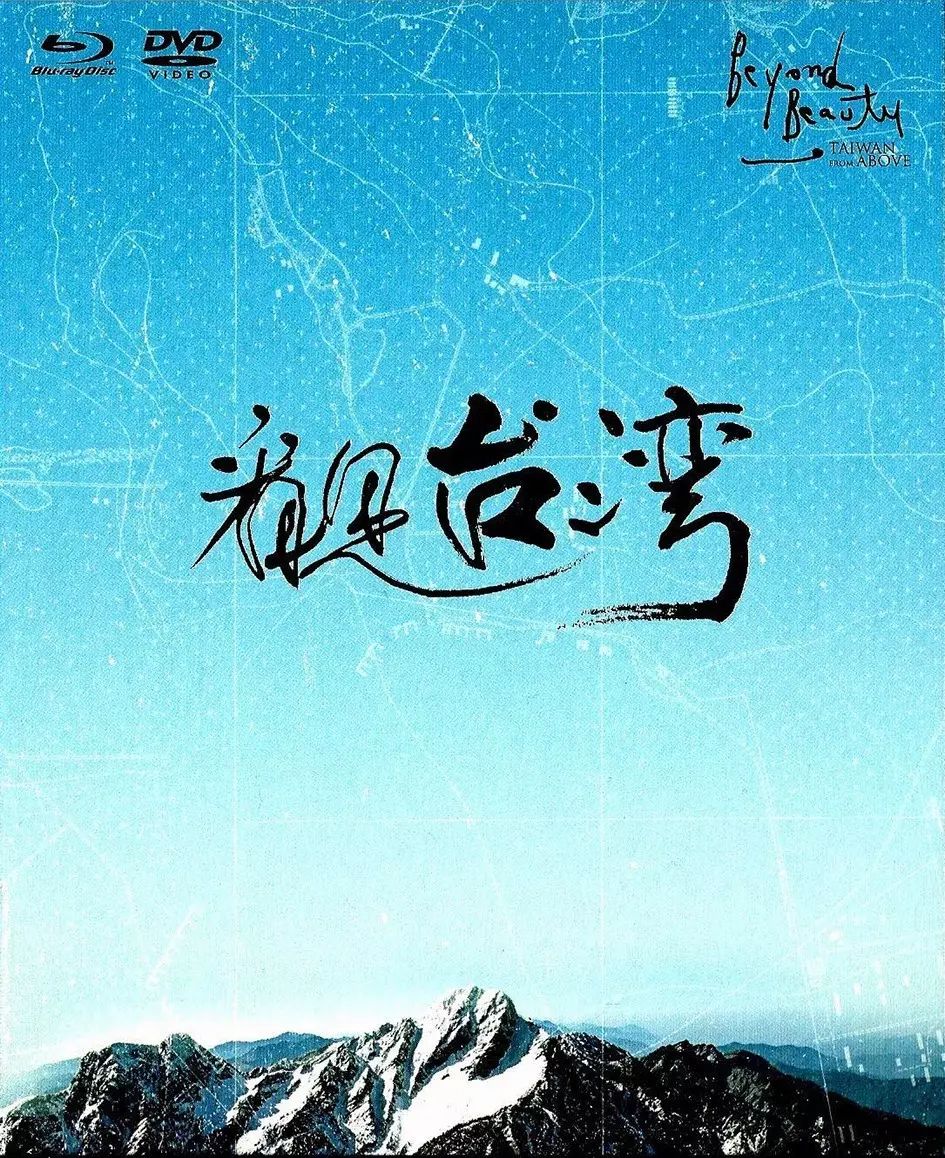
如果人类都有一对翅膀,可以飞上天空的时候,就会以一个更大的视角看到这个世界,可能就不会对自己的生存的家园肆无忌惮地破坏了。
去年,纪录片《看见台湾》创造了台湾岛内2亿新台币票房的纪录,超过了很多商业大片的票房。这部看上去没有任何故事和情节全部由航拍画面组成的纪录片,在吴念真平和的旁白与何国杰(电影《赛德克巴莱》的配乐)深沉的配乐“伴奏”下,以温和的方式震撼了整个台湾岛,让人们通过航拍视角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土地的真貌。今年,导演齐柏林和他的制片团队来大陆,洽谈将该片引进大陆发行,齐柏林很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在大陆上映,但是由于进口大片的指标已经满额,也许只能等到明年了。期间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记者说“你这个片子里呈现出来的台湾自然环境被破坏的现实跟大陆比的话,实际上只是小巫见大巫”时,齐柏林说:“大陆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都这么讲。”
齐柏林在成为《看见台湾》这部纪录片导演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他平时最大的兴趣是航空摄影。台湾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美的风光常常使他在空中流连忘返。他这一拍就是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他可能是少有的见证台湾自然环境发生巨变的人之一。当有一天,他想在空中寻找美丽的风景时,发现很难找到了,看到的是那种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的地貌。他觉得很惋惜,很心疼。尤其是最近这10年,那种美丽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他说:“我想每个摄影师都喜欢拍漂亮、美丽的东西,我也不例外。我刚开始拍台湾的时候,就是想拍美丽的台湾,我想让世界看见它。我们在地面拍,可以借景,但从空中拍就没有办法,因为飞上去之后你会看得很远、看得很广,所有的样貌原形毕露。当你想要拍到美丽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知道环境发生问题了。我是从飞到天空之后才开始真正认识我生长的地方,我在没有飞上天际之前,我跟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任何的感受。”

齐柏林
这触动了齐柏林,毕竟能经常在天上飞的人不多,他要把看见的台湾告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现在的台湾已经变成了什么样。齐柏林说:“台湾面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自然灾害。台湾是一个全世界有的灾害通常都有的那种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人为开发加速对自然的破坏,这一点是我最介意的。我们这部片子叫《看见台湾》,之前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域望》,意思是大范围地来看这片土地,而谐音就是人的‘欲望’。其实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最常出现的一句对白,就是‘矛盾跟冲突’。我们在这个土地上生活,我们为了生存,我们追求经济的发展,往往牺牲的都是自然环境。这个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在我没有做这件事之前,都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没有任何疑虑的方式。我从小到长大的过程中,政府告诉我们所有的资讯,都是说这是‘国家’经济发展最优先的,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当我们自己长大了,开始有了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我们经常都是拿着我们的环境去牺牲,换到经济利益。尤其是台湾这十年来,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台湾的自然灾害跟整个地球的气候异常等各方面都有些关联,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抵抗。可是人为的开发跟破坏,加速和扩大了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因为一般人没有这种‘飞翔’的视野,所以我就想要把我看到的,让台湾的人民也可以看得见。这是当时我想要做这件事的初衷。”
由于齐柏林经常从事航空摄影,慢慢他被台湾的《大地地理杂志》挖掘出来。当时杂志社找他,他心里还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觉得应该把拍到的最美的台湾的照片提供给他们发表,至于拍到的不好看的照片,他觉得是不适合拿出来发表的。“我们在台湾的高山上看到很多高山农业,我小时候对它的认知是:这群农民都在以非常勤恳、勤奋、很有毅力的方式,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与天争地、与天搏斗,然后创造出这样的产值,供给我们的需求。那是一个很正面的认知。”后来,杂志社做了一个选题《大地的脸》,编辑让齐柏林提供一些类型照片,比如海岸线布满消波块、堤防那种的照片。当这个选题出来之后,彻底颠覆了齐柏林过去的观念,原来这些建筑物会改变海岸的生态,可能会导致物种消失。这件事让齐柏林开始思考他过去见到的景象——在河的源头兴建水电站、整座山上都是槟榔树……他开始从一个大地的观察者变成一个社会问题的观察者。“原来我们过去认为的那种类似像愚公移山的精神,其实都不见得是正确的。”齐柏林说。
齐柏林出版过三十多本摄影集,其中有一本摄影集全部是台湾的负面影像。他经常办影展,到各处演讲,呼吁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他说:“你会发觉所有的人对这项议题的反应是很冷漠的,都觉得破坏环境破坏地球的那是你,跟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所以我很泄气、很挫折,我很急切地希望大家要爱护土地,可是偏偏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不断地在伤害土地。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管是媒体也好、教育也好,都说要重视环境保护。可是在我的观察中,不仅没有被保护,而且是持续地被恶化当中。我当时在大学演讲的时候,七八成的同学都在睡觉,不爱听,因为我讲得也啰嗦。到2008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讲——拍纪录片。但是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有点像白日做梦。当我把这个想法跟很多人说出来,希望能够得到支持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人都想象不出来用航拍的方式去拍一部纪录片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当时已经有非常专业的航拍系统、设备,但是台湾没有。所以2009年我从美国引进这个技术,到2010年我拥有这套设备,就正式开始来拍这个片子。”
但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最大的问题是经费。因为直升飞机和这也空中摄影设备所需的费用,不是一个公务员能支付得起的。在台湾,公务员是不能去做找赞助和募款这样的事情,公务员不能有额外收入。当时齐柏林很犹豫,如果再坚持三年到退休,他就可以拿到“终身俸”了。但是他想拍纪录片的意念又非常坚定。那时候他非常痛苦,他说:“我很犹豫就是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我家里面就没有办法照顾到,而且我又牺牲了我的退休金,值不值得。那段时间我非常讨厌我那种犹豫不决的个性。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告诉自己,为了追逐你的理想,你明天早上就勇敢地去辞职,递出辞呈。可是每次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看到一家老小都是靠我来养的时候,又退缩了。所以这种纠结持续了一整年,我真是讨厌死我自己了,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没有勇气。”
最终促使齐柏林下决心辞职是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这是台湾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台风,在南台湾地区三天降雨量超过了3000毫米。当时齐柏林坐着直升飞机飞到山里,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了。“那是我第一次在飞行摄影当中掉眼泪。”他说,“3000毫米的降雨量,落在的地方不管过去有没有滥垦滥伐、滥建的这种现象,即使是原始的森林也是撑不住的,那是种毁天灭地似地破坏和摧残。我第一个反应是恐惧,台湾怎么了?好像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近年来天灾人祸一直不断;第二个反应是心疼,台湾的森林资源非常丰富,千百年的林木傲然的姿态,矗立在山头上面,某种程度上是台湾人的骄傲。土地上能够孕育出这么珍贵的林木,在那一次的天然灾害里面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很心疼,所以难受,心里面难过。但是因为重灾区在南台湾,台湾其他地区的人感受不到那样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放弃我的工作,来拍这个纪录片。”
齐柏林要面对家人了。当他跟妈妈说,把房契拿出来时,妈妈变得非常紧张和惶恐。因为在父母眼里,齐柏林从小就是一个不让家人操心的乖孩子,这么多年一直循规蹈矩,突然要房契,他妈妈问:“要房契干什么用?”当齐柏林说辞职拍纪录片,拿房契做抵押时,妈妈非常反对。但是齐柏林的父亲非常理解他支持他。齐柏林的儿子还在上高中,他问齐柏林:“你辞职以后,还有钱供给我读大学吗?”
当时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齐柏林只能故作镇静,安慰儿子,鼓励他考上国立大学。当真正开始拍摄的时候,资金从来就没有完全到位过。制片人找到一点钱,就拍一段时间,没有钱就停下来继续找钱,他们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总算把片子拍出来了。这前后花费了大约9000万新台币(约合1800万人民币),有将近一半的费用用于租直升飞机,直升飞机每小时大约15万新台币。这期间,齐柏林不止一次想过放弃,“只要资金不到位,这种念头就会出现。”齐柏林说,“可是你要想到,你要怎么回去面对已经赞助支持你的人,影片最后面的那些上面的感谢,是从台币500块到3000万,帮助过我们的人名字全部都在上面。”
刚开始的时候,齐柏林给纪录片写了一个详细的脚本,因为在过去的20年航空摄影经验中,他已经非常清楚该拍哪里怎么拍了。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发现很难实现。有些画面由于天气和季节原因根本拍不到,飞去两三次也拍不到,但有时候他能拍到意想不到的画面。后来,齐柏林改用纯纪录方式,把有价值的影像拍下来,直接用影像讲故事。三年间,他飞行了四百多个小时,拍了三百多个小时的素材。
让齐柏林没有想到的是,《看见台湾》上映之后,一时间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在这之前,他只是希望自己作为导演,能让影片进电影院,让观众通过这部电影来了解台湾。最终,它创下了2亿新台币的票房纪录,并且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完全没有,这是个意外,也是个惊喜。我不是说了吗,我演讲的时候有七八成的同学在睡觉。我之所以要坚持上大银幕,因为我觉得大银幕那种视觉的感动是没有办法用手机、电脑、电视可以感受到的。台湾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女性叫陈文茜,她非常关心我这个计划,在电影要上映之前,我去上她的节目,广告时间她一直骂我,说在台湾片子上院线要拆账,大部分钱是被院线赚走了。她怕我赔钱,就不赞同我上大银幕。可是每一个导演的梦想,一定是希望他的作品可以上大银幕和观众见面吧。当时大多数人是不看好的,一开始愿意上我们这个电影的大概只有20家左右的影院。电影上线之前,很多公司都要我们砸钱去做广告、做行销,我不同意。第一我没有钱;第二,这个片子如果在台湾不受青睐、不受关心的话,那我真的是对台湾人彻底地失望。因为我们台湾人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爱台湾’。当时我觉得如果这部片子没有得到台湾人支持的话,我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地灰心。所以我不愿意花钱去做广告行销这些事情,但是我愿意花钱去免费放给大家看。我当时想要在台湾的主要城市,通过募款的方式,免费放给当地民众看。因为我们这部片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企业的无偿赞助,我应该回馈给他们。那时候所有人都告诉我说,不能免费让大家看。因为很多观众会因为免费反而不珍惜它。他们认为坚持要卖票。结果我们在高雄办第一场首映的时候,本来打算只卖6000个位子,但卖了10000个位子,整个体育馆坐得满满的。影院的业者看到我们这个片子反响这么好,觉得我们应该是有机会的。所以后来上映我们片子的就变成四十几家影院,后来变成六十多家。在台湾,以纪录片来讲,它的规模是都破纪录的。上映到一个月就破亿,上映到66天的时候破2亿。如果用票价来折算的话,大概有一百多万人次看了这部片子。”

《看见台湾》是一部揭台湾疮疤的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即使到了没钱继续下去的时候,齐柏林也不想去找政府补助。因为在台湾,拍电影都会有一笔政府补助资金。他说:“当时我担心拿了政府补助的话,我怕我的观点会被左右。譬如它会要求你不能讲这个,不能讲那个。后来我发觉完全不是这样。台湾‘行政院长’通过新闻得知这部片子大概是在讲什么事情,引起了很大的反想,他就包场,让内阁官员陪他一起看,我坐在旁边陪他一起看。看完之后,‘行政院长’夫人就掩面哭泣,她受不了。‘行政院长’看完以后马英九跟着看。过去我是一个基层公务员,换个身份变成导演,我还是有公务员的尊卑概念,还是觉得要很尊敬他们。我非常惊讶是,政府是用一种非常开阔跟包容的胸襟来看我片子的,他们不会觉得我这个片子是来找政府麻烦的。事实上我也非常厚道,因为我自己从政府部门出来,知道什么样的议题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也不愿意制造对立情绪。所以那时候他们都很感谢我,谢谢我拍了这部片子,因为他们认为‘民气可用’。政府以前没办法处理环保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民主了,很多立法委员议员都包庇姑息这种问题。所以他们反而感谢我,说他们可以抛下之前的那种包袱,来改善环境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