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况《荀子·性恶》
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商鞅《商君书·错法》
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
——韩非《韩非子·奸劫弑臣》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老子《道德经·绝圣弃智》
勒庞:始于大革命
在吉登斯看来,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塑造了现代世界。(吉登斯 2013)
当我们跳过作为极端年代的20世纪向前回溯,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激情、暴力、血腥和动荡在向世人宣告,曾经的一个世界被打碎,一去不返了。从此,直到20世纪初的人类更剧烈的冲突产生,人们都不得不始终生活在大革命的阴影下,那是时代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母题。
这场血腥的革命于1789年爆发。当然,它的思想根基早已潜伏已久,全欧洲的制度都已腐败,而新生的力量也在急切地破土而出,但最终法国却成为了整个欧洲的那个火山口。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奉持者推动着革命的战车滚滚向前,这辆战车最终依凭着惯性,却将这些理想碾为齑粉。独裁者、街垒和断头台将“自由、平等、博爱”取而代之。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支配社会的幻想在人们非理性的歇斯底里中被击得粉碎。
而之后的20世纪(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极端的年代”)似乎也在大革命的阴影下书写着历史的续章。苏联帝国和第三帝国先后建立,又土崩瓦解。这似乎意味着人们依然在咀嚼着大革命的苦涩遗产,“如果这些政权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继承人,那么托克维尔和孚雷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大革命的意义不在于增进自由,而在于扩张国家权力。对理性化国家的美好前景的信念,是启蒙运动的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两百年中的所有其他革命,都是其真正的继承人。”(威廉·多伊尔 2017)
勒庞的思想正是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余波的现实和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想的反动当中。他做出了他对于时代的论断,“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
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勒庞 1895/2015)
而另一个比他稍早做出类似论断的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曾祖父马勒泽布在1792年大革命爆发后在对法皇路易十六的审判中担任辩护律师。次年罗伯斯庇尔上台,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将成千上万的人送上了断头台,而马勒泽布就是其中之一。而托克维尔的父母也在被处决的名单之中。所幸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很快又被推翻,他们才从断头台的铡刀下留得性命。
横扫欧洲的拿破仑战败,使得波旁王朝复辟,而1830年的七月革命又使得奥尔良王朝建立。拥护后者的托克维尔和效忠前者的父母产生了冲突,或许是为了回避这种冲突,他接受了一项考察美国监狱制度的任务。(周晓虹 2002:119)在美国的经历使他写成了《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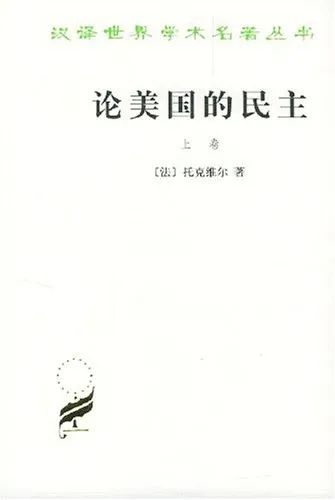
托克维尔身后破碎的旧欧洲,使得他向着这篇充满生气的新大陆眺望。在这里他看见了与勒庞相似的未来,旧时代确实正在终结,托克维尔看到了民主制在逐步取代贵族制。在他的表述中,这两种理想类型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大革命中被推崇的“平等”价值的最终实现。帝王将相的退却代表这个社会不再创造一个个体“英雄的美德”,而是去养成每个个人“温良的习惯”。
当然,平等也意味着个体之间的相似和庸碌,同时意味着人们会因此而备受打击。在群体之中,个体会自豪于其与群体的不同,也同样会因此备受压力。身为贵族的托克维尔不见得喜欢只管实用而缺乏神性的美国产品(也包括文学艺术),他认为这些要归咎于美国的民主。但他还有深层的忧虑——没有哪个国家向美国这样缺乏独立性和言论自由。这并不是指异见者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而是根本不会有人理睬他们。
托克维尔更与穆勒不同,他承认少数人比多数人更开化,却并不认为少数人可以去引导和教育舆论。他认为事情恰恰相反,民主使得作为少数人的知识分子为舆论服务。
(哈维·C.曼斯菲尔德 2016)
托克维尔在1856年写出了另一部巨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然而此时大革命余波仍在。1848年路易·波拿巴通过革命建立了第二共和国,通过利用马克思所描述的小农的权力崇拜心理和对拿破仑的感恩戴德背叛了革命,通过了人数众多的农民投票建立了第二帝国。(马克思 1951:693)1859年托克维尔撒手人寰,而他所仇视的第二帝国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的全面失败才宣告崩溃。
勒庞生于1841年,他目睹了第二帝国的溃败和第三共和国的成立。1889年的布朗热危机令他印象深刻,群众们簇拥着布朗热高喊“万岁”的场景,与其很快堕入为嫌犯的境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件事显然为他创作于1895年完成的《乌合之众》一书提供了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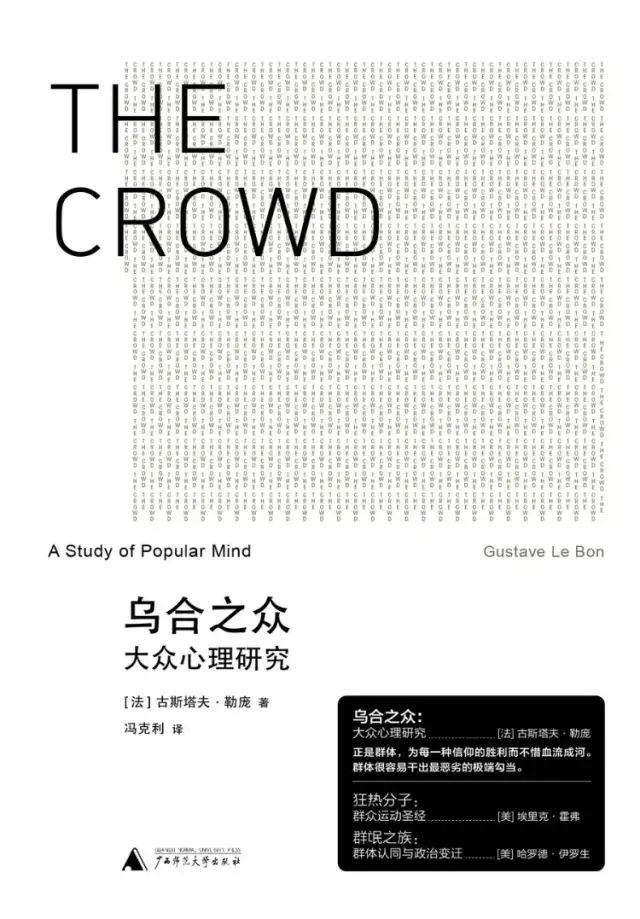
他写道,“群体很容易作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干出什么事情,……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他轻蔑地在另一处写道,“只要候选人能够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对群体产生影响并不困难。根据捐款人的招认,300万法郎就足以保证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就是如此。
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勒庞 1895/2015)
他在一方面深刻认识到了群体的破坏力和群体时代必将到来的大势,“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注定要屈从于群体的势力。因为群体的眼光短浅,有可能让群体守规矩的所有障碍都已经被一一清除。” 但另一方面,却隐含着进一步的轻蔑:他对历史下着虚无主义的判断,似乎是某种程度上暗示操纵群体的方法。“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我们极可能一句也没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勒庞 1895/2015)
勒庞用他深邃的目光试图去穿透这个作为新生的怪物的群体,王侯将相原有的作为个体的超凡魅力正无时无刻不在被面部不清的个体的集合冲击着。勒庞认识到,这个怪物将诸多个体包裹在其内部,却又具有了超于这些个体的特征。他认为这些特征来源于个体的具有催眠性质的暗示感受性。这使得个体在群体中是去个性化的,处在群体之中会使得个体丧失个人责任感,同时使得情感作用蒙蔽了理智。“单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勒庞 1895/2015)显然,在勒庞看来,正因为群体的非理性和无意识,使得个人即使具有足够的判断力,当他融入群体时,他也变得不足以令人信任。
但是同时,勒庞揭示了一种可能性。他指出,“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得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勒庞 1895/2015)
勒庞的论述带有着精英主义的居高临下,正如默顿所指出的,“
这是一幅世纪末的人类画像,它把人类描绘成极易受到操纵,莫明其妙地情愿受骗上当。不过这显然是一幅未竟的肖像画,因为如果有些人受到控制,必定还有一些人在控制。因此从根本上说,有些人是把别人当做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另一个更深刻的假设是,人类有着自我欺骗的无限能力,他能够头头是道地把罪恶说成美德,为了犯罪而否定美德。
”(默顿 1969)
这正是勒庞与托克维尔的不同,在托克维尔眼里,贵族制崩塌后的危险在于,民众日益成为“苍白的国王”,沉溺于用日常的庸碌来填充灵魂。而那些少数人引导民众的努力却不会成功,恰恰相反,少数人(如知识分子)却会变得了迎合和服务多数人。但勒庞却在暗示,作为多数人的群体,尽管力量强大,却是处于无意识中、非理性的。而作为精英的少数人能够通过谙熟群体心理学的规律来对群体进行操弄。
在这个意义上,群氓政治学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正是一体两面的。群体容易受到迷惑、诱导的特性,恰恰意味着有人在迷惑和诱导群体。而作为少数的精英之所以能够被体现,正在于更大数量的多数被表现为愚昧。正是因此,勒庞从群体的面向上的叙述虽然切中要害,却还并不完整。而另一个面向我们还需要从更遥远的传统去寻找。
马基雅维利:工具主义政治学
马基雅维利被认为臭名昭著的学说产生于彼时分崩离析的亚平宁半岛。意大利当时的困境我们可以从马基雅维利一个秉持了一生的主张窥见些许端倪。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将军队划分为两种类型——雇佣军和公民军。在他看来,意大利的乱局就在源于意大利的各个政治势力都依赖于“百无一用,反添危险”雇佣兵的作战,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这导致了,意大利陷入“被查理蹂躏,被路易洗劫,被费迪南德扫荡,被瑞士人羞辱”的境地。正因为如此,他在君主论中建议道,“不要使用这种军队,而要组建自己的武装”。(马基雅维利,1532/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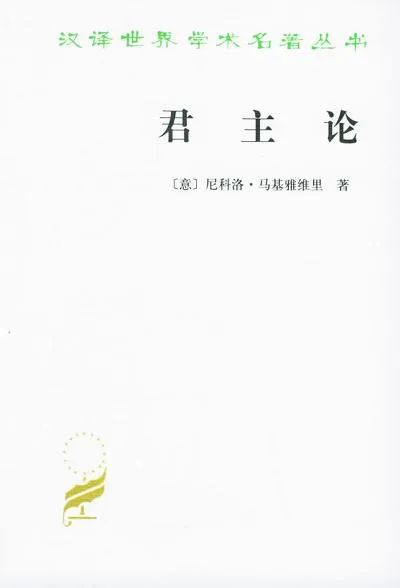
即使从当时看,佛罗伦萨的公民兵在战场上也难堪大用,而后世史家也普遍认可雇佣军制度的有效性。但马基雅维利对此的执着实际上与他的其他学说的观点是具有一致性的,即
去支配可以被支配的一切
。他反对当时主导的基督教神学所认为人被上帝和时运统治的想法,他认为“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而试图去支配所能支配的部分,正是他的一贯思路。即使是不能被支配的时运,他也在强调,“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 (马基雅维利,1532/2011)在这样的观点下,他强调做“自己军队的绝对主宰”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马基雅维利的十年外交生涯中,他能始终深切地感受到大国对于其城邦佛罗伦萨的轻蔑。这种轻蔑正是建立在强大军事实力和君主控制力之上的。这也就成为了《君主论》中的两个核心议题。在意大利的纷乱中,他认为,“一个国家绝不可能统一和幸福,除非它像法国或西班牙一样,只服从一个政府的统治——不管这个政府是共和政府还是君主政府。”(杜兰特 2018)马基雅维利并非君主制的拥趸,他仅仅是抱持着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政体,这也是他对佛罗伦萨统治机器的软弱痛心疾首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于罗马教皇国的谴责的重点可能并不在于其保卫自身的世俗权力,而是其没有用尽一切力量使得意大利归于统一。
当然,意大利的混乱也使得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性抱持着悲观的态度。就如他不信任雇佣兵一样,他认为一个好的君主是不应倚仗于对他人的信任(也因为这是不可控的)。
在他看来,“关于人类,一般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
(马基雅维利,1532/2011)
正因为如此,权术是必要的。所以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不能同时使得自己受到爱戴和畏惧,“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依靠恩义来维系的爱戴是脆弱的,但依靠对惩罚的恐惧而形成的畏惧却会保持。而他所强调的军队和法律正是使得惩罚成为一种潜在的可能。
这种对政治的工具主义思路是开创性的。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完全对道德嗤之以鼻,但他强调更加技术性的问题。道德与统治行为的松绑使得道德变成了虚空而没有依凭的戒令,或者变成了而一种对于权力的装饰。即使马基雅维利并不强调这点,但其中的潜在逻辑已经昭然若揭。马基雅维利的主张完全摈弃了与基督教的教义进行道德上的论辩,
他直指问题的核心,君主行动的核心并不应该是奉行美德,而是保持权力。
后者才是前者的前提,而前者也是为后者服务的。
他以作为君主美德的“慷慨”举例,他指出,受人称誉的慷慨必须要为人所知,因为“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获称誉,它就损害你了。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而慷慨的行为同时也会让君主的财力耗尽,到最后为了保持慷慨的名声,横征暴敛,使得臣民仇视他。因此,君主实际不应当在意的吝啬之名。但有一种情况下,保持“慷慨”之名是有益的,“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慷他人之慨”,却能使得君主赢得美名。而“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马基雅维利,1532/2011)
这种根植于现实的工具主义观念贯穿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这并非意味着其缺乏对于现实政治的好恶。但他将一种技术性的政治凌驾于作为美德和价值的政治之上。以对政治的有效性的追求来取代对于善政的追求。我们将会看到,马基雅维利所播种的观念将会在新时代中生长、茁壮。在一个被认为君主与贵族即将退场的新时代,另一种政治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开枝散叶。
莫斯卡&帕累托:统治阶级和精英的循环
1848年,帕累托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是意大利热那亚贵族,因追随马志尼共和理想的自由主义事业,而受到吞并热亚那的皮埃蒙特王国的萨伏依王朝的迫害,流亡巴黎。(科塞 2007:357)在萨伏依王朝的努力下,1861年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马基雅维利的梦想终于在此时终于实现,意大利终于统一了。
但政治上的统一并不能完全弥合社会上的分裂。一个政府之下,南方和北方的冲突却日益激化。北方在经济发展顺利,政局稳定,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右派政府指导下步入了现代化的正轨。但南方主要是农业地区,而贫富两级分化又极为严重,大量人口处于常年失业的状态。原来皮埃蒙特的政治精英掌握着国家的命运,延续了加富尔自由主义的传统,对全国课以重税,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提倡自由贸易,使财政收支平衡,并实行谨慎的外交政策。但他们对南北的撕裂视若无睹,而他们的支持者——仅约占人口2%的有权投票者——也对此置若罔闻。(科塞 2007:367-368)
他们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左派政党上台,尽管这场选举充满了舞弊和对选民和官员的恫吓,但这也同样意味着人民(尤其是南方的人民)对于右派政府的厌倦。但此后的现实证明,除了政治日渐腐败,政客换了一茬又一茬,所谓的改革从未实现,但政客们对于权术的运用却愈加炉火纯青。为了缓解国内矛盾,意大利对外保持着激进的殖民主义政策却屡屡受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参与其中,并成为战胜国,却在巴黎和会上并未争取到丝毫利益。即使如此,北方的经济仍然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南方农民却仍然处在赤贫状态,期望改善这种状态的改革却举步维艰。这种撕裂甚至持续到1946年意大利在结束了法西斯统治后对于是否保留君主制的全民公投上。在投票结果上的南北撕裂仿佛意大利本来是两个国家。
在帕累托的早年,受到父亲的影响,他抱持着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信念。但这种信念并未坚持很久。马志尼和加富尔的思想在那时也是整个意大利的主流。但现实中政治的逐渐腐败和社会的动荡,使得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者所抱持的对未来的乐观信念被日益消磨。这时,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又找寻到了曾经的遗产——马基雅维利的遗产。
1893年,帕累托受聘于瑞士的洛桑大学,此时他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左派。他为在 1898年米兰五月骚乱后被迫逃离意大利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左派提供掩蔽处。当邻国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爆发时,与许多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热情地支持着德雷福斯。(科塞 2007:359)而此时与他立场相同的还有当时在巴黎大学的埃米尔·涂尔干,他在德雷福斯时间的高潮时期为其辩护。并不巧合的是,涂尔干对群体的认识对勒庞产生了影响,涂尔干认为群体显然具有着个体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这是这一点被勒庞所借鉴。(周晓虹 2002:187)而帕累托显然关注到了勒庞对于群体的论述。(科塞 2007: 366)
但无论如何,帕累托变了,1898年后,他急剧地改变了观点,放弃了对将意大利经济进行自由主义改革所抱的希望,并转向激烈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思想。(科塞 2007: 359)而帕累托所提出的精英循环论就是这种对悲观和失望的一个总汇集。
帕累托对于马基雅维利的继承是极为明显的。马基雅维利写道,“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马基雅维利 1532/2011)而帕累托则将政治精英分为,狐狸与狮子两类。狐狸式的精英意味着“善于试验、改革、标新立异”,喜欢通过计谋、 宣传来维持自己的权力,而老虎式的精英则代表“代表着‘社会惰性’的保守力量”,他们是果敢、富于勇气的铁腕人物,喜欢使用强权和暴力来解决问题。而所谓的政治,正是这两种精英交替统治的循环。
在帕累托眼中,一个政权的早期统治者是狮子型精英,他们运用暴力夺取权力。而他们的后代则逐渐沉溺于文明的享受,丧失了强权的特性,却通过精巧的权术来进行统治。而当这种的统治日渐趋于瓦解之时,非统治群体中新的狮子型精英又会以强力卷土重来。而历史便在此时完成了一个循环。

但帕累托对于精英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他时而认为精英是具有才能的人,时而又指出处于精英地位的人完全是被吹捧出来的。而另一些非精英的人反而具有才能。(科塞 2007:353)这是因为精英的长期统治导致的腐化必然会使得另一些人取而代之。帕累托认为,有两种办法可以避免这种状况,一是消灭掉非精英群体中的那些优秀分子,因为他们是潜在的革命者。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将他们吸纳进精英阶层,实现和平的社会流动。
帕累托受到了比他稍早一些的莫斯卡的影响,莫斯卡的在1896年撰写的《统治阶级》中,首先提出了完整的精英理论。他的最基本的原理可以概括如下,“
在所有社会,只要存在一个政府,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利(统治者)的总是少数人,而多数人(被统治者)事实上从为能参与政府,而只是服从罢了。
”(莫斯卡,1892/2005:2)与马克思以经济划分阶级不同,莫斯卡以政治来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更与马克思大相径庭的是,他认为,阶级斗争并非是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前展开,而是两个精英群体的竞争。只不过这两个精英群体,一个占据了当前的统治地位,而另一个则宣称代表大众的利益。

 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莫斯卡的理论是一种悲观的学说,他将政治的追求良善价值的行为判了死刑。莫斯卡代表了一代人对于进步主义的失望,这种失望可以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上看到。他在1890年代就尖锐地指出,“共产主义或集体主义共和国的领袖对他人意志的控制及暴虐程度将会是空前的。由于可以随意支配短缺或盈余,这就使他们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和虚荣心。尽管他们表面上装出一副艰苦朴素的面孔,但实际上却毫不含糊。而这些在目前还只是那些当权者和富人们的额外所得。更有甚者,共产主义共和国的那些领袖们往往贬损其他人的人格尊严。”(莫斯卡 1892/2005:326)
米歇尔斯:人性的铁笼
进步主义最终在意大利崩溃了,不管这个时间节点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或许是意大利实现统一之后的虚空,也或许是一战后的外交失败。而究竟是哪种进步主义的叙事失去了市场,也变得不再重要,自由主义者在意大利一溃千里,而社会主义者也无法力挽狂澜。最终,一个结束一切的人来了,1922年,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
莫斯卡和帕累托都将马克思的构想看作是另一套统治者的神话,而统治者的更替带来的除了失望,只有失望。在这种意义上,正如彼得·格鲁克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夕开始撰写的著作中所指出的,
“极权主义的兴起,导致大众逃向极权主义绝望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失败,而并非其胁迫与承诺”。
(彼得·格鲁克 1939/20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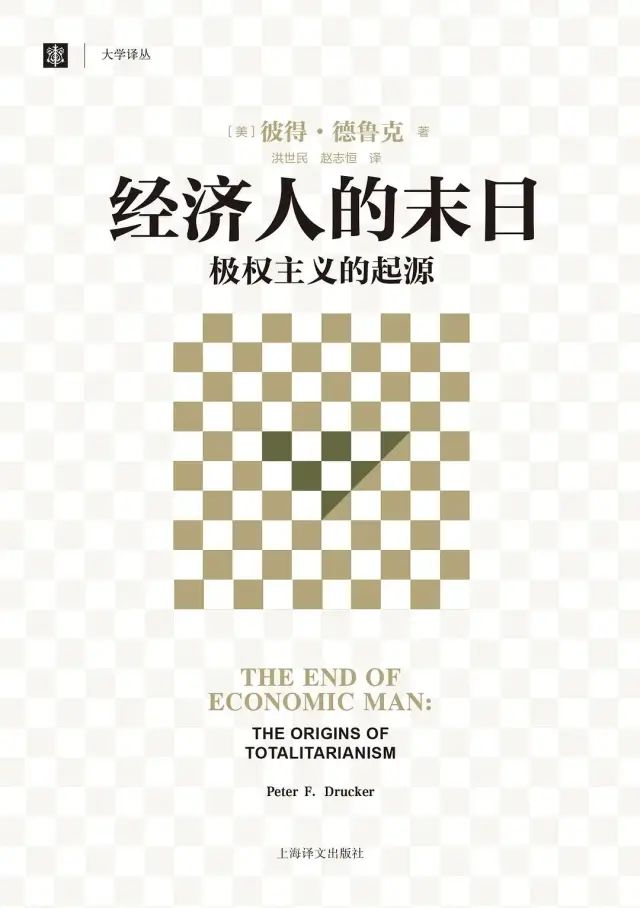
 彼得·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彼得·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我们似乎无法理解这种断裂,纳粹主义究竟追求什么,抑或是它正是对于进步追求的反面?帕累托看到了墨索里尼掌权的开端。更值得品味的是,1904年夏,流亡瑞士的墨索里尼在洛桑大学选过帕雷托开设的两门课,而他对此又津津乐道,将帕雷托的精英思想称之为“可能是当代最为杰出的社会学理论”;而1922年,在上台后,他确实仍然对帕雷托推崇备至,不但将后者选为意大利王国的参议员,而且还指定他担任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意大利代表。(科塞 2007:361)
这当然不意味着帕累托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认同,他的思想底色从一开始便是启蒙运动式的,但他却包含了对进步主义幻想的破灭。但这样的事实似乎是在暗示着二者存在某种思想上的关联,至少具有某种逻辑上的一致性。
比起帕累托,莫斯卡更早地影响了另一个人——米歇尔斯。米歇尔斯于1876年生于德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大学求学时便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但他所信奉的工团主义使得他在社会民主党内变得边缘。在他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赢得议会席位做出了过分的妥协,而议会政治的道路也并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们更可以参照另一位社会思想大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的理论中,权威类型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对于他来说,在世界无可避免的理性化的过程中,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卡里斯玛权威)中,作为法理型权威的科层制将不断扩张,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它将逐渐吞噬人的主体性。而可以期待的变革不过是卡里斯玛型权威在某一时刻跳出,来阻挡这种愈演愈烈的理性化进程。
而米歇尔斯在韦伯的基础上更近一步,他在社会民主党内的经历使得他看到,一个宣称革命的组织日益官僚化的过程,他最终悲观地指出,
“少数人最终凌驾于多数人的意志之上,党组织成立时期的目标成为少数人维持组织本身、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权威的牺牲品。可见,寡头统治是任何现代组织无法摆脱的‘宿命’”。
(米歇尔斯 1911/2003:2)他将此称为“寡头政治铁律”。
米歇尔斯吸收了勒庞对于群众的看法,并且指出领导者对于群众的必要性。“大众的这种事实上的不成熟状态并不是一种将随着未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进程而逐步趋于消失的暂时现象,相反,它导源于大众之所以成为大众的本质特性。正因为如此,即使将大众组织起来,他们仍然会在那些亟待解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上手足无一因为大众本身总是缺乏确定的目标,所以就需要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必要的引导。”(米歇尔斯 1911/2003:352)米歇尔斯认为,在现代的政治组织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分化是无可避免的,这正是现代专业分工所带来的。
一方面,领导者的长期地位优势使得其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于他们的支配欲和维持权力的冲突使得其刻意增加二者的分化。另一方面,对群体来说,政治的专业化使得他们再难窥伺其中日益复杂的运行结构。以至于显得漠不关心、得过且过。然而,如果凌驾于其上的权威被抛开,群体又会丧失其行动能力。因此,即便是最反对组织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也无法脱离组织化来进行。
1907年,在韦伯的帮助下,米歇尔斯在意大利的都灵谋到了一份教职。就是在那里,他受到了莫斯卡“统治阶级”理论的影响。他结合自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历,于1911年写成了《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应该不会有人比米歇尔斯更加了解宣称某种理想的虚伪,但这却并不妨碍他投身于另一个带有相似或相反宣称的政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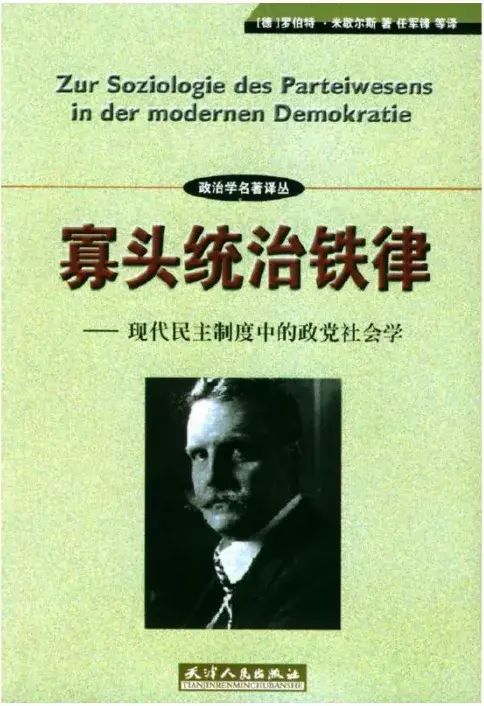
 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924年,米歇尔斯加入了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党。并在后来又称为了墨索里尼政府钦定的官方政治学家,而其主要职责就是帮助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建立一门法西斯政治学。与此可进行比较的是,1930年代,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全面溃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最终掌握了政权。
现实中的社会撕裂和政治动荡,使得民众的政治信念不断幻灭,民众陷入了混乱、彷徨中不可自拔。当虚无主义降临,所有的幻想都已经破灭,而所有的许诺都不可被兑现。直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承诺,一切混乱将被终止,但取而代之的,又是一个非理性的巅峰。
马基雅维利从支配者的面向,将政治工具化,剥离了价值理想。而勒庞则提供了被支配者被支配的原因,尽管它们具有无比的破坏力,但他们却不可避免的受到操弄。莫斯卡打破了革命的神话,一切政治不过是不同精英群体之间的斗争。而帕累托又告诉人们历史的演进不再存在进步,不过是不过精英统治的交替循环。最终,米歇尔斯指出组织自身成为统治工具的必然。至此,一切统治都归为虚无,而一切统治都成为必然。人们最终都陷入异化的政治,逃不开人性的牢笼。
但假如不将思想推向如此极端的境地。从马基雅维利以降,直到米歇尔斯,都围绕着一个问题:政治(或是什么样的政治)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而这至少意味着工具化的政治,具有成为善政工具的可能性。而这又蕴含在其他的思想脉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