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鸿
采访︱饶佳荣
整理︱洪珊珊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是以政治体为视角观察和理解华夏的。那么,何谓政治体呢?为何选择政治体这种视角?
胡鸿:
其实“政治体”这个词在社会科学的写作中很少使用,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概念。而我使用政治体是受罗新老师的启发,他在《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一书中说到历史视野中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之后又补充说:“政治体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的社会团体,尽管(“民族”)这种团体总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在我看来这就是对政治体的解释,算是一个定义,我的写作便是从这个定义出发的。
政治体这个概念有一些新的内涵。首先,它可以指一个政治性组织,比如部落、王国或帝国等。进而,它还可以指某种政权或政治关系的组织之下凝聚起来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随着后者而流动变化,我认为这是政治体的基本属性。这里要强调一下政权组织,在民族和族群问题上,王明珂先生更多的是从主观认同的角度关注边缘人的自主选择,这点当然非常重要,而我关注的是一个从上而下的划界权的问题,就是谁把某一群人规定为某一类人或某一种人,借用姚大力先生的一个很好的标题,叫“谁来决定我们是谁”。谈到划界权,民族问题就跟政治体建立起了关系。尽管有时候,一些边缘人群会凭自己的认同来加入或逃离某一政治组织,但通常的情况还是由政权来主导,比如户籍登记、民族识别、人群分类,等等。古代的户籍里面有时会标注个人的族群属性,比如秦简里会说荆不更,表示他原先是楚国人。
其次,被视为“民族”的古代人群集团拥有多重属性,而政治体属性只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则是文化共同体的属性。之前,我们对包括华夏在内的古代民族的研究都过于关注血缘共同体,或者说文化共同体。这里说的血缘当然是虚拟血缘,虚拟血缘共同体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即对起源的共同的文化信仰,因此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对文化共同体属性的过多关注,让许多没有经过一般民族史训练和反思的人认为古代人群集团是由于有共同的血缘或者共同的文化而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但这是不符合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的。人群能够结合在一起,其背后必然有一个组织他们的力量和网络,这个力量和网络就是由政治体完成的。政治体属性和文化共同体属性可以并存、相互影响,也可以不同步存在。
同时,我还必须强调这两种属性是有主次之别的,政治体属性是群体的主要属性,也是发挥主动作用的属性;而文化体属性则是次要的、从动的。政治体建立以后,文化性认同也会随之慢慢建立;政治体消失后,文化认同可能会再存在一段时间,而更多的情况是被纳入另一个政治体,文化认同也慢慢进入另一个建构轨道。

关于政治体属性和文化体属性之间的互动,可以举一个出色的研究案例,就是鲁西奇老师从古代族群凝聚的角度对秦楚汉之际楚人的分析和理解。他认为楚人最初是指以国君、诸侯为中心的楚国公族,春秋战国时期拓展到指整个楚国境内统治的人群,楚国后来征服了淮河中下游即东国地区、以及吴国故地、越国故地,这些地方的人也被纳入了楚人的范畴。秦灭楚国之后,楚国江陵地区和东国地区人群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陵地区是楚的腹心之地,按理说应该是楚人认同感最强的地区,但这个地区在秦末没有任何大的叛乱,反而是东国故地成了反秦浪潮的中心。这是因为江陵地区已被秦朝的南郡稳定地统治了五十年,基本已经建立了对秦朝政治体的政治认同,进而也部分建立起对“秦人”的文化认同;而东国故地只被统治了十几年,楚人自身的认同尚未消失,加上对急剧推行的秦制度的反感,使这一地区叛乱不断。再说楚这个集团,楚基于楚国的政治体而扩大,吸收其他人群,形成了一个既有共同政治体又有共同文化的一个集团;后来政治体被消灭,但共同文化认同仍旧存在;秦汉之际,政治体再次复兴,出现张楚政权和项羽政权;汉初之后,楚地分封的诸侯国逐渐被消灭,楚人再次沦落为只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人群。我认为鲁老师的这个例子很好地论证了政治体属性和文化体属性在一个类似族群的群体中的互动。
但是相较于楚人,华夏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尤其体现在秦汉时代以后。华夏对应于古代社会中能见到的最高级的政治体,即一个帝国级的超级政治体,所以这个政治体所对应的人群超过了族群的规模,可以说华夏具有一种超族群性。古代希腊人说Ethnos,包含了外来的、异族的、“非雅典人”的意思,同样,对于古代华夏来说,华夏指的是非族群的。就如同我们今天通俗口语说民族,往往指的是少数民族,反而不说民族的时候指的才是普通的主体民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政治体视角来分析华夏可能会更有收获。
书中说:“整个古代与中古时期,除了各级政治体能够有效地组织人们共同行动,其他的‘群体’如阶级、性别、地域、职业群体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某些宗教成功地组织起大量人口,也只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教团性的政治体。”为什么只有政治体才能有效地组织人们共同行动?换句话说,要满足怎样的条件,才可能产生有效的社会动员?
胡鸿:
我在书里面引到了美国社会学家布鲁贝克的理论,他认为社会学的分析很多时候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社会学意义上分类的群体作为一个事实上存在的行动主体。当然,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不一样,现代社会中人们有很多信息渠道,以美国的亚裔群体为例,他们可以在选举中发出利益诉求,因为现在有足够的沟通手段;在网络上发起一则倡议,许多人就会相互呼应地走上街头。而古代则缺少这样的信息渠道,比如湖北山区的蛮人和江西山区的蛮人相互认识认识的概率极低,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面对同一个政府苛政暴政的时候,可能会做出相同的反应,但绝对不会团结在一起,不存在现代意义上所谓的民族自觉,所以古代会出现民族问题地方化的倾向,甚至以政区+族称命名(如武陵蛮、雍州蛮)在史书中成为了主流的指称方式。
以某种身份把人群结合起来并共同行动,需要有严密组织和有效的社会动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农民起义很多都与宗教相关,因为宗教提供了一个组织框架,对人们进行了类似国家进行的人群编制,这样就能够很清楚地把人群调遣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人群就是松散的,且不说按共同的节奏行动,甚至都很难发出共同的声音。东汉时期的儒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组织,类似于政党,虽然没有达到现代政党的程度,但明显有一个以太学为中心的组织网络,正是这种政治组织领导了他们的共同行动。

您在书中提出:“西周初年的‘有夏’是一个以地缘和共同政治目的纠合起来的短暂政治军事联盟,不能看作族群。“周人”与“诸姬”为西周宗法制下的诸侯所认同,它们更应该看作一个扩大的氏族,或者是以氏族外形出现的封建国家秩序,尚不足以成为族群。”氏族、族群、政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有夏”为什么不能够称为族群?
胡鸿:
我们一般把氏族放在家族、部落、世系中,这是一组概念群,反映从家庭逐渐扩大、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形式,氏族往往是比较实在的;从现代往回看,把拥有共同文化的一群人划分出来,称为(古代)族群;而政治体在之前已经讲过了。氏族、族群和政治体是不同范畴和领域的概念。
从有夏到后来的华夏,有一个扩大的过程。最初有夏表示的是西土之人,我认为这是一个他称。古代一般人都会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西边角落的人,所以“有夏”,甚至是“西邑夏”,很可能都是来自商人的称呼。这是以地域为指向的,所以是一个地域群体,而不享有共同血缘。自称“有夏”的西土之人后来一起反抗商朝,自然也就是一个地域性的、政治性的联盟,所以“有夏”最初不是一个族群,这是我在书中第一部分的论证。西周建立以后,“有夏”这个词几乎没有再出现,因为此时西土之人已经是天下的主人,叫做周人,“有夏”不再适用。这个时期,国家的政治结构不是后来秦汉式的统治,而是一种向外、向东方扩展的封建体制,但并不是诸侯国里的人都可以叫周人,国内统治的殷人军队不是周人,还有所谓的“野人”,更是没有资格叫周人,只有以王室为中心的一批人才能称为周人。可见此时周人与严格的宗法体系相关,更像是一个扩大的氏族。
春秋时期,随着战争的扩大,人们开始各自以诸侯国建构一个新的认同,比如鲁人、楚人、齐人、秦人等等。我推测“有夏”这个词的内涵在齐桓公时代得到了延伸。齐国在周人这个体系中比较吃亏,周人的体系只认姬姓,姜姓是个异姓,所以齐国需要找到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符号。西土时代,姜姓地位很高,齐桓公便利用有夏来团结分封的诸侯国,“有夏”因而成为一个新的旗号。这个旗号是一种政治立场,和中原的齐、晋站在一起,就是“有夏”,不站在一起就被说成是戎狄。所以这时候的“有夏”仍然不强调血缘,还不能说是族群。秦统一之后,天下都变成了秦人,但因为秦进入有夏这个体系已有很长的时间,早已认同自己是夏人,会比较自觉地使用华夏、有夏这些词。
可见,从最初的有夏,到春秋战国的有夏,再到秦汉时期的华夏,都与当时的某个政治体相联系,如反商联盟、五霸主导的联盟和秦汉帝国。有夏和华夏并没有强调血缘,而更多的是与政治体相关,从这个层面而言,有夏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族群。
从先秦到秦汉,华夏化是否有一个重视血缘(譬如商周的宗法制)向重视文化(春秋战国)的转变?如果存在,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胡鸿:
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转变。按照我的分析,华夏或有夏这个符号所指的人群只有在西周那个时期特别重视血缘,当然,到后来,说自己是华夏的时候肯定也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血缘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与古代英雄祖先搭上关系。应该说,到秦汉以下,华夏化其实既不特别重视血缘也不重视文化,重视的是政治身份,比如在不在政府的户籍系统里面,是民还是夷,是附塞蛮夷还是归义蛮夷。把编户即“民”等同于华夏是总体情形,但有时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即进入了编户,但之前的非华夏身份还会被大家记住,经过几代之后,这个记忆被慢慢磨平,最终成为正常的民。
书中指出,上层人物可以经由家世血统攀附黄帝来变身华夏,而普通民众只有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才可能成为华夏。那么,上层为什么不通过法律来转换身份,由夷变夏?下层民众为什么不能通过攀附来变身华夏?
胡鸿:
其实王明珂先生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那本书里触及了这个问题,他提到除了地理意义上的华夏边缘以外,华夏边缘还存在于社会阶层上,他举的例子是土司往往说自己是汉人镇守军队的后裔,他下面统治的才是蕃人。这是王明珂先生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在古代的很多民族中都有这种现象,即攀附是从上层开始的。比如北魏时期拓跋族的华夏化就是如此。北魏的皇室有受到最好的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最早接受华夏文化;而勋臣集团的代人就要滞后一点,在孝文帝时代,就已经显现出了这种差距,华夏化存在阶层间的差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家世血统的攀附需要依赖家世谱系,因此底层的攀附要到出现家谱族谱之后才能看到。中国的普通家庭出现家谱大概是从宋代往后,一般是从明代甚至是清代开始。底层的族谱会把自己祖先追溯到汉代甚至是先秦史书中记载的某个人。以我自己的姓氏为例,大别山区的这支胡姓,按郡望自称是安定胡氏,说从江西迁入,中古以来安定是胡氏中郡望最高的一支,所以大家都会说自己是安定胡氏,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就不得而知了。汉字撰写家谱,意味着接受了汉文化,自然就会把汉代作为典范的时代,把三代作为黄金时代,找祖先首选五帝三王名相名将,这就是使用汉字书写文化后对人们思维和认同的影响。
家谱族谱出现以前,我们很难看到下层民众的攀附情况。下层基本都是被政府登记了户口、承担了赋役,而后被划定为华夏,成为所谓的民。另一方面,顾炎武已经说过,普通人是在汉代以后才开始有的姓氏,在这之前,他们大概没有能力追溯太遥远的祖先。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时期,上层可能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和能力去做主动的攀附,而下层往往没有知识,不知道该攀附谁,或者他们自己的追溯没能表达和流传下来,因而在史料中所见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地等着被划分、被教育。
南方、北方的华夏化分别受到怎样的制约?这种制约对南北方的华夏化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胡鸿:
南北方的华夏化过程其实像人字形的结构一样,在秦汉前面是一条线索,到后面就朝着两个分叉发展。简单来说,南方是一个旧的华夏帝国的延续和扩大,还是由原来占据着华夏名号的人群集团在统治着;北方,所谓的五胡,原来是被排除在华夏圈子之外的,所以他们开始主导政权之后,面临着是继续坚持自己的非华夏的身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统治模式,还是通过某种方式最后把自己变成华夏的问题。
十六国的历史其实很复杂,并不是所有政权最后一定都会走向华夏化,只能说在历史中往下传承下来的政权恰恰都是走向了华夏化的政权。许多政权附塞已久,很熟悉华夏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政权,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些汉族文化人,让他们按照已有的制度进行社会动员,把人们组织起来,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去发明或者从外引进一套新的组织理论和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北方这些政权没有自己的文书,但他们又需要文书来发布命令、登记人口等。文书行政是一个非常强的传统,改朝换代以后,文书格式不一定会变,它的技术性质最后会上升到政治性质或者说政治文化性质。北方政权可以不管华夏之说,强调胡人是单于可汗的后代,是天之骄子。但是当这些政权运用了华夏的政治文化,就必须承认华夏的优越性,否认自己是蛮夷,最后陷入华夏话语体系中,只能说自己就是华夏,是黄帝之后。
以北魏为例,北魏到了中后期,引进越来越多的旧朝官员和文士来做幕僚和政府官僚,许多汉晋的政治文化制度也慢慢被带进来,如法律制度、选官任官制、考课制度、门阀制度等等。门阀制度原是被北族排斥的制度,因为按照门阀制度,门阀高低的标准在于汉代魏晋以来祖辈父辈的官爵,而北族的先辈们在魏晋时期多是夷虏,甚至还是奴隶。根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崔浩的悲剧之一就在于他过早地想要建立门阀制度,他当然为拓跋皇室做了充分考虑,将元氏与汉代的陇西李氏接连上,但他没有也无法顾及北族的勋贵,冲撞了他们的切实利益。另外,华夏化程度加深,文治倾向随之变强,文人得势,北方以马上征战立身的武人则失落,二者也有冲突,北魏后期北镇与洛阳的分裂就与这种冲突相关。所以可以看到,北朝的华夏化并非直线发展,期间也有其他尝试,不断出现反对力量。北魏孝文宣武时期,华夏化力量达到压倒性优势;到了魏末,反华夏化力量加强;六镇之乱以后,到北周北齐的建立,其实一定程度上又一次重复了北魏的发展历程。所以,北方的华夏化确实存在阻力和制约。
南朝情况不同,南朝统治者本身就是华夏,所以不存在要不要华夏化的疑问,而是重视如何把华夏的政治体系向原来统治不到的山区扩展。六朝时期,山区的蛮人力量强大,甚至胜过两汉,经常让政府军队无可奈何。蛮人强大以后,政府只能和他们妥协,给他们加官进爵,后来发现这个办法比打仗更有用。于是,政府就逐渐以收编当地人的形式把国家的郡县体系推进到原来统治不到的地区。
总体而言,南北方所面对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北方统治者有选择,可以选择要不要变身华夏,而南方没有选择,只需考虑如何扩大华夏的统治范围。

在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相互竞争的现实是否会加剧这些政权的华夏化?而南方,如果站在山地民族的立场,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胡鸿:
华夏化事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应该说,这种合法性不能过于强调,因为它不会直接影响政权的生死存亡,只是关系到史书上会如何记载,是锦上添花、粉饰太平的手段。但是统治者也不会随便对待,他们仍旧会有意识地争取合法性,比如他们会争真命天子的名声,会追问天上的星象到底应在谁的身上,会欢迎地方上不断地上报祥瑞。所以最初,合法性并非很关痛痒,但有则更好。随着政权从征服进入稳定常态,合法性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但十六国大多没撑到这么久。
南方与北方有很大差异。如果说东亚世界有一个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或相互抗衡的政治文化的话,那就是草原游牧帝国的传统。草原游牧帝国很强大,而且其面对的他者不仅是中国,也有西域和朝鲜半岛等,所以它不仅是中国的边缘,它自身也是一个中心。与之相比,南方的地形和经济形态决定了这个地区的政治体系比较破碎,所以几乎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与中原政治体相抗衡的高级政治体,最多只能达到滇国、夜郎这种级别的政权。当华夏帝国的势力到来时,南方山地民族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他们只能考虑如何保全自己,如何能够在这个体系中获得更多利益。平原、河湖等地理位置较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被中原占领,山地民族不得不加入中原的交换系统,这种经济上一定程度的依赖,会使山地民族与中原的政治联系不被切断。另外,在山地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部落林立。率先与帝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得到帝国的支持,就能够首先强大起来,号令周围的部落,所以这也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东汉之后,帝国解体,原来地方上很强的华夏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衰败了,周边平原上的郡县城邑互相成了敌对关系,山区里面的人强大起来,但他们并没有想到建立一个取代帝国的新政权,而是通过在两边政权间反复选择立场来获得更多政治资源的输入,于是不知不觉中更深地卷入到了华夏的政治体系之中。
当然,南方山地人群也存在逃离的情况,即反抗华夏化,反抗被纳入国家的编户体系,这点在鲁西奇老师《释“蛮”》和罗新老师《王化与山险》这两篇文章中谈到了很多。进入华夏体系对于山地人群固然有美好的一面,因为在山里的生活十分艰苦,官府军队随时可能抓他们去贩卖做奴隶,投奔了华夏体系之后可以得到一定的保护。但是进入华夏体系也并非一定就是好事,因为代价是要承担更重的赋役。所以在这过程中,不断有人在两面跳,有时被引出平土成为熟蛮,但当赋役突然苛暴起来,承担不了就又逃到山里,被追急了则依托山险进行一定的军事反抗,如此反反复复。山地族群始终没有推翻华夏体系建立新制度的想法,他们只是在苦与更苦之间不断地进行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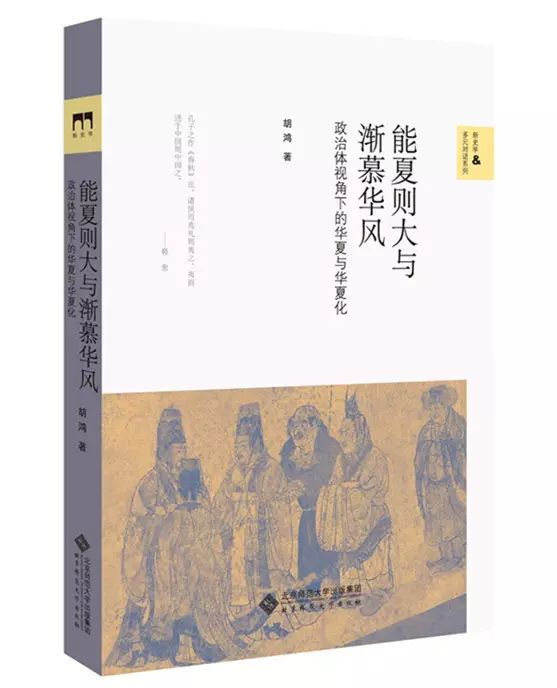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
华夏体系为什么扩张到南方的东南亚就停住了?帝国的突破口或者说极限在哪儿?
胡鸿:
帝国的扩张当然是有限度的,首先就是物资补给的问题。新征服的地区有时候甚至连语言都不通,能够做到的就是让这个地区的人民不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想让他们踊跃参军、提供粮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在短时间内很难成为继续前进的补给基地。汉代将南方新拓展的疆域设为初郡,初郡的特点是无赋税、以其故俗治,就是不改变当地原有的政治组织和生活方式,不向他们征收赋税,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地在名义上接受汉的统治。而想要在这些地区征召军队去征服更远的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维持漫长的补给线还需要大量的成本,成本达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承受,如海南岛设郡县以后,过了几十年,汉朝不得不放弃这个地区,就是因为维持的成本太过高昂。其次就是地形的制约。秦征伐岭南,岭南居民跑进山林中进行反抗,最后秦军也无法稳定控制。同样,汉代想攻进东南亚的雨林山区也是很难做到的。
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统治者并没有现代主权观念,不像现在重视寸土必争。对他们而言,反正天下都已被天命授予自己,“莫非王土”了,帝国也已占据天下中心的最美好的地域,多数蛮夷戎狄已经“朝贡”和“臣服”,那些不顺服的蛮夷迟早要沐浴王化的阳光,僻远之处一时冥顽不通的,更没必要为他们大动干戈。这种天下观当然有自我膨胀和自我安慰的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却是和平主义的,而不是穷兵黩武一心追求领土扩张。
·END·

本文首发于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
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
shrb.thepaper.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