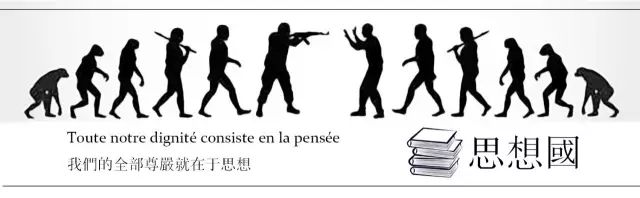
前日没有忍住,写了篇有关江歌的文字。
详见:
有关江歌案,于是他继续云游,继续吆喝……| 熊培云
留言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反对,其中夹杂着许多谩骂,有些内容实在不堪,就在后台放着。 二是表示难得有我这种观点。
写作者被毁被誉,乃世之常情。
我只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拉选票争一个输赢,所以对于多少人赞同或者反对,其实并不重要。
有读者留言说自己孤独,面对巨大的舆论的声浪,不知道如何站队。我说你终究是要站在自己一边的吧。“有时候你要把自己想象成大海,大海不会因为陆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这是我二十岁的时候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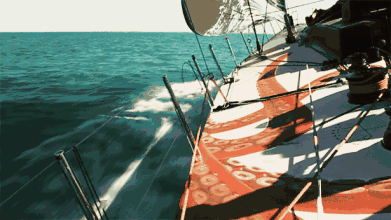
当有人高歌跟着某个soleil走的时候,我心里却唱起了《月亮走,我也走》。虽然那也是一首有着军旅色彩的歌曲,人的内心却还是正直、纯朴与饱满的。而且,那是一个从封闭时代走向开放时代的一首歌。
今日决定更新公号,是因为收到了苏州一位读者的来信。苏州是个神奇的地方,在那里我有不少热心的读者。今年
《慈悲与玫瑰》
出版后,若非因为外出访学,我定是要在那里的慢书房做一场活动的。
感谢这位朋友。她的来信很好地解释、深化了我上篇文章的内容。相较微信上的闲言碎语,还是书信更能进行与完成思想交流。有不少读者添加了我的微信,抱歉因为名额限制,我的个人账号早就无法再添加人数了(5000为限)。
有时候觉得遗憾,想想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帮我隔绝许多琐碎的事情。如果读者真有想要表达的观点,可交流的思想,写信依旧是最好的方式。时代变化太快,纸质信不敢奢望了,电子邮件正在成为古典。
作为思考与交流的平台,思想国读者的文后留言常常言不尽意,所以欢迎大家来信。也许我会因为忙碌甚至慵懒不能及时回,但通常都会认真看的。若有必要并获得许可,有些观点我会搬到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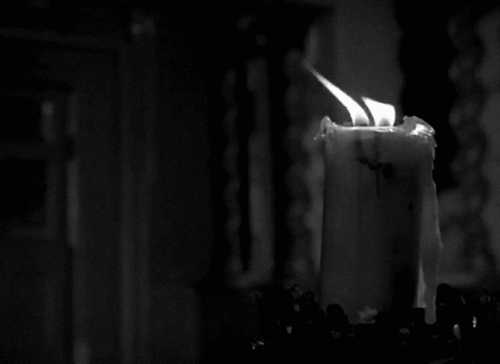
熊老师:
您好!
最近还好吗?访学生活还顺利吧。前日,读了您公众号推送的
《有关江歌案,于是他继续云游,继续吆喝······》
一文,特别欣赏您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悲痛与困难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拒绝再被“凶手”撕裂的生活,一种自主选择不被仇恨吞噬的生活,其实是自救。文章里,您既未为杀人者开脱,也对刘鑫的态度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您或许是认为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您从来不是死刑支持者。您的文字,警醒着我,让我意识到,对留存于心间的事物,美好抑或丑陋,决定权在我。因此,我感叹,或许,我们无法决定心中所“流”(如木心所言,人生如导管,发生的一切都是流过),但绝对有权选择心中所“留”。
作为一名法律人,出于对司法独立的尊重,未经生效判决,对犯罪嫌疑人当定何罪或如何量刑,一般不可能代替法官发言。我只是希望借由您的文字提醒自己与朋友们,我们对心中所留的决定权,从而更自主地生活。万万没有想到,分享了您的文章,我也被拖入了小小的争论。最让我意外的是,一位名牌政法院校毕业的朋友,留言称“理性与仁慈解决不了问题,杀人者斩,若你的至亲被砍十几刀你还会这样嘛······”
(略)
我学过一些心理学知识,当然极为浅显,也会定期去我们当地的监狱为囚犯做一些公益心理疏导。我向来认为,即便杀人者,伤人者,他们内心也是伤痕累累,只是无法处理好这些伤和负面情绪。昨日读到张德芬老师的《是否愿意为自己负责,是衡量人品的关键》,她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江歌事件相关当事人,而她给出的结论似乎与您不谋而合——“暴力只能创造暴力,而爱是所向无敌的”。
您的文字里,我读到的是对江母的不舍,是希望她的人生不被仇恨吞噬,是希望她在经历大悲大痛时仍能看见爱与温暖。很多人都谈到,您所倡导的宽容、慈悲与爱,那是圣人,大家都以“我们只是凡人”作为发泄情绪的理由。我觉得,任何人经历如此重大伤痛,情绪的产生都是自然的。若真正关心江母,或许情绪上的陪伴与支持最重要,虽然这一路只能靠她自己。是的,我们都是凡人,我们有悲伤,也有脆弱;但正因为我们是凡人,我们也拥有宽容与慈悲的力量。
| 阅 读 更 多 文 章
有关江歌案,于是他继续云游,继续吆喝……| 熊培云
问与答:漫长的告别 | 熊培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