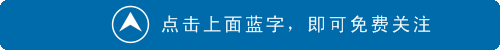
天涯微信号
:
tyzzz01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17年全年征订,108元六期,包六次快递。
点击左侧购买。

本文来源:凤凰网文化
当城市化的大潮席卷全球时,我们如何识别我们所居住或向往的城市?城市究竟有什么独特的气质为我们提供归属感?城市又应该具备什么特质让我们能够认同?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精神?
两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哲学家、曾合著《城市的精神》一书的贝淡宁与艾维纳,做客“启皓对话”,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一道,分享了他们各自对于城市精神的理解。
凤凰文化将活动中的部分言论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整理:徐鹏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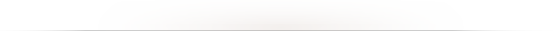
贝淡宁:21世纪,我们的身份认同越来越放在城市层面上
贝淡宁: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是谁?在21世纪如果你问我“我是谁”,我可能会说我是加拿大人,我的朋友是以色列人或者中国人,我们总会先想到国籍。之后人们可能会想到在21世纪,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世界,我们的身份可能是全球性的人,我们认为我们是世界公民。但是并没有很多人会这么想,我们仍然有很强的归属感,我们仍然希望自己归属于某一个社区。当然,我们也希望能有自由,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于某一个社区的依赖感,这样的社区有它的特征,尤其是21世纪的城镇化,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面,城市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认同。
我现在算是一个“老北京”了,我很喜欢北京,但是我不喜欢上海。我的朋友他喜欢耶路撒冷,他不喜欢特拉维夫——也就是以色列另外一个城市。我只是在开玩笑,我有很多好朋友都是上海人。
我爱纽约,这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口号了。我们可以在网络里面搜索,这个口号在很多城市都有,比如我爱北京、我爱上海等等。因为这样的口号表达了非常深的情感,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情感。为什么这样的一句话传播如此广?纽约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城市,在纽约的人有非常强的身份认同,甚至很多时候比他们国家的身份认同要更强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21世纪,我们不是在往上、往更广泛的层面去走,而是越来越多地把我们的身份认同放在城市的层面上或者社区的层面上。
我们并不是喜欢所有的城市,我们会喜欢生活很长时间的城市,往往更青睐有独特气质或有独特身份认同或有独特精神的城市。
比如说你喜欢当地的一些餐馆,并不是麦当劳,而是具有当地特色的餐馆。对于城市来说也是这样,我们喜欢的城市往往有它的独特气质、独特特点、独特精神。在我们的书里,提到了城市应当去推广、增强它的独特气质,因为这样的气质能够增强人们的归属感。
什么是精神或者说什么是气质?精神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词,但是它并不是那么抽象,那是人们讨论的话题。
每一个城市都有独特的价值观,有一些价值观比其它价值观更加重要。
比如说我的家乡蒙特利尔,我们在蒙特利尔会非常关注语言,因为我们有法语有英语,人们很关注语言的争夺;比如说在北京,人们很关心政治,如果你跟北京出租车司机交谈,他们会讨论政治,但是上海可能并不是这样。这就代表了城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精神,并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认同这样的精神,但这样的精神以及气质是人们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城市公民应该具有这种城市精神?在现代城市,比如说北京,我们非常多元化、非常现代化,我们宽容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尊重多元化、现代性。但是我们怎么样获得归属感?一般来说是来自于这个城市本身的。
小城镇或者村庄并不是那么开放的,但是城市更加开放,给我们提供一种比较强烈的归属感。
城市可以把我们现代社会的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
第二个原因,我并不是反对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有时候是很极端的,有时候我们会盲目热爱我们的国家,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爱,在很多国家也会转化为一种比较极端的行为,有时候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如果人们有其它的一种归属感,这样的归属感就能够缓和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这种归属感是更加理性的。比如说纽约人当然会说他们热爱美国,同时他们也会对民族主义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他们并不会有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比如说二战期间,德国纳粹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在纽约不会存在,
城市可以缓和极端或者保守民族主义,我们称之为爱城主义
——这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新词。
像全球气候变化这样重要的议题,美国国家领导人是怎么来看待气候变化的?可能美国国家层面对气候变化不再那么关心了,那么由谁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城市来做,很多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做着非常多的努力。在中国,最高层面就是国家层面在做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努力,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杭州以及其它很多城市,他们也有非常关注环境,他们也在致力于向全球范围内的其它城市学习一些最佳的做法,来解决一些国家层面难以解决的问题。
另外一个认可城市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提到曲阜这个城市,孔子文化非常深厚,也是吸引很多游客去曲阜的原因。当然,这种旅游开发也可能让它过度商业化,但是城市比较理性以及合理地推广城市气质——也就是孔子文化——的话,也可以帮助孔子文化传播。
另外,
城市精神可以使人们更多思考全球影响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比如说古希腊,很多的讨论都是关于雅典精神,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小国家都有不同政治思想,比如说孔子的思想和其他的一些思想都是不一样的,有着非常多的争辩。
我们怎么样定义精神?怎么样给它下一些定义?我们用的是不同的方式来定义。第一个方法,看它的历史。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为了弄懂它的精神、它的气质,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它怎么发展到今天的样子。
同时,也要有客观的衡量。比如说我们要去调查一些当地的人,通过这样的一项调查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在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就会做这样的准备工作,有的城市可能未来有这样客观的指标。
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点,我们取了一个漫步的主题,因为我们漫步的时候会搜集不同人的想法,有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职业,考虑他们的兴趣点以及争论点,通过这样的角度我们就可以了解最初的想法,同时把我们的观点越走越宽。

耶路撒冷/网络图片
艾维纳:不再只思考自己的需求才能和平共处
艾维纳:
各位晚上好。我叫艾维纳。我想和大家分享关于耶路撒冷的一些故事。其实我们也是研究了耶路撒冷差不多四年时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有90万人,同时还是三大宗教的中心。
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城市的气质,
它一个冲突之地,罗马人在两千年之前来到耶路撒冷摧毁了这个城市,一千年之后穆斯林重塑了这所城市。
这些穆斯林是从巴勒斯坦迁过来的,他们想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找到自己的墓地,大家可以看到老的耶路撒冷拥有着很多穆斯林的墓地。
其实耶路撒冷可以说是亡灵的圣地,他们喜欢在这里让尸体下葬成为亡灵之所。
耶路撒冷有主题吗?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一个很美好的所在,包括整个宗教现在还有强大世俗势力,目前正在慢慢缓解。同时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我们虽然有不同的信仰或者相信不同的分支宗教,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团结。公元前19世纪,差不多是四千年前就有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由于出现一些政治的原因,我们把这个城市作为了犹太国的首都,当时耶路撒冷还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不知名的小城,有很多的部落开战。当时这个城市的照片回头来看还是非常漂亮。
它在历史上被不断占领,包括巴比伦,包括基督教,好像任何大国都在历史上侵略过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并不清楚一些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以宗教的名义在耶路撒冷开展杀戮。耶路撒冷对于穆斯林来说是一个圣城,因为穆罕默德在这为大家唱颂了《古兰经》;同时也是基督教的神城,上帝在此留下了宣言,我们还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上帝想考验他的真诚和信仰,要求他杀害自己的孩子以撒献给上帝,亚伯拉罕同意了,他想杀的时候被上帝阻止了,我们用一个单词来描述这种未完成的奉献,就是悲剧;对于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也是耶稣受难的地方。
我们知道一位非常著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1867年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是充满了嘲讽精神的:“耶路撒冷的人口由穆斯林、犹太人、拉丁人、叙利亚人组成,这样的民族构成和他们各自的语言太多了,数不胜数。在我看来地球上所有的种族和肤色都存在于耶路撒冷一万四千人口当中”,这是他当时写的一段话。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人口只有一万四千人,但是他们的多样性太复杂了,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寻找了一些照片,就是20世纪前后的一些照片,我们找不到两张重复照片,或者找不到任何一张照片只由一个种族构成,每一张照片都有各种种族人群存在。
在犹太非常神圣的节日,很多犹太教徒来到耶路撒冷,人们会念祈祷词。同样,穆斯林又有自己的祷告,他们的声音也是很洪亮的。所以这两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并不是非常和谐的,他们在企图相互的竞争。我们听到的时候非常希望世界能够安静下来,但是耶路撒冷一直都是这样的。
191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当时有很多的土耳其人。很多犹太人会到哭墙边上祷告,但是同时还有阿拉伯人来到这里,因为他们希望在这个墙边沿着这条路回家,但是因为有很多犹太人拥挤在这里,他们非常不耐烦,就有争吵以及争斗。有的阿拉伯人说这是一块石头为什么非要在这儿祷告,可以往这个墙往外移一两公里去祷告。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并不是石头,这是有心的石头,这个石头是有精神的,而且这堵墙是非常美的,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耶路撒冷,我们因为太关心这些石头了,往往会忘记了人的存在。
每一个人都非常热爱这座城市,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说耶路撒冷并不是人们很喜欢的城市,不是很干净,不是很有秩序,但是它绝对是人们非常热爱的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热爱这座城市,有的人对于耶路撒冷的热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座城市使他们个人变完整,他们认为他们必须生活在耶路撒冷。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办法去另外一座城市,如果我不带着我的护照不放心,所以我对于耶路撒冷是有很强的归属感。
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这些国家的,信仰是人和上帝、和神性、和永恒的力量之间的联系
。信仰跟宗教是不一样的,宗教是制度化的信仰。
有人就告诉过我说,你知道信仰跟宗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吗,你可以想象有一大群人他们站在路边,有一大群成年人非常高大,站在路上想观看什么事情,但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孩子站在后面完全看不到,所以这个孩子就想跳起来看,这个孩子想请求人们让他挤到前面观看,但是这些人完全忽视了他的存在,这些孩子就是信仰,这些成人就是宗教。
宗教并不能让我们真正遵循我们的信仰。
在耶路撒冷,宗教并不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它是一个公共领域的事情。而且它有其他的一些偏好,人们并不是思考自己做什么,而是希望别人做什么。我作为犹太教徒,我可能会希望穆斯林不要在我祷告的时候去祷告。可能人们有这样的情绪,会希望别人做一些他们希望别人做的事情。这并不是犹太教教义的最初规定,比如《申命记》里面提到了,你们需要怜爱,因为你们也在埃及做过寄居。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怜爱这些陌生人或者说是寄居的人,因为这些陌生人他们经历了一些苦难,所以我们必须要怜爱他们。
怎么样能够和谐共处,我觉得这里可以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明,就是所罗门王的审判。两个妇人来到所罗门王面前,一个人说这个孩子是我的,另外一个人也说这个孩子是我的,他们彼此争夺这个孩子,所罗门王就说我们把孩子一分两半,一人拿一半,一个母亲说好吧,另外一个母亲说不要,让她把孩子抱走,所罗门王说才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你宁愿放弃孩子抚养权也不希望他死去。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表明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和平共处,我们有不同的宗教,彼此争斗,因为我们只是去思考自己的需求,为什么我们不能共同分享耶路撒冷?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我们最终也是兄弟姐妹。

五道口/网络图片
刘瑜:城市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刘瑜:
今天来到这里非常高兴,我参加过很多北京文化活动,这是第一次在这么美丽的场景。有天、有地、有河、有草,还有很多的蚊子。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场景,感觉好像是一个婚礼的场景,而不是一个讲座的场景。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城市的精神”。
在我们的传统里,当国家精神出现的时候,城市精神就消失了。无论是国家精神还是城市精神,是自上而下被规定的。我所理解的城市精神与之相反,它首先是自下而上生发的东西,政府并不是它的作者,每一个街道、每一栋写字楼、每一个小区才是这个城市的精神的作者。
比如北京,可能马化腾是北京精神的作者,可能范雨素也是北京精神的作者。
与之相关,城市精神作者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它是多样的、多元的、碎片化的。不但巴黎和北京不一样,北京和上海也不一样,即便是在北京内部也不一样。我来自于著名宇宙中心五道口,五道口精神和CBD精神非常不一样。每次我到CBD来的时候都觉得进城了,因为这里楼明显更高大上,这里的餐馆明显更好吃,这里的女孩子也穿得更漂亮。相比之下,五道口更像是一个野草园,一个麻辣烫小馆,但是野草园也有野草园的美,麻辣烫也有麻辣烫的味道。
即便是同一个城市,它的城市精神也往往是多元的、碎片化的,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
我所理解城市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是一种消解权力、某种意义上反抗权力的东西。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往往是自由自治的象征。当农奴想逃脱封建主控制时就会逃到城市里,当商人想逃脱封建等级制时就会逃到城市里。看一些相关学术研讨就会分析,为什么有一些西欧国家走向了专制主义的道路,有一些西欧国家走向了相对的宪政主义道路,很大程度上是跟某一个地区是否具有发达的城市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我非常理解贝淡宁所说的爱城主义,尤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我们的社区认同过多地集中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一个丰富、多元的生活除了爱国主义以外,应该有爱省主义、爱市主义、爱县主义、甚至爱村主义,这才是一个丰富、多元的社会认同,是一个更健康的认同。

北京CBD/网络图片
发展全球化的过程中,城市应该成为风向标
刘瑜:
先问贝淡宁,您非常看重儒家精神,也是儒家精神的推手。其实有人说整个儒家基础是在农业社会中,我们有乡村意识,每个人都熟知彼此关系、非常密切,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精神和基本原则能够统治整个社会,原因很简单——你知道每个人,你认识每个人,整个社会生活组织方式是通过血缘关系推开。但是在城市化社会中,整个社会基于现代化精神,我们都是与陌生人打交道。所以怎么样考虑未来儒家发展方式,尤其是在现代化的社会里?
贝淡宁:
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宗教我们都可以追踪到乡村和乡村意识中来,不光是儒家,基督教也是如此。一些伟大的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其实或多或少都是和乡村相关的。我们今天谈的儒家精神,它其实和现代的宽容精神非常相关,他们是一个天然的交集。我们和谐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词语,我一直觉得儒家精神和而不同。我们知道儒家精神还可以考虑到仁爱,我们从家庭开始推及他人,这种和谐精神在现代生活中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瑜: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强调全球化的社会中,人们以两个维度解读全球化,首先是不同文化的冲突增加,第二是多样化强调。您觉得多样化和全球化怎么看待?你是来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文化冲突的前沿地,您怎么样理解全球化?
艾维纳:
我自己有两个角度来回答。一方面我们有时候非常不愿意承认全球化,但全球化可以阻挡战争,我不希望人们太多走向极端爱国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温和的爱国主义即可;另一方面,我又很不赞成分割主义,因为在全球化世界中可以四处投资,可以享受全世界不同的市场商机,可以四处去旅游,虽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确会丧失一些乡土的精神。我总觉得全球化和物质化是相辅相成的,大家想变得更富有。发展全球化的过程中,城市应该成为风向标。

提问部分
观众:
我之前在英国待了很长时间,我观察那个城市的人,看到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面孔。来到北京大概四年时间,我也在CBD附近工作,一眼看过去,看到是建筑、不近人情的道路。我看到一些非常模糊的东西,没有时间以及精力注意。对于您来说有没有这样的观察,这个观察的原则是什么?
刘瑜:
像刚才讲的,北京不同区域的氛围和文化完全不一样。五道口最大的问题,第一到处是人,第二没有人遵守任何交通规则,第三,那边的平均年龄是22岁。
我可以理解你所说的问题,尤其是你说宽阔到不近人情的道路。我记得我刚刚回国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体验,每次过马路像一次探险,飞奔一会儿再停一会儿,再飞奔一会儿再右转,像游戏打通关一样把这个街道过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城市设计不太人性化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因为北京人多,所以马路必须有六车道或者十车道才可以缓解交通问题,导致行人交通不便。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个解释,也是与城市规划者的自上而下眼光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前两天在五道口附近,我发现路边一排小吃店的牌子全部统一换掉了,所有的小店招牌是一模一样的牌子和一模一样的字体,说实话我当时看到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既然是小店,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各美其美呢?为什么要统一的招牌呢?包括北京的城市有点太规范化了,在我个人看来,都是一种过度规划的结果。
观众:
刚才贝教授提到城市的精神,帮助我们更开放、更宽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比如说北京看不起上海人,或者是纽约人看不起其它地方的人,有很多这样情绪存在。这样情绪不正是你们所说的反面吗?
艾维纳:
我先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城市是一个替代,比如说对于国家来说,竞争是军备竞赛,但是城市之间的竞争是不一样的,曼哈顿人可能不喜欢其它地方人,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是积极的,因为这让城市变得更生动。比如说在上海有很多高楼大厦,北京也有很多高楼大厦,上海吸引很多游客,北京可能会想我怎么样吸引更多的游客。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通过城市之间的竞争,对当地城市精神,也包括对当地的经济都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