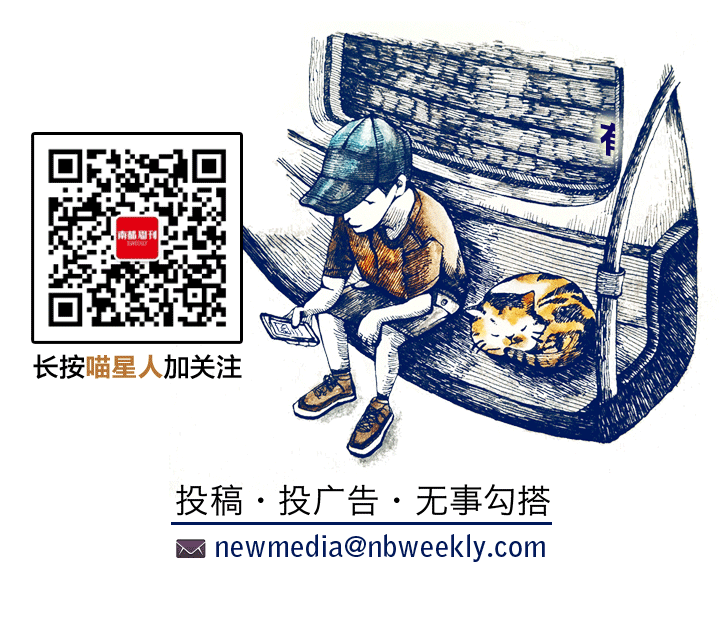封 面
张悦然以一部《茧》兑现了她对自己的期许,但还是不小心透露出一点少女时代的哥特气质,这感觉就好像一个在严肃场合里偷笑的孩子。
文|燕玉涵 摄影|孙海 卢慧明
200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张悦然坐在教室里,一连串带有各种计算机专业术语的英文从她耳边经过,没有一丝停留,或者说,她根本没想留住它们。她才睡了两个小时,天蒙蒙亮时,她刚刚钻进被窝。
她又进入到了那种失控的写作状态里。只要一坐在电脑前,她就好像溺水的人抓住了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再也不愿放开。
从黑夜写到天明,如果不是意识到接下来还要上课,恐怕她还会一直这样坐下去。
落在椅子上的衣服兜里突然发出了「嗞嗞」的声音,震动的手机跟木板碰撞了两下。张悦然回过神,掏出手机。是一条国际短信,来自中国。她一字一句地读完那条信息,随即开始坐立难安,看了一眼时间,距离下课还有五分钟。
铃声响起时,其他人还在收拾着课本,张悦然抄起早已收拾好的书包直奔学校机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开了萌芽论坛的界面——之前发表在《萌芽》杂志上的作品不仅在论坛上引起了热烈讨论,还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
屏幕四周散发出柔和的白色光晕,张悦然「唰」地一下红了眼眶。
挣 脱
张悦然从不穿校服。她总是把校服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经过校门的时候,勉为其难地把它套在自己的衣服外面,一进校门,她又会马上脱掉。在张悦然的意识里,校服是一种泯灭独特个性的东西,「特别特别讨厌」。
「我就是不想跟所有人一样」,张悦然说。
从小到大,张悦然一直成绩很好,还经常担任班干部。当按照循规蹈矩的教育一步一步走到高中的时候,张悦然显然已经对努力扮演好学生的角色感到非常不耐烦了。
她的自我意识变得很强,厌倦千篇一律的集体生活。她读了村上春树、杜拉斯,看了阿尔莫多瓦的电影,还听了一些音乐,这些片段拼凑在一起,一点一点在她的脑海中勾勒出一个有趣的世界。那个世界很酷,却与她的高中时代格格不入。
「高三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离经叛道的边缘了,还好勉强撑下了高中阶段。」
张悦然的叛逆始终是适度的,她的内心甚至还惦记着维系一个还可以的学习成绩,也没有做出什么真正意义上出格的事。
到新加坡以后,她再也不用穿校服,甚至连过校门时套上的那一下都省去了。
按照父亲的意愿,19岁那年,张悦然成为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名新生。好在,她终于自由了,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了济南——那个待腻了的城市。
到新加坡后,她飞快地打了耳洞,但打耳洞带来的短暂的愉悦感并没能支撑太久。她发现即使刚刚从一个集体的约束中挣脱出来,却还是没有得到她想要的那种自由。背井离乡的孤独感开始蔓延,读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每天面对着枯燥的代码,成绩下滑得厉害,这种生活让张悦然感到很痛苦。她挣扎着,想抓住一些东西。
她开始写作。每天写作的时间越来越久,也越来越失控。到最后她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写作上,甚至快不能维持基本的学业。
她想起了儿时兴冲冲写好的无数个故事的开头,想起了发表在高中校刊上的小说,想起了让她获得了一点荣誉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想起了她在萌芽论坛上收获的读者的支持。她发现,原来写作一直陪伴着她。「在那个环境里面,就跟写作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这也让我比较快地就选择了写作这件事情。」
除了写作,张悦然也在进行大量的阅读,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内心慢慢地形成了一些标准。在当时那个青春文学盛行的时代,表面看起来,张悦然好像是属于那里的一员。「但是其实我从来都不是在那个框架下,或者说不是在那样的一种追求里面去写作的。」张悦然说。
2004年,张悦然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樱桃之远》,这一次她没有再随随便便地扔掉那个开头,而是第一次走过了一段完整的道路。
然而在写第二部长篇《水仙已乘鲤鱼去》时,张悦然又到了一个低谷时期。那段时间,她自闭到不愿意出门,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作。
「因为当时的环境和写作状态,它可能是一个太把自己的内部情感放大和表达出来的作品,感情太强烈,又特别坦白,22岁的我坦白到让三十多岁的我看来觉得很羞愧。」
对于那时候的张悦然来说,写作是她的一种诉求,更是她情感的出入口。
大学毕业那年,张悦然已经出版了五本书。第二年,《誓鸟》出版,首印20万册三周卖光。这个成功对于一个24岁的女孩来说,好像来得有点猝不及防。
隔 绝
张悦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为了一名作家,「作家这个身份,如同一件忽然派发下来的制服,并不能算合身。」
她开始需要不停地奔波于各种文学之外的活动,张悦然忽然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作家的角色。除了单纯的写作以外,她不仅要学会经营自己的作家身份,还要维系自己的名声。
她发现自己无法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大学的时候,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从我不喜欢的专业、我不喜欢的生活里面挣脱出来,然后过上了一种我觉得自由的生活。结果很快发现这个生活也是套路。」
彼时,张悦然依旧处于跟「写作」的蜜月期,每天写得很多,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她也感受到了压力。这个压力并非来自出版界,而是来自一种写作的惯性。这种惯性让她开始想放慢脚步,停歇下来。
「从大二开始写作,我就已经变成一个作家,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份别的工作,也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除了写作就是以作家身份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只有24岁左右的人来说是挺可怕的。」
一直以来都被文学保护着的张悦然不甘于就此被隔绝,这一次,她决定跳到保护层的外面吸收现实的养分。她为自己寻觅了两个新的身份——杂志《鲤》的主编和高校教师。
「我觉得不能写和生活脱离关系的东西,只有把一切放到现实的层面里去,让它在现实中展现出光芒才有用。」 就这样,她卸下了作家的身份,全情投入到新的身份中。
她开始编杂志,不时也会写一些小短篇。她跟周围的人平等地交流,而不再以作家的视角观察别人的疾苦。
在去学校教课的第一个学期,张悦然还很不适应。那种自由而没有规律的生活过了太久,「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需要准时到那个程度,因为我们晚几分钟就算教学事故,要特别特别地准时。」一个学期下来,张悦然焦头烂额,甚至觉得当老师比小时候当学生还累。
这样几年下来,张悦然似乎真的从很久之前那个不切实际而又懒洋洋的文艺少女中慢慢抽离出来,在这些真实的身份里工作和生活着,感受着这些身份带给她的种种烦恼和快乐。
教师工作也成为一个新的窗口,她开始在这个全新的角色中看待世界。「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体验,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因为作家这个身份是一个常常离开地面、架空的状态。你常常凭空想象别人的烦恼,把自己代入到别人的身份里,但当你真的有另外一个身份的时候,你感受到的东西是特别真实的。」
就这样突然停下来,曾经一年能够写出两部长篇佳作的高产作家,看似在做着跟写作不太相关的事,难免会有人问起。每当这时候,张悦然就会觉得很痛苦,「其实我也在写,只不过写得很慢。」随即而来的是一连串的追问和自我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写」,「到底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张悦然开始审视自己。
好在写作对于张悦然来说是一件内部的事情。即使经常自我怀疑到被消极的情绪裹挟,但当她真正沉入到小说创作里的时候,就像又回到了文学的保护壳里,把自己跟外界的纷杂隔绝开来。
「就有点像沉入了一个水底,你憋一口气扎入水底,其实外界那些声音你就听不到了。」
她喜欢那种扎到水里的感觉,与世隔绝,安静而专注。

对 话
1977年,张悦然的父亲告别了他工作的粮食局车队,走进学校的大门。那时,中文系的他还怀揣着一个文学梦,于是写了第一篇小说《钉子》,源自他少年时代目睹的一个真实事件。隔壁楼的一个医生在文革批斗中,被人往脑袋里摁入了一枚钉子,之后渐渐失去言语和行动能力,变成了植物人。
这篇小说当时由于「调子太灰」而没有被采用。时隔多年,他无意中提到这篇小说和钉子的故事,没想到却被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张悦然听到了。这恐怕是她童年里听到过最惊悚的故事了。这颗可怕的钉子也牢牢地钉在了她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张悦然向父亲宣布要把钉子的故事写成小说时,父亲并没有当回事。直到他发现,张悦然竟跑到那间医院做了调查。
2011年除夕夜,接近零点的时候,张悦然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点亮整个夜空的焰火,在一片喧闹声中写下了《茧》的开头。在《茧》的故事里,男女主人公程恭和李佳栖以双声部的叙述方式讲述了文革背景下钉子案件所引起的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和命运纠葛。
书中的女主人公李佳栖对于父亲有着强烈的情感,她用尽全部的力气去追寻父亲的故事,对父亲的历史和过去交付了她全部的感情,然而最终也无法得到回应。
看完《茧》,有的人认为李佳栖太「作」了,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自己的历史。
「其实我写的主人公都不太讨人喜欢」,张悦然说,「
我不太会在写一个小说的时候考虑一定要塑造特别可爱或讨人喜欢的人物。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牵动读者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而是她在情感中所体现的突破。
就像李佳栖,她是有很多地方不让人喜欢,但她对父亲的感情很真挚,她在这个感情里一直在突破自己的极限,这种试图和父辈建立连接的努力和情感使她变得完整,使她找到了某种力量。」
父亲的意象在张悦然以往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很多我以前的小说里面其实也充满了‘我’跟父亲的关系。‘父亲’在我的小说中肯定是多义的,他既是作为我生身父亲的一个存在,也是作为更大的父权的、阳性的、甚至国家的象征,更是一种对于少女时代的我形成某种压制、或者我想逾越的一个对象。」
儿时的张悦然成长在一个父权环境中。这个环境本身的色彩也随之确定。小的时候,她会觉得妈妈跟自己是同一边的,不是站在对面需要去反抗的那个人。而那个她需要去对话、需要去看清楚的人则永远可能是父亲的形象。
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答谢辞里,张悦然讲道:
「《茧》这部小说中所回到的两个历史现场,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分别站着两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和祖父。在所有亲人里面,我最不熟悉的是这两个人,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很沉默。那种沉默神秘而威严,阻碍了我们之间的交流。」
而这种沉默制造的威严则是张悦然一直想用任何方法去瓦解的。因为他们的沉默,她更想让他们打开心扉,跟她知无不言地讲起过去的故事。
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中,张悦然和她的爷爷才有了一些迟来的交谈。她把爷爷的一些回忆写进了小说里,成为了一种恒久的存在,也算作一种纪念。
同样沉默的父亲在张悦然心里一直以来都是一堵很高的墙,在之前的很多小说中,她都有一种感觉——她在跟这样一堵高墙对话,或是赤手空拳地去打这堵高墙,试图把它破坏掉,又或者试图从它上面翻过去。
然而在《茧》里面,父亲的形象却变弱了。「他不再是一个强大的象征,反而变成了一个有点虚弱的、走远了的背影这种感觉。父亲他不再是一个特别高大的形象,因为你长大了,你看清楚了,你知道他也是软弱的。你知道那些所谓的带有男权色彩的压制着你的东西,它可能也是会坍塌的。所以我觉得《茧》里父亲的这个形象可能比之前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完整。」
当问到父亲对于《茧》的评价时,张悦然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我也没有问过他,他也没有跟我讲,我们就假装没有这个事情一样。」
所以当张悦然想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一直渴望的跟父辈的对话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有些话不能在现实中说,为什么非要用写作的方式去说呢。
张悦然也曾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她发现:「小时候已经形成的那种沟通模式是非常难以打破的,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以这样的方式说话,习惯了只说这些话,习惯了去有所保留地跟对方交流。这真的非常难以改变。但是在小说里面,好像就完成了某种东西的一个重建。」
有很多现实中永远无法进行的交谈,就这样在小说的时空里得以完成。
个 体
「读完大学再回去济南……」
「没有回去过。」
张悦然打断了我。
我诧异了一下,想再次确认,「没有回去过?」
张悦然突然意识到,是我们在「回去」这个词上产生了理解偏差,随即解释道,「肯定回到过,毕业以后我就在北京定居了。那个回去不是回去居住,因为父母住在那里,是一种造访吧,造访自己童年现场的感觉。」
济南在张悦然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北方城市」。从这直白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描述中,仿佛能感到她对于这个城市那股淡淡的疏离感。
张悦然以往的作品里从未有过故乡的概念,在新作《茧》里面,她第一次写到了故乡。小说中故事发生地南院的原型正是她成长的地方——山东大学家属院。
但张悦然笔下这个的故乡与上一代作家笔下的故乡却不一样,不像高密之于莫言,也不像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这个故乡并不是一个有着那么强烈的独特属性的地方,只是她童年的发生地。
「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流动的空气,我记忆它的方式是一种气息的记忆,并不是我对那个地方深怀独特的感情。就是我的童年没法在别处发生,它只能发生在那个地方,它也只能用那样一种空气、那样一种色彩。」
在张悦然看来,故乡是童年里面的一种空气,那个地方是哪里却并不重要。「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不是一群人的生活,是一个个体。故乡永远是一个集体的故乡,是一个地方。而童年则是一个个体的概念。」
在创作《茧》之前,张悦然就对历史很感兴趣,她尤其喜欢具体研究个体在历史中的关系。
她想起沉默寡言的爷爷其实参加过远征军,然后开始自己想象爷爷的历史。她还把爷爷的这段经历安插在《茧》里面李冀生院士的身上,并在小说里为他设想人生的另一种结局。
「我蛮喜欢去把人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层面去考虑。」张悦然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历史就像一道光线,谁也无法描述这道光线的样子,因为它无法被触摸。只有当这道光线投射到一个人的身上,你才可以通过这个人看到这道光线是亮的还是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质感。但若是脱离了这个人的存在,脱离了这个个体,就没法描述这道光线。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凭空地去描述历史,历史这个概念在小说里面必须是有个体承载的。」
就像在《茧》中,历史是散落在时空中的碎片,正是李佳栖和程恭这些个体的情感把它们黏合在一起,让读者产生了共情。「历史啊文革啊跟我的主要人物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写的是几个个体的人他们命运的变化。」
张悦然最近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大乔小乔》,讲的是一个关于两姐妹计划生育的故事。这在别人看来,尤其是她以前的读者看来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张悦然会写一个和计划生育有关系的故事?但其实她只是听闻了这样一对姐妹的故事,对具体的人物产生了兴趣。
「无论写哪个小说,打动我的都是某个人物在那个处境中的感觉,我不禁会想,那时候他该多痛苦啊,那时候他多么地怪诞啊,那时候他多么地难堪啊。我都会先找到这样一个入口进入到那个人的那个处境。小说永远的立足点在于具体人物的情感,这是最重要的。」
失 效
作为「80后」那一代青年作家的代表,直到今天,张悦然也依然常常和这个标签捆绑在一起。
在她的新作《茧》的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现在80后这个词挺失效的,而且你会发现,当我们从一代人经验的角度上去谈问题的时候,你首先面对的可能是一代人内部的严重的分歧和分裂,你从这个起点出发不一定走到那样的结局。」
对于这个在自己身上贴了这么久的标签,张悦然坦然道:「80后早已不是最初的那个时候了,他们已经是正在走向成熟的写作者。其实去找80后的共同点是一件可能比找他们的不同之处要更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其实很不同。非在他们身上找共同点,然后把他们放在标签底下,我觉得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就像风格这件事情对于早期的张悦然来说曾经非常重要。在写《誓鸟》的时候,她曾不断地确认,确保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感受到这种风格,否则她就会觉得好像失去了自己在写作中的属性。
「因为写作这件事它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充满的挫败和失败的尝试。所以我们永远在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去触碰自己风格的边界,拓展到我们曾经不能抵达的地方。」
曾经那个喜欢装饰想穿华丽裙子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懂得要用最朴素的词写最特别的句子。「去掉多余的东西,让它简单一些,直接一些。」
张悦然以一部《茧》兑现了她对自己的期许,但还是不小心透露出一点少女时代的哥特气质。在《茧》里面,我们依然能找到很多哥特式的东西。比如死人塔的场景,比如两个小孩子以病房里的植物人为道具玩过家家。这感觉就好像一个在严肃场合里偷笑的孩子,褪去沉重和浮华,她仿佛还是那个叛逆的哥特少女。
「我觉得这种气质真的是天生的,也可能跟阅读有关,但这个阅读是很小的时候读一些童话故事时就已经形成的东西,从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流露出来了,后来到《誓鸟》的时候就表现得很充分。但哥特文学其实是狭窄的,它很难走向一个更开阔的领域。所以我后来的小说,这个气质就在变弱,但是你说它完全不存在,我觉得不可能。」
张悦然就这样始终夹带着少女时代残存的那一丝哥特气质越来越接近自己寻觅的文学,就像她调侃的那样——哪个作品都会被说成是转型,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都转了三百六十度,感觉又转回去了。
她并没觉得这次是一次煞有介事的转型,「转型真的是一个特别外部的词。对于作家来说,写作中所有的变化都是有迹可循、循序渐进的,所以不存在这种所谓这种忽然之间的转型。一个作家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型可以去塑造,她就是她自己。」
文章选自《南都周刊》2017年第11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