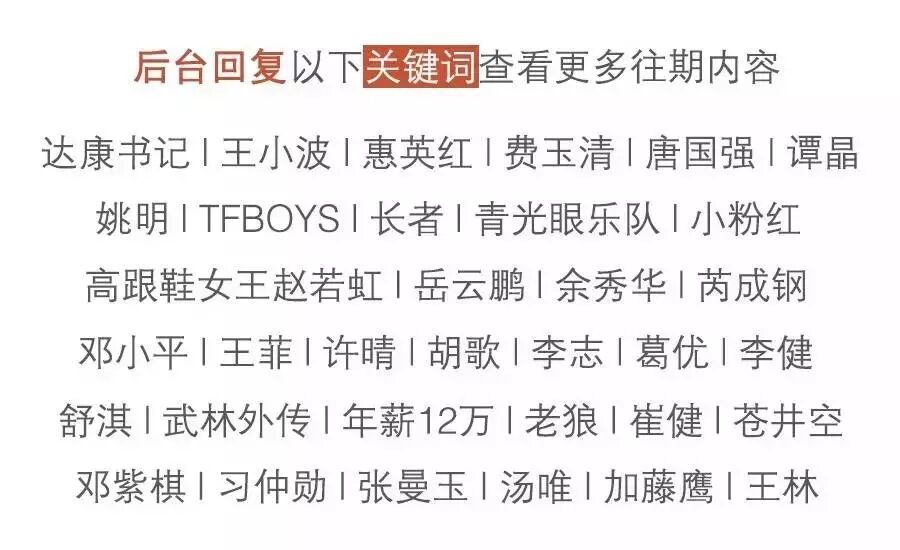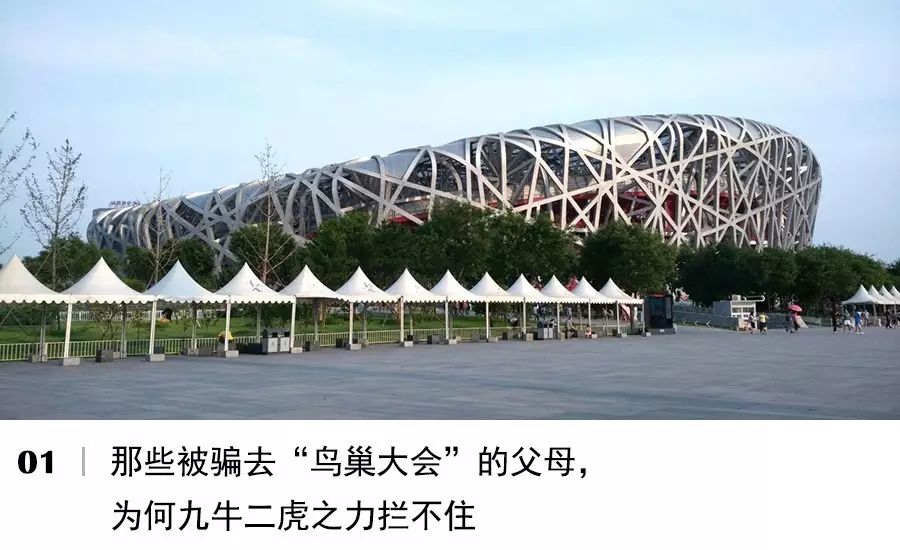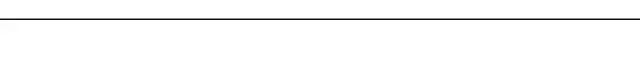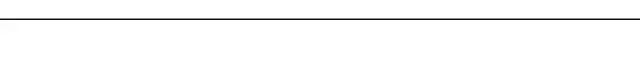正常的应用都希望流量和使用频次越多越好,而“团圆”的终极诉求是,有一天人们不再需要它,那才是“团圆”最好的结局。
文
✎
施展萍
图
✎
小黑
2016年5月15日,“团圆”正式上线时,马云发了条微博:“改变世界的不是技术,是技术背后的梦想和责任。互联网打拐,阿里巴巴为有这样的同事而骄傲。”
“团圆”是公安部与阿里巴巴集团(以下简称“阿里”)合作的项目,另一个更长的名字叫“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但起初,双方的沟通并不顺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告诉《博客天下》,当时的阿里技术人员听不懂自己的需求。“团圆”公益项目负责人、阿里巴巴集团首席风险官刘振飞同样提到,对阿里而言,建立“团圆”系统,技术上并无太大难度,真正的难度在于搞清楚“团圆”项目的需求是什么。比如,儿童被拐、走失案件发生时,民警上传相关信息的步骤与系统框架等程序设置如何变成具体产品,双方存在理解上的差异。
一个抽象的需求要被做成应用,离不开各种细节。走失儿童的照片格式、名字字节数、年龄限制,这些都必须明确下来。
公安民警天天琢磨怎么打拐,阿里技术人员则天天琢磨怎么写代码。为此,“团圆”公益项目组成员一次次飞往北京与公安部沟通,民警性格直爽,技术人员也有自己的主见,“一开始互掐,吵着吵着就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该做成什么样了”,刘振飞对《博客天下》说,产品的最终形态是一边吵一边磨合出炉的。

▵“团圆”公益项目负责人、阿里巴巴集团首席风险官刘振飞
“团圆”上线半个月后,河南省辉县市的连叶经历了让她心惊动魄的17个小时。
17小时前,她3岁的儿子连成穿着一件蓝色秋衣、白色长裤到小区楼下玩耍。17小时后,重新回到连叶怀中的连成身上穿着一条粉色裙子。
当天上午,当连成与爷爷连纪在小区楼下玩耍时,一名圆脸、微胖的中年女人过来,和爷孙二人玩了起来。20分钟后,连纪想到地下室整理东西,中年女人对他说:“你先忙吧,我跟小孩玩一会儿。”
等连纪再次出现在地面,连成和那个中年女人都不见了。连纪隐约记得,他曾听到孙子喊过一句:“你可要给买糖啊。”事后追溯,危险的信号曾在那一刻警示过他。
连成被拐后,家中亲戚几乎全部出动寻找,他们去往车站,进入商场,向商铺店员和行人打听,并很快报警。民警秦志丹记得,报案时,连成的二爷几乎说不出话。
在警方调出的小区楼下的监控录像里,连叶清晰地看见儿子跟在那个中年女人身后。女人时不时回过头来哄他几句,儿子就跟着她,一步步走出监控视频外。
连叶从未见过那个女人。后来有邻居告诉她,女人已在此地徘徊过一段时间了,甚至曾试图带走楼下卖菜人家的孙女。

连叶开始不停地哭泣、抽搐,感到命运对自己太过刻薄。她还有个11岁的女儿,患有免疫性血小板紫癜症。儿子被拐当天,女儿在医院住院,连叶怀着巨大的悲痛和恐惧一边在医院陪伴女儿,一边等待消息。
连叶不敢猜想儿子究竟去了哪,会不会遭遇危险,具体的想象容易让人害怕。杂乱的思绪中,只有一个念头是确定的——如果连成找不回来,这个家就完了。
普通人永远无法体会丢失孩子的痛苦。
安徽省公安厅打拐办副主任唐庆美参与打拐工作十几年,她认同一句话:“拐卖是超越谋杀的犯罪。”唐庆美见过太多因丢失孩子陷入困境的家庭。有些人因此失去工作,有些人精神失常,还有些妻离子散、抑郁而终。
唐庆美认识电影《失孤》中雷泽宽一角的原型郭刚堂。郭刚堂告诉她,自己从未在家过过春节。每年春节,他都在寻子路上。
郭刚堂不知儿子在哪儿过年,是否吃饱穿暖。他必须在路上,仿佛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被拐的孩子。
被拐儿童的家庭面对的是未知。时间不会消除伤痛,只会将未知无限放大,希望与失望屡屡交织,信心不断燃起又破灭。
那种惶恐的感觉让连叶直到现在都心有余悸。一年后,重述儿子走失的场景时,连叶话刚到嘴边,眼眶就红了。
一年前的5月30日是让她心碎的一天。当天,接到报案后,辉县市公安局启动了重大案件侦破机制,成立专案组,刑事侦查大队30多名警察全部出动。
连成被拐的消息很快被通报到新乡市。下午1点左右,新乡市公安局在“团圆”系统上发布了连成走失的信息。一小时内,连成的年龄、外貌特征、走失地点被推送到10多个APP上。
消息被推送后,不断有人打电话到公安局提供线索。关键线索来自一位出租车司机。当天下午,他载过两位乘客——一位中年女人带着个小男孩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刚上车,男孩就不停地哭泣,女人的表情有些怪异。他杵着方向盘,用手机悄悄拍下女人的侧脸。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得知,女人带着男孩去了辉县的旧车站。从旧车站调看视频,发现她带着孩子坐上了开往新乡市的汽车。
夜里8点左右,在嫌疑人的落脚点,警方将被拐的连成解救。

连成回到连叶怀里,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多。在辉县与新乡交界处的加油站,儿子扑向她,手中攥着一包饼干,穿着嫌犯为掩人耳目为他换上的粉色裙子。
回家后,连叶将那条裙子扔了。
如果不是那条从团圆系统发出的消息,找回孩子的过程也许会更曲折些。
在与互联网结合以前,寻找走失儿童依靠的往往是寻人启事、线索排查,对人与人的沟通依赖性强,但这往往使案件侦破陷入困境。
毕节市织金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是贵州的金三角地带,连接着昆明与贵阳。
当地警方透露,改革开放初期,生活于此的人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传统农业。织金贫困、闭塞,是毒品问题的蔓延地,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非常原始的作案手法和非常原始的侦破手法。”织金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李健告诉《博客天下》,过去,在织金警方侦破的多数案件中,嫌疑人的作案方法往往是内外勾结,外部有市场需求,内部有中间人帮助勾连。
拐卖妇女靠的通常是欺骗,向她们描述一个美好的外部世界,说服她们离开;拐卖儿童则主要靠哄骗,许诺给孩子买东西,在脱离村庄地界后,立刻乘车离开。
等到父母发现孩子不在身边时,距离发案时间已经过去很久。那时,织金县还未普及电话,连传呼机都稀少,地方闭塞且多山路,从村里走到派出所,往往要耗费两三个小时,远的地方要走上一天。
相对应的,警方解救被拐人员的方法也很原始。拐卖是没有现场的犯罪,无法获得指纹等常规线索,只能根据受害家庭或目击者的描述,找到中间人,再通过中间人,找到买家。这当中的每个环节都可能突然断掉,导致侦破无法继续。
拐卖案件往往是跨区域作案,解救妇女儿童时,通常需要其他地方警力的合作。
但在过去,这种合作并不顺畅。李健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局里有一次去安徽打拐,曾被当地村民用棍棒和刀具团团围住。
现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陈士渠告诉《博客天下》,过去,公安机关会用发放寻人启事的方法寻找线索,效率有限,将东西印出来再贴出去需要时间,风吹雨淋下,纸张很容易破掉。

▵现任公安局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陈士渠
2007年,公安部刑侦局命案处单独成立打拐办公室。陈士渠受命任打拐办主任。
工作中,他察觉到传统打拐方式的滞后,“所以后来我们也在研究要利用一个高科技信息化的手段迅速发布信息。”陈士渠说,“团圆”系统正是这样诞生的。
2015年11月中旬,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提出建设这一平台的构想,与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沟通。11月25日,阿里“团圆”项目志愿者团队成立。
2016年5月13日,“团圆”系统线上测试。当晚,一位名为“吉斯么吃作”的彝族女孩走失的消息被传到系统上。这个“奇怪”的名字一度让孟庆甜误以为这只是又一次线上测试,但她很快确认消息属实。
这一天,两岁的吉斯么吃作跟着父母从四川出发,在漫长的火车旅程后经过河北衡水火车站,因为太过疲惫,吉斯么吃作的父母在车上睡着,醒来时,女儿不见了。
衡水火车站附近100公里的手机用户迅速收到了团圆系统通过各个APP客户端发出的紧急推送。线索纷至沓来,5月15日,女孩在河南郑州被警方解救。
这是“团圆”系统发布的第一条儿童失踪信息。因为互联网的介入,寻找走失儿童的效率明显提升。
“团圆”有个推送原则,以儿童失踪地为中心,失踪1小时内,定向推送到方圆100公里范围内;失踪2小时内,定向推送到方圆200公里范围内;失踪3小时内,定向推送到方圆300公里范围内;失踪超过3小时,定向推送到方圆500公里范围内。
“‘团圆’系统的发布范围是有限的,实际上超过500公里之后范围就大了,发得太多没有太大意义。越近的时候发,意义越大,对无关群众的干扰越少。这主要解决初期的发现线索作用。”陈士渠说,一条儿童失踪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发布后,也许会有上百万、上千万人接收到消息,这意味着,在嫌犯身边,有许多人关注着他,嫌犯与孩子都可能被发现,从而帮助警方以最快的速度将孩子解救出来,“‘团圆’的意义在于,它织密了儿童保护的体系。”
截止2017年5月15日,“团圆”系统共发布失踪儿童信息1317条,找回1274人,找回率为96.74%。在这1274人中,离家出走的有750人,迷路192人,有75名儿童不幸溺亡,29人遇害。
此前,有媒体称中国每年被拐儿童有20万人。陈士渠想知道这一说法的确切来源,经过调查,发现是媒体听走失儿童的家长说的。他认为这一数据并不可靠。“信息透明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力量。”刘振飞说。
在团圆APP上,离家出走占了走失儿童中的大多数。
2017年3月8日晚11点,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民警唐远接到单位电话,有个12岁的小男孩走失了。唐远与派出所联系,找家长要了孩子的基本信息,凌晨1:10,她将消息在“团圆”上发送出去。
第二天下午,管庄附近一家超市的店员看到了走失的孩子,然后拨通了他母亲的电话。
小男孩是跟家里吵架后离家出走的,他从管庄附近的家中走到天安门,又从天安门返回管庄,最终被发现。
唐远告诉《博客天下》,在她所发布的儿童走失信息中,90%都是离家出走。
不同地方显示出细微的差异。在河南省辉县市,秦志丹每周都会碰到一两起群众求助。那些走失的孩子多数是贪玩忘了回家。有一回,全刑警队出动,在走失儿童的村里来回找。那天村里停电,无法发送广播,一整天下来,都没有找到。等到夜里,电来了,广播一播放,孩子就出现了,原来他在同学家睡觉,睡了一天没去上学。
无论在哪类儿童走失事件中,时间一样显得紧迫。越快找到孩子,意味着孩子遇到危险的可能性越小。
在安徽,2016年5月15日“团圆”上线至今,通过系统发布失踪儿童信息133条,找回132人,其中有8人溺水身亡。“这个比例并不小。”唐庆美说。
她曾亲眼目睹这样的场景。几年前,一对双胞胎小男孩失踪了,找了一夜没找到,第二天,唐庆美开车往失踪地赶,途中听说,孩子在离家门口50米处远的小沟里淹死了。
赶到现场时,警察正将孩子的尸体往上捞。孩子的小脸圆圆的,屁股圆圆的,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场景——“船要沉了,孩子慢慢地掉入海底,脸还薄薄的、圆圆的,这么可爱的孩子,捞上来以后就放在旁边的小草坪上。”唐庆美很难过。
时间的紧迫性还体现在那些悬而未决的积案上。
过去,因为打拐手段有限,不少拐卖案件发生后未能及时侦破。
案发时间过去太久,许多中间人已经过世,而孩子被拐时往往年幼,没有记忆,寻亲像大海捞针一样艰难。
2009年,公安部建立DNA数据库,此后,通过被拐儿童与父母双方的血样比对,4600多名被拐儿童找到了家,这当中,有些案件发生在50多年前。
即便找回被拐的孩子,亲人的团聚也不总是简单。
唐庆美曾帮助安徽宿州一对姓郑的夫妇寻找他们被拐的女儿。2014年,当她找到孩子郑芳时,郑芳已在浙江舟山的一个小岛上生活了14年。那年,她16岁,即将参考中考。在过去的14年里,她的养父与奶奶视她为掌上明珠。
因为担心强行将孩子带走会令她崩溃,唐庆美安排双方在孩子的养父家吃了顿饭。
面对陌生的亲生父母,郑芳始终牢牢抓住“奶奶”的手,母亲郑逸与哥哥给郑芳买了件大红色的滑雪衫,“奶奶”一把将衣服丢回来,说:“我们家的孩子不穿别人家的衣服。”
郑芳不肯开口喊郑逸“妈妈”,从房间往外冲,一边嘟囔:“这家人怎么这样,再逼我,我就跳海了。”
唐庆美很理解她,女孩在南方长大,长得漂亮又洋气,对来自农村的生母和同行的大妈又搂又抱劝她回安徽的架势很是反感。她也理解郑逸。郑逸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不认自己。当唐庆美劝她先回安徽时,郑逸一屁股坐在郑芳养父家楼下,大哭起来:“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儿对面租一间房,就在这儿看着她。”
唐庆美好不容易劝郑逸离开。次日,他们离开舟山时,郑芳没有出现。后来,又经过整整3年的沟通,郑芳才决定回趟安徽看一看亲生父母。
这3年里,唐庆美告诉了郑芳父母这些年寻找她的艰难过程。
郑芳问她:“我奶奶跟我说,我是被他们家卖掉的。”
唐庆美告诉她,事实并非如此。在郑芳两岁半的一个夏天,夜里8点多,郑逸与丈夫干了一天农活,十分疲惫,就在家门口铺了一张床,父亲搂着儿子,郑逸搂着女儿入睡。半夜,母亲臂弯里的孩子被偷走了。
许多年后,唐庆美带领警员顺线追踪,竟找到当年的人贩子。人贩子是郑家邻村的村民,想偷孩子卖钱,当晚抱走孩子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怀中的孩子是男是女,他一路狂奔到南京,将女孩卖给了后来郑芳养父的姐姐。
“你知道女孩卖了多少钱吗?”唐庆美自问自答,“60块钱,就是这60块钱,造成了这个家庭的骨肉分离。”
每个被拐儿童的家庭都有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张柱在24年后才找回贵州织金的亲生父母。这24年里,他的母亲因为与丈夫吵得不可开交,改嫁四川。父亲张隐常年在外寻找张柱。家中剩下的3个孩子无人照料,其中一个男孩,在18岁时发高烧,由于医治不及时,最终去世。
张隐是个土郎中,寻子路上,他用给人开药的方式赚取上路的费用。出于绝望,张隐开始吸毒,他一共进了3次监狱才将毒戒掉。
一次,他在监狱里听狱友说,曾有人将一位男孩拐到云南去。仅凭这样的线索,他在出狱后,立刻去了云南寻找张柱的下落,未果。
被拐走的张柱日子也不顺利。被送到河南新乡市原阳县一户人家时,张柱几乎奄奄一息。他隐约记得自己有个小名叫“小浪”,发现自己更喜欢吃米饭而不是河南人爱吃的面条,他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努力地抓住这点记忆。
张柱的养父母不许别人叫张柱“小浪”。张柱从小就对自己的身世有阴影,因为村里总有人对他说:“你是别人捡来的,你父母不要你了。”
张柱还曾被绑架过。他被绑了整整6天,忍受饥饿和殴打,最终,养父母凑齐了绑匪要的50块钱,他才得以死里逃生。
2012年,张柱去广东学习美容美发,第一次知道“宝贝回家”网站,将自己的信息填写了上去,不久便接到原阳县公安局的电话,让他回去采血样。
2016年,张隐说服嫁到四川的前妻回织金采集血样入库。很快,通过血样比对,张隐找到了张柱。
父子俩见面是在原阳县宾馆。得知第二天能见到儿子,张隐激动得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他就在宾馆走廊上徘徊,远远地看见有个年轻人过来,特别激动。张隐一眼认出是张柱,立马冲上去:“你是小浪?”双方抱头痛哭。
类似的故事,唐庆美与孟庆甜听过太多。孟庆甜在2007年开始打拐工作,在她看来,过去10年,是打拐工作的黄金十年。
她喜欢这份工作,因为“让亲人团圆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10年来,她发现群众的力量、民警的转变、机制的改革,很多地方从不重视打拐到现在人人都有了反拐的意识。孟庆甜的生活也有了些改变,她将迎来自己的孩子。
5月15日是“团圆”上线一周年的日子,即将发布3.0版本。新版本的“团圆”会接入钱盾、国家应急广播、ofo等更多APP。
在刘振飞的构想中,“团圆”能做的还远不止于帮助寻找失踪儿童,如果社会各界能形成合力,还可以扩大功能用于寻找老人丢失、家长教育、心理辅导等。“但需要强大的运营方,能将资金、技术、爱心人士等多方面力量凝聚在一起,共同推进。”
刘振飞认为,正常的应用都希望流量和使用频次越多越好,而“团圆”的终极诉求是,有一天人们不再需要它,那才是“团圆”最好的结局。
(文中连成、连纪、连叶、郑芳、郑逸、张柱、张隐为化名)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总第243期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转载授权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