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余秀华的诗歌舞蹈剧场《万吨月色》在上海首演。
余秀华的7首诗歌被“翻译”成了舞蹈,由她和几位专业舞者配合着表演出来。
是的,余秀华跳舞了。
在观看过程中,很多观众落泪了。
他们在诗人笨拙的舞步中,看到了自己内心的脆弱和与这个世界拉扯的疲惫,还有,由此而生的力量。

正如余秀华的经纪人所说的:
她的姿态谈不上优美,甚至有一些笨拙,让人时刻担心她会跌倒,但那跌跌撞撞的姿态反而生发出一种奇特的、只属于她本人的韵律与美感,不可抑制的生命力如同早春的新芽一般破土而出。
与此同时,周围也有质疑声,有人不客气地说:
“余秀华跳得就像一个小丑,一个人为什么要展现自己的短板。”
这位从小灵魂就被身体所禁锢的诗人,听说有人请她去表演舞蹈,第一反应也是诧异:
“跳舞?站都站不稳,跳什么舞啊!”
父亲想来上海看首演,她也以“跳得不好看”为由拒绝了。
但她还是站在了舞台上,试探着身体所能伸展开的极限,摸索着自身与命运对抗的潜力。
这四十多年来,她一直在与命运抗争,并始终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潇洒恣意地活着。

余秀华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在2014年之前,石牌镇最出名的是豆腐。
如今,村里的指示牌和墙壁上都印着余秀华的诗,双层洋房一排排矗立着,其中有一座老房子跟周围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那是余秀华旧居,如今已经成为了当地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部分。
1976年,余秀华就降生在这里。
请来的接生婆没有经验,再加上没有消毒设备,小婴儿小脑受损了。
命是捡回来了,残缺的身体却让她从小就生活在异样的眼神和无情的嘲笑之中。

从家到学校的路,对余秀华来说,是如此崎岖而漫长。
一开始,她用拐杖走路,同学们嘲笑她拄拐难看,像要饭的,她一气之下就把拐杖扔了。
走不动了,那就爬,哪怕爬得头破血流,手足生茧。
受不住了,她向母亲哭诉:“你为什么把我生成这样?”
她不甘心自己的与众不同,不甘心命运对她的戏弄,她要抗争,用努力读书的方式。
然而,因为身体的限制,别的孩子能轻松办到的事,对她来说却是难如登天。
刚开始学写字时,由于无法控制手部的稳定,字写得龙飞凤舞。
多次失败中,她琢磨出一个办法:用左手压住右手腕,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中考的时候差了十来分,父母商量着让余秀华不要再继续读书了。
她不认命,一瘸一拐地跑到市里去找校长,最后学校没收任何费用,让余秀华去上学。
上高中后,随着学业的加重,身体负累带来的挫败感越来越强。
读到高二,她一把火把课本都烧掉,主动辍学了。
苦心孤诣的父母担心女儿后辈子没有依靠,给她在村里盘了一间小卖部,还给她找了一个大她十来岁的上门女婿尹世平。
那一年,余秀华才19岁,对于婚姻,她尚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
在这段婚姻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余秀华不仅感觉不到丈夫的爱意,也感受不到基本的尊重。
在尹世平的心里,是一直看不起余秀华的,嫌弃她长得不好,也不会干农活。
她跌倒在地的时候,他不仅不去扶,回到家后还会笑话她。
有一年,尹世平被拖欠工资,就拉着余秀华跟他一起去讨要。
他跟她说:“等那个老板的车开过来,你就过去拦。你是残疾人,他不敢撞你。”
余秀华问:“如果他真的开过来了呢?”
尹世平没吭声。
在这桩婚姻里,绝望和痛苦远远大于幸福,离婚的念头时不时地从心底冒出来,母亲却劝她:“你是残疾人,能有人肯娶你已经不错了。”

成名之后,余秀华第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离婚。
2015年12月,余秀华用写诗赚的稿费给了尹世平15万,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后,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终于结束了。
离婚那天,两人都很高兴。
尤其是余秀华,离婚后的那段时间,是她最开心的,长达二十年的不堪回首的囚徒生涯总算离她远去了。
在一档旅行综艺节目里,余秀华安慰因自驾游走红全国却一直无法顺利离婚的苏敏:
苏敏老师,没有离不了的婚。
就像我当时和前夫离婚那样,老子死了,都不跟他埋在一起。
是的,世界是自己的,终究与他人无关。
余秀华的心里始终有一团火,让她不甘于命运,进而尽情燃烧自己。
而我们大多数人心里的那团火,却早已熄灭在茫茫时光中。
太多太多的人,都是在为上一辈或者下一代活着,却独独丢失了自己。
长辈的一句“为你好”,自己内心即便有多少不甘,都会在这句话面前缴械投降。
卓别林曾在70岁生日时写下人生感悟: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
人的命都是自己活出来的,不断努力不断抗争,才能见到更广阔的天地。

在横店村人眼中,出名之前的余秀华无疑是个怪人。
她不像别的女人一样喜欢家长里短,整天只是捧着书,有时候还在埋首写着什么东西,对人还爱答不理的。
生活的转机往往蕴藏在念念不忘的坚持之中,且以一种意外的方式陡然降临。
有一天,村支书找她下棋,在她家看到了一个写满了诗歌的本子,于是鼓励她去投稿。
不久,余秀华的诗歌变成了铅字,出现在了当地报纸上。
彼时,互联网的兴盛更是给蛰伏在小乡村里的余秀华搭建了一个让世人认识她的平台。

2008年是余秀华的转运年,她开始在QQ上写诗,之后又在博客上发表诗歌,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有《诗刊》的编辑刘年。
那是一个寻常的中午,带着困意的刘年精神一振:
2014年,《诗刊》——这本“唯一的中央级诗歌刊物”一口气发表了她的九首诗。
2015年,学者沈睿写了一篇品评余秀华诗歌的文章,并为其贴上了“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的标签。
随后,这篇文章以《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为题在微信朋友圈里疯狂刷屏。
一夜之间,余秀华彻彻底底地火了,那一年,她38岁。
2014年12月,余秀华在母亲的陪同下,一路颠簸着去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朗诵了自己的诗歌。
回到老家后,余秀华写下北京之行的感受:
人生到此,仿佛所有的不幸,磨难都得到了回报了,我还是觉得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
刘年却觉得余秀华未来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觉得,她是大师级别的人物,是可以拿诺奖的。
余秀华的诗集以山呼海啸之势,被市场拥抱着。
2015年,《月光落在左手上》经四次加印后,销量突破10万大关,成为30年来销量最高的诗集。
到2024年的诗集《后山开花》为止,这十年时间,她的作品总销量已超过百万册。
出名后,余秀华的生活变得花团锦簇,她频频在各档综艺节目、谈话节目中露脸,人们喜欢她,讨论她,也谩骂她。
互联网上的流量始终是把双刃剑,纷至沓来的巨大流量背后,是对她无休止的攻击。
有人说她是“女流氓”,说她的诗是“荡妇体”,甚至攻击她“心理残疾,人格分裂”。
遭遇网暴,谁都无法平心静气,最开始,她也愤怒地回怼。
骂多了,她也释然了,且将键盘侠理解为一群读书太少的人吧。
余秀华被流量和声名裹挟着,一举一动都在大众的眼皮子底下,她越来越像个明星,而不是诗人。
伯乐刘年一直很关注余秀华:
她一直作为一个残疾人在农村生活,骨子里的自卑给她带来了对钱的渴望,底层生活带来了视野的局限,这都限制了她不敢往艺术的最高峰攀登,小富即安。……其实她的才华应该是一流的大师,她至今还在低估自己。
2017年,刘年借着酒劲,不客气地批评余秀华:
“你的作品一直没有我给你发的那一组好,你没有用心思在诗上。你的才华确实非常大,但是你没有用生命去写。”
刘年是在余秀华身上放了太多的期待,所以才会如此恨铁不成钢,其实,余秀华内心一直是清醒的。
只是,她就像小时候用爬的方式去上学一样,胼手胝足着,用残损的身体摸索着身下的土地,即便跌得头破血流,即便不小心爬入岔路分了心神,但她始终是向着前方那光明地方。
在《后山开花》的自序中,余秀华说:
我是如此幸运,能够找到最适合我的方式,用最忠诚的文字把自己平放在世界上,一切的苦厄都成了配菜。
终其一生,我们也要像余秀华那样,找到真正的自己。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一生,内心里的理想和现实一直在拉扯。
可是,我们就像是岁月的奴,匆匆跟在时光背后,束缚在由各种功名和人际关系编织的网内,忘记了当初的追求,也自满于手心里的所得。
原本,我们每个人都是小沟小溪,只有那些坚持着找到最适合且最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一生的人,才会最终把自己折腾成大江大河。

余秀华在诗中频频书写爱情,现实生活中,却几乎没有品尝过爱情的甘美滋味。
有缺陷的身体,是无法回避的原因。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真正爱情的人比比皆是,只是有人认命了,有人还在孜孜以求。
余秀华想要的,其实并不完全是爱情,是按照自己意愿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
她的诗歌中充溢着的爱情的躁动与呼唤,归根结底,是对存在、真理、死亡等形而上问题的本质追问。
凭什么身有残疾的人就不能追求高质量的感情生活?我偏不信!
2022年,余秀华恋爱了,男友杨某是一个90后养蜂人。
这一次恋爱,再次把她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杨某紧紧捏住余秀华的七寸,像蛇一样钻进她的生活,他为她整理衣裙,陪她出去旅行,用大捧玫瑰公开示爱,填补上她生命里欠缺的爱情。
在春天里,余秀华身着白色蕾丝裙在秋千上晃悠,杨某为她戴上漂亮的花环,一切都是如此的甜蜜快乐。
这份甜蜜快乐,却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轰然破碎了。

余秀华发微博说男友家暴,杨某则把直播间镜头对准蓬头垢面、情绪失控的余秀华。
这一场恋爱,以杨某交出漏洞百出的道歉信,和余秀华发出的律师函而匆匆收尾。
对于爱情,余秀华开始缄口不谈。她认为,“如果我们到了这个年纪,还关注这些,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不公平。”
这几年,她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遭遇了苦楚,经历了出丑,最后看开了。她选择突破自我,坦荡而舒展地尽情体验人生。
她尝试了拍内衣、化妆品广告,也参加时尚活动,也第一次尝试着用不灵活的手绘画。
如今,她站在了舞台上,跳一场属于自己的舞。

导演法鲁克,这位64岁的舞蹈制作人最初是被余秀华的诗歌深深打动,才决定找余秀华跳舞的。
法鲁克是巴基斯坦裔移民,小时候全家移民英国,那些遭受过的属于“边缘人”的歧视让他刻骨铭心。
而余秀华诗歌里的脆弱和挣扎,坚韧与倔强让他心有戚戚。
诗歌和舞蹈,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内核却可以是一致的。
一开始的训练自然是艰辛的,余秀华笨拙地转动着不灵活的躯体。她与它相处了四十余年,如今,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面对它,打开它,驾驭它。
练了几天之后,法鲁克是惊喜的,他从中看到了余秀华独特的领悟力和艺术天分。
这一年多的训练,余秀华是快乐的,对于自己的身体她有了更深的慈悲,“我领悟到我的肉体是我灵魂的选择后,我对它少了怨恨多了怜悯。”
关于最终的呈现效果,法鲁克则说,“这不是一部关于舞蹈的作品,而是一部关于生命的作品。”

他特地为余秀华设计了一段5分钟的独舞,她站在舞台中央,双手举过头顶,光影打下来,那一刻,摇摇晃晃的她振翅欲飞。
这一副残缺的身体曾经淌过悲伤海,她爱过,痛过,不甘过,最终舒展而释然。
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一场舞蹈,只不过有人沉重,有人轻盈。
到底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
是担心出丑所以一辈子谨小慎微,还是无所畏惧酣畅淋漓地去成全自个儿?
余秀华选择了去直面,去体验,去畅快地跳这场生命之舞。
有人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其实说到底人世间哪有什么输赢,人生不过是求仁得仁,尽量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活得舒服且坦荡,便是最大的圆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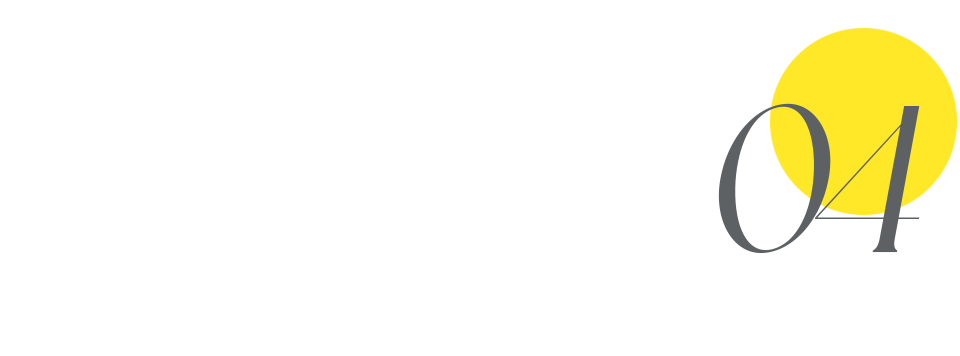
余秀华曾说:“我的天命,就是写文章、谈恋爱、好吃懒做。”
人活一世,很多时候,我们被世人的眼光、家人的期待和约定俗成的条条框框所囿,把真正的自我摁死在岁月里,最终长成了自己也曾讨厌的模样。
能为自己而活的人,实在太少太少。
每个人都会死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
正如作家贾平凹说的:
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
红尘纷纷扰扰,人群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
愿我们能如余秀华,为自己,痛痛快快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