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孔较瘦发布的
第166篇
文章
欢迎转发,欢迎留言交流
关注孔较瘦,非常有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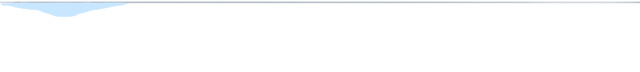
一
一直以来我的睡眠质量都不高,似乎每天都会做梦。昨天出差到温州,夜里又梦见了我的爷爷。
爷爷生前居住的那座院子,衰败的速度令我惊讶。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想起他活着时,与奶奶一起把那个农家小院,搭理地葱郁繁育的模样。
那些年,院子里除了行人的小路,剩下的地方全部栽满了瓜果梨桃、各式鲜花。他们的花期不同,瓜熟蒂落的时节也不相同,总之,鲜艳从初春一直延续到入冬。
小的时候,我听信了书上写的,说是用玻璃酒瓶装满泥土,然后再抓一群蚂蚁放在里面,他们就会在瓶子中安家落户。等时机成熟,就能隔着透明的玻璃瓶子,观察住在土里的蚂蚁家庭,记录他们的日常起居。
后来我发现这种点子压根不切实际。蚂蚁有自己的家,就算酒瓶里面的土壤上摆满了山珍海味,他们还是不会“乐不思蜀”。等他们吃满喝足以后,就会连咬带拖,把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根本不屑于在瓶子里落地生根。
记得那时候,我做过很多实验。除了想给蚂蚁重建家园,还把家里的铁皮暖瓶打碎,用哪个网状的金属壳,做成鸟笼子。我用这种“监狱”收留过麻雀、喜鹊、斑鸠、白头翁,甚至红嘴乌鸦。

老式暖瓶的网状金属壳可做成鸟笼
看到笼子中那些五官扭曲的小鸟,爷爷总是吸着旱烟,骂一句:兔崽子,你就不能消停会?
如今,三十岁的我再也没有曾经那般嬉戏的心境,也再不能听爷爷斥责的声音追着钻进耳朵。爷爷离开我,已经整整九年了。那座院子都像蒙上了一层再也无法抹除的灰尘,纵使日光璀璨,也显得荒芜冷寂,失了灵魂一般。
我的奶奶也搬离了那间老房子,任凭老屋自己经受风吹雨打。我回家后,总是会自己绕开人群,钻进屋子里转了一圈,陈设依然,只是少了曾经那呛人的烟味。
嗯,只是没了熟悉的味道。
二
家乡习俗,除了清明节,周年祭和农历十月初一都要上坟。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墓室前火光起,灰烬扬,姑姑们哭的不能自己,两个人伏在地上涕泪横流,嘴里喃喃自语,诉说着此生再不能与老人家聊聊天之类的话,听的人心酸。
旁边的亲戚看不下去,作势要拉他们起来。我拦了一下,说,让她们哭一哭吧,哭哭也好。
还剩半句话憋在嘴边没说:
“那毕竟是她们的爸爸呀。 ”
所以哭吧,做女儿的,何必掩饰对爸爸的思念呢。
家里的男丁却不哭,中国的男人都克制,话都在心里,不在泪里。
我记得爷爷头七那天,我写了《世界上最疼我的一个人去了》。之后,我开始期待每一场梦,期待能像传说中那般,在梦里再和爷爷见上一面。
神奇的是,我竟然真的做到了,我总能在梦里见到他。关于他的所有梦境都分外清晰:我背着行李走下乡村公交,他斜依在河边的青石桥上,笑呵呵地问我放几天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