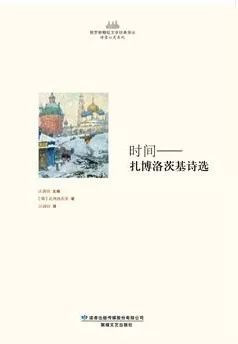
据说,有一次,曼德尔施塔姆在听过《秋天的标志》一诗的朗诵之后,欣喜地高呼:“又一个丘特切夫被发现了。”丘特切夫是继普希金之后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诗人,其富含哲理的抒情诗对“白银时代”诗人的创作,乃至对整个二十世纪俄罗斯哲理诗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曼德尔施塔姆的惊叹,无疑是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那种关注自然生态,并蕴含着深刻哲理思索的写作风格之褒赞。
这个新的“丘特切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扎博洛茨基一九〇三年五月七日出生在喀山附近一个名叫库克莫尔的小村庄。父亲是一位农艺师,笃信宗教,拥有不少藏书。按诗人的说法,他的立场“介于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母亲曾是乡村中学的老师,后因失声而放弃了这一职业。七岁时,扎博洛茨基创作了生平第一首诗,似乎自此便立下了献身于诗歌事业的志向。多年以后,扎博洛茨基回忆道,正是在父亲的书架旁,“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终生职业”,而他当时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重大事件的意义”。他曾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同时还修习医学,后转入彼得堡的赫尔岑师范学院语文系。一九二五年在该校毕业,进入儿童文学杂志《刺猬》和《黄雀》做编辑。同年,他认识了先锋派诗人哈尔姆斯和维杰恩斯基,二人为他的诗才所折服,与之保持了长期和坚固的友谊,并向他介绍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观念和创作精神。扎博洛茨基借此感染了时代的创新氛围,接触了马列维奇、塔特林和费诺若夫等艺术家关于“至上主义”、“结构主义”和“非客观主义”等新潮的艺术主张。马列维奇宣称:“模仿性的艺术必须被摧毁,就如同消灭帝国主义军队一样。”他希望打破理性的束缚,提倡“非逻辑主义”,以简约、纯朴的线条还原现实,摆脱物质性的桎梏,让精神重新归于无限。这些主张对扎博洛茨基成熟期的写作无疑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早期创作阶段,扎博洛茨基学习和模仿象征主义与未来主义的创作风格,关注城市和小市民问题,深受勃洛克、别雷、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等的影响,作品有很强的形式主义特征,尤其对赫列勃尼科夫的立体未来主义浸淫甚深。后来,他又对德国表现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受到这股思潮的启发,他的思想自由地穿梭于有机界和无机界,有时赋予无生命的东西以生命,有时又将人和动物写成无生命的物体,由此塑造了不少怪诞、夸张、古怪的抒情形象。
一九二七年,扎博洛茨基与哈尔姆斯、维杰恩斯基、弗拉基米洛夫、列文等人创建了一个名叫“奥拜利乌”的组织,它是“真实的艺术协会”的缩写。他们赋予“真实”或“现实”以特殊的意味,认为在尘世间要找到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们要努力寻找新的处世之道和靠近事物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具有通往彼岸世界之可能的新艺术和新诗歌。他们在宣言中声称:“我们,奥拜利乌分子——是自己的艺术的忠实工人。我们是持有新世界观和新艺术的诗人。我们不仅是诗歌语言的创建者,而且还是对生活及其细节的新感受的缔造者。我们的创作的意愿是包罗万象的:它席卷艺术的所有形式,掘进生活,从各个方面来包裹生活。”在实践中,奥拜利乌分子倡导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纯真的幼稚来克服成熟的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未来主义玄妙诗歌的理念。他们刻意追求某种怪诞、大胆的风格,进行词与韵律的探索性实验,这在那个正由“艺术对话”逐渐演变成“政治独白”的时代颇为引人注目。
奥拜利乌的成员发现,生活的现实本身不是一种逻辑的关系,它充满了荒诞与偶然,因此,艺术和诗歌也不需要逻辑化的表达。在他们看来,“艺术有自己的逻辑,它不破坏现象,而是帮助人们理解它,扩大现象、言词和事实的意义”。他们对人性的复杂有着深刻的体会,为此他们在创作中致力于描述与刻画暴力、荒诞、反讽、黑色幽默,制造语言的狂欢,在作品中漾入了较多的黑色元素,从而显示了某种后来为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美学解构的可能,扎博洛茨基的《变形》一诗便泄露了这样的信息:
万物变幻莫测!从前的一只鸟
如今躺着,成为书写过的一张纸。
我往昔的思想是一朵普通的小花,
叙事诗蠕动,像缓步的老牛;
我过去的一切,或许,
会再度生长,植物世界日益繁茂。
需要指出的是,奥拜利乌的成员只是希望建立一个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空间,并不是要借此确立某种共同的艺术风格以形成所谓的文学流派,因为,“文学流派——这是某种类似寺庙的东西,僧侣们在其中戴着同一个面具。我们的协会是自由和自愿的,它联合的是大师,而不是大师的助手——是艺术家,而不是艺匠。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每个人都懂得他是依靠着什么才与其他人发生联系”。当然,这种文艺观和实践对文学史家平庸的归纳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却为艺术的丰富展示了无限的前景。事实上,扎博洛茨基不久便脱离了该组织,但协会的一些原则和写作策略仍然在诗人的创作中得到了贯彻。他意欲打破传统意义上对诗的认识,让诗变得“几乎不像是诗”,在暴力地摧毁某些优雅的游戏规则之后,重建诗的活力空间。在他看来,诗与绘画、建筑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的表征,却与散文毫无共同之处。因此,扎博洛茨基注重在创作中灌注色彩美与立体感,在雕塑般的语言中捕捉时间神秘的呼吸。
扎博洛茨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而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什么安宁。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肯定负有某种使命,而不是徒然走上这么一遭。这种“不安宁”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尤其显著,这就提醒诗人首先要成为“一个观察者”,因为,“观察是观察者与他周围的世界的某种积极的交往,而且对任何现象都要提出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这种观察落实到创作中,就是对词与形象的重视。
在《思想-形象-音乐》这篇文章中,扎博洛茨基写道:“为了让思想赢得胜利,他(诗人)应该用形象将它体现出来;为了让语言工作起来,他就需要汲取它的整个音乐能量。思想-形象-音乐——这是诗人追求的最理想的三合一状态。”由此理念出发,扎博洛茨基开始了对日常世界之秘奥的探寻,在细节中展开关于人、自然和宇宙的思考,立意用“世界自身的眼光来看世界”,尝试着借助动物、植物的视角来扩大人心的域界。对自然的倾心使得扎博洛茨基对艺术持有异样的看法:“艺术像一座修道院,人们在里面抽象地相爱……艺术不是生活。它是一个特别的世界。”在《艺术》一诗中,他宣称:“词飞进了世界,就成为客体。”为此,诗人看重智慧和安静的力量:
“诗歌的脸应该是安静的,聪明的读者在安静的表象下可以出色地看到智性与心所有的游戏。”
遵循这样的原则,他努力在诗中寻找生活之问题的答案,捕捉时间充满生机的呼吸。
扎博洛茨基的第一本诗集《专栏》出版于一九二九年。这本书引起的反响很大,“拉普”批评家给予了苛刻、严厉的批判,诗歌行家们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它较多地体现了扎博洛茨基诗歌的一些艺术特征:反讽、怪诞、戏仿、奇特的隐喻。随后,扎博洛茨基创作了三部长诗:《农业的庆典》《疯狼》和《树》。《农业的庆典》于一九三三年在《星》杂志上发表后,被批评界指责为具有对当时的集体农庄进行诋毁的倾向,导致了该期杂志停印,主编吉洪诺夫作检查,另一个后果便是诗人已经付印的一部诗集《诗歌一九二六——一九三二》被销毁。后两部长诗在诗人生前一直未曾公开发表。《星》《文学批评家》《真理报》《红色处女地》等报纸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扎博洛茨基掀起了新一轮“政治性”的批判。这种观点直到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苏联文学史》中还留有余迹。
一九三七年,扎博洛茨基又出版了一本诗集《第二本书》。同时他开始了用现代俄语翻译和改写《伊戈尔远征记》的工作。但这项工作意外地中断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扎博洛茨基突然被捕,罪名是从事“反苏维埃的宣传活动”。经过一部分知识界人士的营救和申诉,最后未经公开审理便被判决五年监禁,被流放到远东的劳改营服苦役。获释后,他继续在西伯利亚和卡拉干达地区修筑公路。但即便是这段时期里,诗人也没有丧失对美好人性的信任。《这发生在很久以前》一诗记叙的便是一名普通的农妇在自己面临亲人丧失的悲痛之时,仍然向饥饿中的抒情主人公赠予土豆和鸡蛋的故事。许多年后,这个场景仍然让诗人刻骨铭心:
一个头发灰白的农妇,
就像年迈、仁慈的母亲,
拥抱了他……
在书房,他扔下笔,
独自一人徘徊,
尝试用自己的心
去领会只有老人与孩子
才能领会的一切。
扎博洛茨基的记述令人想起《圣经》中关于寡妇的捐赠的事迹。在《圣经》路加福音里有这样一段经文:“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种赠予所包含的善心远远超过亿万富翁们所创办的慈善机构,诸如医院、学校,等等。
一九四四年,扎博洛茨基获释,但他仍然没有选择工作和自由居住地的权利。直到一九四六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获准回到首都,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在作家伊利耶科夫的别墅里,借住了两年。从劳改营回来以后,扎博洛茨基把妻子小心保存的那些早期诗歌的手稿付诸一炬。因在原创性写作方面受挫,诗人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诗歌与外国诗歌的翻译工作。此外,由他译写的现代俄语版本《伊戈尔远征记》获得了专家与读者的一致好评,被誉为“诗的功勋”。一九五七年,因翻译格鲁吉亚诗歌获得“劳动红旗勋章”,这个勋章对改善他的处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以前的劳改营生活极大地损害了扎博洛茨基的健康,或许是感觉到生命已不长久,扎博洛茨基销毁了自己的许多戏谑性诗作和一些长诗的片段。一九五八年秋天,诗人因心肌梗死离开了人世,被埋葬在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
在俄罗斯文学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识:以劳改营生活为标志,扎博洛茨基的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作两个阶段。不过,在这个共识下,对这两部分创作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一部分批评家的看法是,他后期的作品“终止”了“迷茫的青春期”,是向经典作家的传统的回归;另一部分批评家则更倾向于认为,它们不是对早期作品的“否定”,而是对以前的“可能性”的发展,是对青年时代绽露但尚未完成的追求的延续。布罗茨基所持的便是后一种观点,他觉得晚期的诗人远比早期出色。
关于理智的悲剧的思考一直折磨着诗人的神经,他甚至为词在流传过程中那种激情的丧失感到痛苦。在最后的岁月里,诗人依然相信,美和创造的基础都是情感,而不是理智。这不由得让人回想起马列维奇对“至上主义”的解释:“所谓至上主义,就是在绘画中的纯粹感情,或感觉至高无上的意思。”纯粹如“白色之上的白色”,这位先锋派画家的追求与诗人的理想大致吻合。扎博洛茨基晚期的作品大多显示出一种“豪华脱尽”的气象,从揭露人的委琐转向对崇高人性的挖掘,由早年辛辣的讽刺转为温情的叙述,只是它们比以前更音乐化、更富于激情,显现出某种新古典主义的风格,表露了向普希金、巴拉丁斯基、丘特切夫的传统回归的趋势。
在一篇文章中,扎博洛茨基曾经谈论道:“许多人的脸,其中每一张脸都是内心生活的活镜子,是各种隐秘的心灵的精巧乐器,有什么能比经常与他们打交道,观察他们并与他们友好相处更有吸引力呢?”因此,他如是吟唱“人脸的美”:
有一些脸就像豪华的大门,
门内仿佛到处是伟大蕴藏于渺小。
有一些脸——就像破旧的小屋,
屋里有肝脏在烘烤,皱胃在浸泡。
另外有一些冰凉、死寂的脸
被栅栏遮挡,仿佛是监狱。
还有一些脸——就像塔楼,很久
已无人居住,也无人张望窗外。
……
有一些脸——就像欢快的歌曲。
这些闪耀如阳光的旋律
编配成一支巍峨天空的颂歌。
在这首诗中,人的脸仿佛已成了“心灵之窗”,精神的入口。透过它们,诗人看到了世界的缩影,伟大与奇妙的风景,乃至“春天的叹息”。
在扎博洛茨基的心目中,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印证的关系,自然是思想为灵魂而存在的世界,人是自然在时空中的精神存在。两者并不对称,却相互缠结、转化,甚至侵蚀,有时还会发生悲剧性的冲突。在诗人最后一年创作的《夕阳下》中,他如是宣称:
每个人都拥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创造了我们的世界,
另一个是亘古以来
我们竭尽全力所创造的世界。
对于扎博洛茨基所创造的世界,著名的文学史专家马克·斯洛宁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一九一七—九七七)》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这种情况在他死后名誉得到恢复的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当他的作品终于能和俄国广大读者见面时就十分清楚了。”而今,时间已雄辩地证明了斯洛宁的这个判断。关于扎博洛茨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布罗茨基在与著名的文化史专家、传记作家沃尔科夫的一次谈话中曾不无遗憾地指出,他“是一位评价不足的人物,这是一位天才的诗人”,肯定他的写作拥有的是“丢勒的技巧”。丢勒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画家,他相信,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但知识可以使人变得高贵。他的肖像画细腻、逼真,明暗对比匀称,具有木刻版画般的力度。布罗茨基在此强调的就是扎博洛茨基创作个性中那些与丢勒相近的人文体现和犀利的凿刻时光之能力。
原载于《世界文学》
2014
年第3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公众号责编:文娟)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2017
年《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
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
:
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
010-59366555
征订邮箱
: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