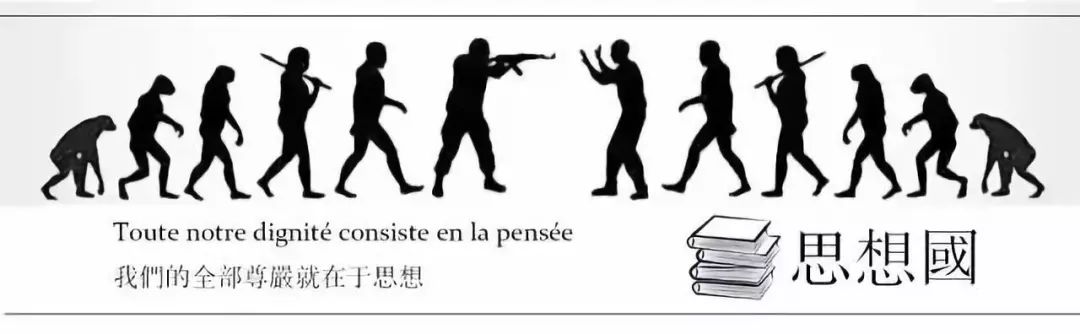

点击进入
《寒山》(《我是一个连环杀手》)——熊培云首部诗歌电影短片观赏
上楼,下楼,离开落满灰尘的办公室。回到车里,准备写点什么。很快暮色降临,只好移步到附近一个老旧的小咖啡馆。将《如歌的行板》塞进耳朵,让自己和世界同时安静下来。
前些天,有朋友在思想国留言
《如歌的行板》过于
悲伤,我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啊,这些年来,我甚至从这首曲子里慢慢听到了甜蜜。
在英国生活的那一年,日夜同行的两首曲子,一是《如歌的行板》,二是徐嘉良的《殇》。
那些连绵不绝的哀愁,像连绵不绝的雨水,将我和喧嚣浮躁的世界隔离开来。没有深究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雨水,也许它和哀伤有着相似的隔离之用。通过这种隔离,我会忘却窗外的世事纷纭,取而代之的是看见内心的车水马龙。
而就在刚才回到车里的时候,收到新近添加的一位永修老乡的长信。这是一位漂泊在京的诗人,我们不曾谋面。据说在看了我前几天发布的短片后,有些不安,为此劝慰我“您是精英之一,我感觉您很不开心一样。不开心的事,本是自己的事……您是有身份的人,千万不要忘记父母培育您的艰辛。也正因此,我甚至为您担心”。
来信言辞恳切,最后没忘嘱咐,“您是永修才子,不可情绪低落,要斗志昂扬啊,那个连环杀手应该从内心驱逐,换个园丁和花匠,这是我想了很久的心里话。”
首先说,这位仁兄的来信难免让我心生感激之情。素昧平生,只是凭着一点乡谊和对诗歌的热爱,不辞辛苦致信问候,这些都是人性中可贵的良善。
与此同时,我也在想,痛苦对于我或者每个人的一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曾经说过,若有药片或针剂让我身心不受损害,同时又能免去三餐之累,我宁愿一试。而如果有人说他有一个药片,只需吞服三二就会变得永远快乐,我一定是会逃之夭夭的。就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所揭示的,相较于无尽的快乐,痛苦甚至是一种权利。没有痛苦的权利,人也就被剥夺了爱的权利。
同样是在影片《头脑特工队》里,人的正负面情绪本质上说可以互相救济,而不完全是简单抵销。更别说,
对痛苦的感知,包括由此生发的沮丧、惆怅、悲伤甚至愤怒,也是完整的人的一部分。
有些痛苦会令人上瘾。这并不表示我在此主张必须迷恋痛苦,而是相信人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痛苦注定会若隐若现伴随我们的一生。这是人类永恒的不可能删除的境遇。如上面这位仁兄所言,倘若我算得上所谓的思想精英,不是成为思想精英带来了我的不快乐,而是我的不快乐让我成为思想精英。
这些年,许多人都在谈论正能量。不想简单断定它是一种庸俗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正能量里面所包含了一种快乐的能力,也是人类之所需),但我宁愿相信,于我人生更有价值者,是痛苦的能力。而我等今日之中国人,能从先贤苏东坡那里得到的慰藉,又几曾是他人生的快乐无边。东坡先生一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甚至让我觉得自己的孤独有了依靠。
正能量与负能量,都是人间的食粮。重要的是你如何面对它们,或者说以怎样的方式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