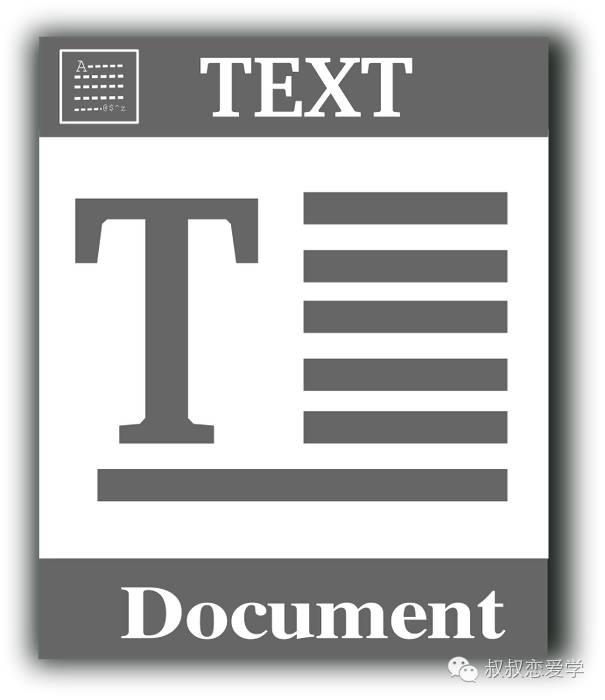【作者简介】
贺欣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现任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曾在纽约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近年来,贺欣教授在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aw & Society Review, China Quarterly, China Journal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其专著Embedded Courts: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 with Kwai Ng于201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律与社会、实证法学、比较法、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中国司法改革与中国家事法)。
吃(混)学术饭的,没有人不知道“Publish or Perish”。
直译是不发表,就死亡。
李连江教授译作“不发表,就出局”,强调发表在学术界谋生存的重要性。
我斗胆作个新译:
不发表,等于零
。
这是因为,至少从对社会有所贡献的角度上看,研究需要全部完成才算数。
发表了,才是100%。
否则,就算工作做了99.99%,最后没有发表,也还是零。
不发表和发表,是0和1的差别。
一壶水烧到60、80、90度,不管花了多少燃料,还是反复烧了多少次,没有烧开,就不是开水。
▲ 李连江著:《不发表 就出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问题在于,如何把已经做了30%、50%、70%、乃至90%的研究发表,或者说在更重要、更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
博士生们也许对这一点理解不深。
读博士,能否毕业不是看发表,而是看论文能否达标。
这容易造成一个错觉,就是论文写完就行了,不一定需要发表。
论文写完,作者自己当然有收获。
但学界是以学术成果来评价的。
就算研究做得再好,最终没有发表,也等于零。
国内很多大学为了增加研究成果,要求博士生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刊物发表多少篇才能毕业,后果是拔苗助长,甚至是杀鸡取卵,因为很多研究如果多一些时间去准备,就会将研究的最佳潜力发挥出来。
逼着学生赶在毕业之前发表,不知扼杀了多少好苖子。
至少在我求学和任教的大学,都没有这个要求。
这个议题曾在大学研究委员会讨论过,遭到一致否决。
不要求发表并不等于发表不重要,而是允许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孵化最佳的成果。
闲话少提,言归正传。
如果开始做研究不难(也有人觉得开始动笔是最难的,这个下次再谈),那么真正困难的不是开始,而是完成。
这时候就不能不提到英文学术期刊(除了美国的法律评论)通行的专家评审制(具体见拙文《“专家评审制”应当实行》,《中外法学》2004年第5期。
)。
稿件到达入门的水平,编辑一般会发给专家去审,要求专家建设性地批评。
只要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回来的报告,不管基调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有一堆修改意见。
除了个别例外,基本上没听说过好的期刊不要求实质修改就直接接收的。
众所周知,期刊往上走一级,难度呈几何级数上升。
这其实是一个充满挑战、近乎自虐的过程。
▲ 贺欣:《专家评审制应当实行》,《中外法学》2004年第5期。
每一次收到修改意见,都是忐忑的一刻,因为这时候才是炼狱。
在我所处的不温不火的学术环境下,请人给初稿提意见,不管是同事、老师、亲友、学生,除了少数“诤友”,通常都是隔靴搔痒:
有的不在其领域,有的缺乏洞察力,有的不愿下功夫,有的顾及面子,总体效果索然。
而在这些好的期刊的审查报告中,由于评论人不知道作者的身份,至少可以假装不知道,在匿名机制的保护下,可以真实同时也刻薄到极致。
由于期刊随时准备发表这些文章,直接影响其声誉,所以绝大多数评论十分认真,有的极具创见,更有的让人拍案叫绝:
人家怎么看得这么清楚?
!
但我想强调的是,许多报告让人“不忍卒读”。
我习惯把所有的评审报告都留下,偶尔回头翻翻这些报告,提醒自己:
行内高手们都在看着呢!
最容易受批评的,当然是研究方法和数据材料。
在我学术生涯的早期,有一个评审人说:
“作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悲摧的(pathetic)是提交出这样零星而没有多少原创性的材料。
”我有一篇稿件名为《运转不良(dysfunctional)的法院》,评论人挖苦说:
“文章在选题和收集材料方面的努力是可嘉的,但文章的组织和结构像它的标题一样‘运转不良’。
”当然,文稿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为攻击的对象。
大约十年前,一位评审人质疑我稿件的研究目的:
“这篇文章试图完成三个任务,它最成功地完成了第三个。
虽然这三个任务都是有价值的,但在这篇文章中,它们各自的目的相互交叉,使得分析变成一团浑水,松松垮垮,毫无紧凑、清晰之感。
作者还对……做了猜测,我想这是其第四个暗含的假设。
一言以蔽之,这篇文章里面有太多的假设,而没有进行有效的检验和解读,使得读者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关于文献,另一个评审人写道:
“本文的文献述评是如此肤浅,好像是描绘了一幅卡通”。
关于理论对话,一位评论人说:
“本文的理论架构很有问题,设定了一个假的研究问题去理解所谓的‘意外发现’。
它无法帮助理解中国的制度如何运转。
与美国的比较也是成问题的,有太多的干扰因素存在”。
关于数据,又一个说:
“这篇文章我读了两遍,但还是没读懂统计数据如何与假设有关。
很多论证是证伪假设的,也说服了我,但与提供的数据无关”。
做研究写文章不容易。
“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面对“可悲”“一团浑水”“松松垮垮”“猜测”“卡通”“假问题”等评价,第一反应通常是反感。
他们怎么这样对待我?
好的地方装着看不见?
心里满是委屈。
但这个过程,没有上诉,没有辩论,没有法律人爱提的正当程序,作者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
一位好心的编辑在转发这样的文字时,怕我吃不消,还专门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说这是学术界的常态。
在学术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有的刊物两三轮的邀请修改是家常便饭。
有的刊物在邀请修改的信中写明,这个邀请决定并不保证下一轮的修改稿就能发表,是否再提交作者自己看着办。
有的修改得不行的稿件,主编连外审都不送,直接枪毙。
面对这样的评论,有多少人放弃?
有多少人转投?
不同的刊物自然不同。
曾经负责过一个期刊,让我知道原来在那样一个小刊物,也有超过一半的投稿人即使拿到邀请修改,也再没有下文。
甚至一位建树斐然的同事说,“我根本不敢去投顶级期刊,因为可以想像得到,评审人会怎样挖苦我。
” 研究刚做完,大家都是信心满满,期待着上顶级期刊,一夜成名。
殊不知,投完第一稿,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
投稿时信心满满,评审报告回来时垂头丧气。
一旦进入恶性循环,几个回合下来,对自信心的打击可想而知。
那就不仅是不发表、等于零,而真的就是不发表、就完蛋了。
正如读博士时最可怕情形:
一个题目刚做了一段时间,又转向另一个题目,几次下来,一晃几年过去,博士就该肄业。
很多人即使跨入学界,也拿不下天牛(tenure)或评不上副高,或者幸运地拿下,但之后一蹶不振,或者知难而退,事实上退出学术圈,成为高校头疼的冗员(deadwood)。
因此,如何针对这些修改意见,拿出实质上更好的修改版,是关键中的关键。
我的经验是,在读这些评论前,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个世界没有跨不过去的坎,时间终将改变一切。
读完之后,把它放下。
两、三个星期后拿出来再读,这时它的杀伤力已经降低,或者说我的免疫力有所提升。
又再给自己一段时间消化,慢慢地就可以开始冷静地分析,评审人说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有偏见的,哪些是可改的,哪些是不可改的,哪些是必须扔掉的,哪些是需要新加的。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改下去。
我坚信文章是改出来的;
我同时坚信,改文章比写文章容易。
与其去写新的文章,不如先把旧文章改出来。
在新项目和半成品之间,我总是把半成品放在优先的位置。
谁能够保证新项目就不会碰到钉子?
只要努力,总有改的办法。
而且我不是完美主义者,只要改到能够发表就行。
如果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那就是“一不怕写,二不怕改”。
据说学界有一类人,聪明绝顶,也不是不努力,只是办公桌下面压着二十几篇半成品。
如果开始撰写文章时比的是创造力,那么改文章时需要的不是任性,而是韧性。
▲ 论文作者与审稿人交流的邮件截图。图/曹建军科学网博客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让我感到委屈的评论,变成良师善意的提醒。
材料悲摧的评论让我意识到,只是去做田野并不够,还要看找到什么材料和如何使用材料。
看到一篇文章有四个任务的评论,我后面写的文章永远只有一个任务。
意识到我的文献叙述只是“肤浅”后,我每次下笔都会努力把要做的研究与文献中的空隙联系起来。
面对材料与论证脱节的评论,我意识到不仅要做好进攻,还要注意防守。
对于那些花时间认真读我的稿件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同行,我心怀感激。
“自虐”成为在学术界成长的最好方式。
今天早上收到邮件,编辑说我的一篇文章马上排期出版。
我一脸惘然,没有半点欣喜。
这篇文章从收集数据开始,已经八年,研究助理已经从清纯学生成为副教授,当年接受访谈的人早已不知身在何处。
期间被两个刊物拒稿,合作者几乎弃船,在这个刊物也经历了两次邀请修改,一次有条件接受,中间还因为主编的误解要撤稿。
在完全接受之后,排期也等了快一年。
从0变成1,怎一个难字了得?
有诗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