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朗读小哥哥的全文音频
BGM:音乐治疗 - Floating in the City&Dance of Gossamer
作者 | Lauren Marks
翻译 | Panny
审校 | 酷炫脑主创 & 小草
朗读 | Yikes
美工 | 豆浆
编辑 | Tinda
经历过这场大病,我可能跟五年前、或者十五年前的我不一样了。甚至在 50 秒内,我都可能变成另一个人。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脑损伤患者身上。其实每个正常人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我对苏格兰医院的记忆中,天空始终是蓝色的,尽管我知道我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
夏天快过去了,像往常一样,这个时节的爱丁堡经常遭受不可预测的风暴。但是,在我躺在床上的那两个星期里,我不记得曾下过一场雨。由于服用吗啡,我总感觉自己被笼罩在迷雾中,只零星的记得一些片段:
我记得从病房的窗户外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我记得发烧时出了很多汗,母亲用粗糙的手指轻轻地擦拭我脸上的汗水,我还记得父亲的眼泪。
所有的这些记忆都使我感到困惑。但是这一次,我的记忆不再混乱,变得更加清晰了。我回忆起了那片宁静。
《云之彼端 约定的地方》
01. 我的故事
这不是我以前所知道的宁静。这是一股平静的水流,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空虚。
我所看到的、触摸到的、听到的每一件事都有一种奇妙的秩序感。我像是个废物一样,什么都没有想。 我非常专注于此时此刻,对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打算都提不起兴趣。
我感觉自己身处的环境是一个相互连接着的整体,它就好像是一个正在呼吸的庞大的生物体。我像是它身上一个细胞,与周围的细胞紧密地连接着。 想要体验到这种宁静,自己本身就需要成为宁静的一部分。
但是,我周围的人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宁静。我还记得我当时在爱丁堡的一家酒吧里唱卡拉 OK ,我突然昏倒了,接着被抬上救护车,我的朋友给我当时在美国的父母打了通电话。
那时是爱丁堡的半夜,洛杉矶的傍晚。然而大家都没有过分担心我的情况,因为看起来我只不过是由于摔倒出现了一点脑震荡的症状。可是,在我住院两小时后,一切都改变了— 当时我的脑部 CT 扫描结果显示,我的脑动脉瘤破裂,正在大出血。一位神经放射科医生联系上我的父母,并告知他们我可能有生命危险。动脉瘤破裂后人的死亡率很高,甚至在治疗后,也只有略多于一半的人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存活下来。
每一秒都很关键,医生立即为紧急手术做准备。 我的父母被吓坏了,他们想即刻出发去爱丁堡见我,却被困在了加利福尼亚。他们的护照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可银行当时已经关门了。为了早点拿到护照,他们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敲银行的窗户,说服他们早点开门。当天早晨,我的父母就登上去爱丁堡的飞机,我的兄弟和祖母则留在家里。
当时,我的手术正在进行中,而且很顺利。他们到达爱丁堡时,手术已经结束了。 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们聚在一起,为我在手术中幸存下来而感到宽慰,但是都十分紧张,因为那时的我仍然未脱离生命危险。
手术后,我的脑组织肿胀得厉害。在镇定剂的作用下,我沉睡了好几天,才完全醒过来。但是当我的意识变得更加清醒的时候,我发现沉睡时所经历的宁静十分有趣,比我眼睁睁地躺在病床上有趣得多。
《洛丽塔》
我唤醒了一个新世界,安静而充满好奇。
当我从重症病房转移到康复病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到康复病房需要乘坐电梯,电梯里有一面镜子。虽然我脸上没有绷带,神志也十分清醒,可是我却认不出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感到烦心,因为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唯一改变的事情,周围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变了。
我发现我很难辨别出哪里是墙,哪里是窗户。
就连“他”和“她”、“我”和“它”之间的区别也变得难以区分。我知道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像自己了,反而更像是与周围的事物融为一体。
我的病床靠近一个朝西的窗户,病房里还有三个女人。她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说着方言。我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但我很少参加她们的谈话。 我只是喜欢听到她们说话的声音,那声音就好像是脚步声一样,啪嗒啪嗒地响。
那时的我对自己脑损伤的病情一无所知。我没有感到一丝疼痛,所以我对自己的病情没有过多的担忧。我甚至不曾认真思考过自己为什么会在医院里,或者自己到底生了什么病。
我的思绪反而是被一种全新的感知占据着,我开始关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穿好衣服,我惊讶地发现布料与皮肤之间的空隙大了许多;刷牙时,牙刷毛的坚硬、牙龈像海绵一样的触感,都令我着迷。
我总是花很长的时间注视着窗外的景色,那是一片灰色的、毫无纹理的屋顶。医院的院子里还有一棵树。我从病房的窗户只能看到树的顶端,但我很喜欢观察那些针叶和树枝。每当清风拂过,它们的形状都会微微改变。
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打扰过我。但是,在一个无休止的白日梦中,我记起了那一刻,那种痛苦似乎是真实的。 或许,至少我那时确实失去了一样东西。
那一定是正午时分,因为阳光直射在我的身上,一缕阳光照在我左边的白色床头柜上。我的父母在柜子里塞满了我的衣服,护士们在一旁为我补充饮用水和其他物品。我还注意到床头柜上有一堆杂志和一本书。 我不确定它们放在那里多久了,很有可能在我住院之前就放在那里了。
02. 失语症
不过它们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杂志的封面很有光泽感。我翻开杂志,书页里充满了明星走红毯的照片,还穿插着化妆技巧的插图。我不敢在任何一页停留过久,那丰富的色彩、繁杂的内容,像是在向我大喊大叫。我合上了那本杂志,顿时感到一种解脱。
我转而拿起柜子上的那本书。那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我可能在很多年前读过。我翻开第一章,习惯性的翻阅了几页。但在翻到第三页时,我停了下来。我又回到第一页,以更慢的速度阅读起来。

Agatha Christie 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等 | Google
我的眼睛有些不适应过于明亮的阳光,但我仍然坚持着读着这本书。可是我却发现我读不懂那些语句了。那一个个单词,在我脑中,只是一块块形状各异的黑色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那时有些阅读障碍的我,怎么能这么肯定那是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我手里拿着这本既熟悉又陌生的书,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失语症的痛苦。
我清楚语言的力量,它足以影响人们事业的成败。在我的生命中,文字和语言是少有的给我带来快乐和动力的事物。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我,我阅读文字的能力可能会被剥夺,那对我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就算是暂时性的失去这项能力,也是件十分残酷的事情。可是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反应却是出人意料的温和。
毫无疑问,承认失败令我感到不快,但我有没有因此感到痛苦或者焦虑呢?不,我的感受并没有那么强烈。我隐约地感到有些失望,这一想法只是倏地掠过我的心头……我想,既然已经失去了阅读文字的能力,它无法再对我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了,我不应该再想象有阅读相伴的日子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失去了如此重要的东西,反应居然可以如此淡然,真是令人感到震惊。那时的我,在宁静而舒适的生活中,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悄悄地改变。
过了几个星期,我才发现我有些迷失了自我,需要付出很多才能追回那些消失的自我。那种不快感在我读书的时候尤为强烈。然而,我一合上那本书,那种不快感就消失了。放下书,我将注意力转移到窗外,望着那片蓝天。
术后的我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几天后,我见到了神经科的主治医生,鲁斯坦姆·萨尔曼(Rustam al-Shahi Salman)博士。他耐心地向我的父母解释着我的病情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也许是我的父母第一次从医生口中得知我得的病叫“失语症”。医生解释得很详细,比我说的明白得多。他的身材苗条,说话温柔而体贴。在我看来,他的举止同我身处的宁静的世界是十分相称的。
医生说失语症通常不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而且大多数失语症患者的智力也不会减退,但是不同患者的临床表现会有很大差别。失语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接受性失语症和表达性失语症。
接受性失语症,又称为维尔尼克失语症;这类患者对语言理解存在障碍,虽然口语流利,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却令人难以理解,而且患者也不能理解别人说的话。与之相对的则是表达性失语症,也称为“布洛卡失语症”,其特征在于部分或者全部语言功能的丧失。患者说话时语言不流利,且词汇贫乏。
萨尔曼医生认为我表达性失语症的症状更为显著。但是我在发病的初期,也出现过语言表达混乱,所答非所问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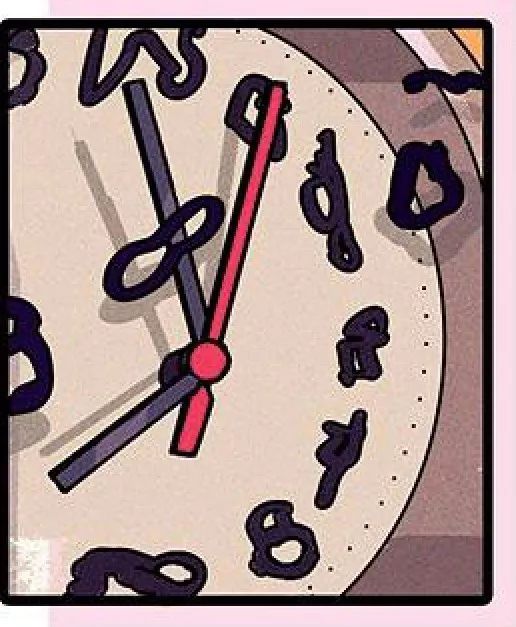
Jackie Ferrentino
03. 治疗过程
为了治疗我的失语症,萨尔曼医生为我指派了一名语言治疗师,安妮·罗(Anne Rowe)。她的年纪与我母亲相仿,留着一头褪了色的红色齐耳卷发。我曾经一度认为,她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给我成堆的训练表。
我还记得她给我的第一份训练表,那是一组人脸照片。安妮要求我找出照片中的一个秃头的男人,并描述我当下的感受。“我觉得不错”,我记得常常这么回答她。但是,安妮却坚持要我说出一个更有深度的答案。她常常问我:“你为什么不能指出来那张你让感觉不错的照片呢?”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图像训练法的重要性,它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训练,因为大多数时候安妮都无法理解我对她的问题的回答。我同时患有表达性和接受性的失语症,这不仅导致我的语言表达不清楚,而且我还不知道自己出现了语言表达障碍。我的父母后来告诉我,在我接受语言治疗的前两周,我只能说 40 到 50 个单词。
我从安妮的治疗记录中得知,一开始,我对单词的发声都感到十分吃力。她在训练记录中写道:“劳伦偶尔能够顺畅地使用短语,但在寻找合适词语和控制嘴部肌肉运动这两个方面有明显的困难。”我很难做出正确的嘴形来发出我想要的声音,这是语言失用症的表现,是常见的失语症的并发症。
其实我所接受的语言训练,与孩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十分类似,为了纠正孩子的发音,父母会一遍又一遍地让孩子练习发声。这与安妮的训练目标不尽相同。她总是一边手指着一张嘴巴的图片,一边说:“舌尖在这里。”然后在自己的脸上比划着说道:“T, T, T, Teh,发这个音要用到舌尖。Th, Th, Th 是 Thuh,舌尖要轻触齿背。”
当安妮让我进行这些发音练习时,我并没有感到困扰。事实上,我从前上过戏剧学校,这些训练很像表演前例行的发声热身。在戏剧课上,让一个演员反复演示p音和b音之间的区别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因此,当安妮要求我做发声练习时,我以为我在这方面很出色。直到后来,我从安妮的反馈中隐约地感到我的发音有些问题。她会说,“这个发音很好”。可有时她会说:“这个发音并不完全准确,再试一次。”
不知从哪天起,我发现安妮总是频繁地说“这个发音并不完全准确,再试一次。”有时,安妮说“再试一次“的次数太多了,她会让我先缓一缓,进行下一项语言训练项目。我知道安妮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的发声训练出了点问题。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过作为天生的乐天派,我相信自己能通过努力解决掉这个问题。

《House of Sand and Fog》
术后一周时,安妮让我做了西部失语症测试(Western Aphasia Battery test, WAB)。在我后来翻看自己的试卷时,我发现安妮在试卷上做了一段标注。在阅读部分下方,她写道:“劳伦非常清楚自己无法完成这项测试。她感到非常痛苦和焦虑,因此测试被中止了。”
其实我对这件事情一点记忆也没有。不过我猜,我当时的情绪反应肯定是肤浅而又短暂的。虽然我相信安妮的报告,但我不认为那时的我有完整的自我认知。我可能压根就没有意识到我在参加一项测试。更不要说考虑这项测试会对我未来的治疗造成什么影响。当时的我对过去和未来一点也不关心。
可是现在的我,逐渐恢复了自我意识,我不想让自己失望。这成了我烦恼的根源。不过幸运的是,那些烦恼总是很快就消失了,好像从来就不曾出现过一样。
我在口语理解方面出现的问题,还间接地反应在了书面文字上。在语言训练中,我发现我并没有完全忘记字母,但我忘记了字母的顺序。假如每次只看一个单词,我仍然可以在大段文字中认出那个单词。
在安妮的悉心指导下,我可以慢慢地念出这些单词。安妮在语言训练记录中曾写道:“劳伦在朗读时经常出现错误,尤其是那些发音不规则的单词。可是问题在于,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读音是错误的。”
虽然我没有完全丧失阅读的能力,但我每次只能将注意力聚焦在一个单词上。当我好不容易读出这个词,继续去读下一个词的时候,我常常会忘记刚才读过的内容。也许,这就是我当时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时所发生的事情。
我习惯性地想用原来的方式来读这本书,可我发现这行不通了,书中的文字在我面前突然变得支离破碎了。文字被拆分成一个个孤立的单元。对我来说,想要理解一个完整的句子的含义,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我又多了一项需要治疗的病症— 阅读障碍。我试着不去思考这件事。每当语言训练不顺利时,我都会安慰自己,我只是累了,这种负面的情绪都是暂时的。语言训练一结束,我就轻轻地回到自己宁静的世界里。那里流动着静谧的快乐。
只是不能那样想。
我可以在我们的交流中摇摆不定,听不到错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会认为我只是累了,或者说这些骚乱都是轻微的和暂时的。我们的会议一结束,我就会轻轻地回到那无处不在的静谧中去。
Jackie Ferrentino
04. 我的宁静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我要扮演的角色很多:女儿,姐姐,演员,室友,女朋友。我有一套协调这些复杂角色的方法,因为洞悉各个角色的需求对我而言并不难。但是在我得了中风之后,我情绪的敏感度明显地减弱了,我很难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了。其实我对别人的想法和需求不太感兴趣。我想,这种对人际交往的淡漠可能源于情感和生理这两个方面。
我左脑的中动脉发生了破裂,出血渗入了脑侧裂和左基底神经节。脑动脉的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对大脑的语言中心提供血液。人们通常认为基底神经节与运动控制有关,其实它也会影响人的认知和情绪。
神经节的损伤会钝化人的情绪和意识,使人的行为缺乏目的性。由此看来,脑动脉破裂对我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而最显著的病征就是语言功能的退化。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所患的病不是语言障碍那么简单。
发病后,我常常感到迷茫,内心也变得越发空虚。在我心灵中的这片空地上,出现了一个宁静的世界,那里总是闪烁着温暖而又灿烂的光芒。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我内心的这片宁静之地。
父母非常担心我会出现继发性中风的症状,因为那是常见的脑血管破裂的并发症。对此,我并没有感到很忧虑。我时常陷入冥想中,高兴地在那片宁静之地玩耍。我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片宁静的存在,但后来从其他左脑损伤的患者的报告中,我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
在《 Injured Brains of Medical Minds 》这本书中,临床心理学家斯科特·莫斯描(Scott Moss)记述了他患失语症的经历。他写道:“我确实感觉自己的理解能力变差了,只能大概地了解别人说话的意思。我仍然能够像以前一样集中注意力,可是就算我认真听别人说的话,也听得不大明白。那些词语和短语,在我的脑中没有任何意义。这只是我遇到的一个小麻烦。更严重的是,我连自言自语都不会了。我好像是一副空壳,好像一言不发就不会担心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一位哈佛大学的神经解剖学家,吉尔·博尔特·泰勒( Jill BolteTaylor ),也曾记述过类似的经历。曾患严重的脑中风的她,将个人的经历和领悟完整地记录在了《 MyStroke of Insight 》这本书中。她在书中写道,“大脑中喋喋不休的声音”被“无处不在的宁静取代了”。
Jill Bolte Taylor:《 My Stroke of Insight 》作者 | brainchemist
她一时无法适应那种静谧,那份寂静似乎要吞噬掉她的内心。究其原因,泰勒认为,脑中风可能影响了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注意力的传输,因而改变了人的认知。
精神病学家伊恩·麦基尔基督 ( Iain McGilchrist )对大脑的生理学原理曾进行过更详细的阐述。他在《 The Master and His Emissary: The Divided Brain and the Making of theWestern World 》一书中讲到,大脑就像一个从中间裂开的核桃,它的两半被称为半球。
每个脑半球都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处理单元,就像是两台并排放着的电脑。人的大脑的左右半球常常协同合作。可中风患者的大脑中,只有一个脑半球在努力地工作,另一半球则处于修复中。左脑主要控制语言和逻辑思维,而右脑掌管着创造性和直觉。
qqtext
人们常说自己是“左脑型人“或者”右脑型人“,但其实这种分类是不科学的。“左脑型人”的左脑不一定总是比右脑灵活,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大脑的两个半球会根据当下的实际需求,相互调节平衡。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也同样存在于大多数的脊椎动物中。
举个例子,一只正准备捕食猎物的鸟,需要同时运用左脑和右脑,左脑负责判断目标物是不是真正的猎物,而右脑负责让鸟在捕捉猎物时,保持警惕,避免出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况。
麦基尔基督解释道,“鸟类在捕捉猎物的同时警惕捕食者,这不是简单的分散注意力就能做到的,这一过程需要同时运用左右脑不同的功能。”
我们左右脑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是非常大,只是各有各的侧重点。与右脑相比,我们的左脑更加注重细节。由于人的两大语言中心都在大脑的左侧,所以左半球对语言功能的掌控更多一些。左脑也有感知的能力,只不过右脑更具有敏锐性,比左脑更警惕,因而更容易接受新的信息。
在麦基尔基督的书中,他是这样解释左右脑的差异的:“人的左脑更倾向于做自己熟悉的事情。它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摆满镜子的房间里,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做出回应。恰恰与之相反,右脑没有被禁锢起来,它的视野更为开阔。”
书中的这一段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由于左脑损伤,我丧失了语言能力,那曾是我赖以生存的才能、认知自我的方式。可是现在,我只能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官打交道。
不过,我终于逃离了那个“禁锢”左脑的镜子屋,我的右脑变得越发活跃了。我正试着用一种全新的感官来洞察这个世界。那种感觉很奇妙,我与周遭的世界连接着,可是我所看到的事物总是缺乏维度,我甚至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了。内心的那个“自我”似乎已经离我而去了。我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
我心中的那片宁静实在是太安静了。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左右脑支配地位的改变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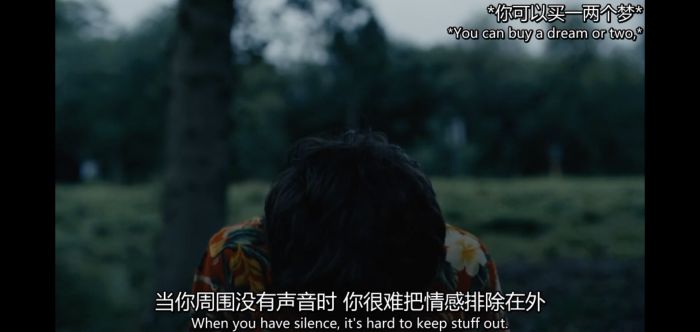 《 the end of the fucking world 》
《 the end of the fucking world 》
原先擅长言语的左脑起着主导作用,可脑中风后,我的右脑暂时占了上风。以前的我总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个声音不停地在我的脑中回响。我很难准确地描述那个声音,但我知道那是我每天早晨醒来就会听到的声音。
我的大脑在告诉我“要起床了”,“该做早餐了”。有时,那个声音会督促我进行自我批评,甚至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有时,那个声音会鼓励我,帮助我了解自己的处境,甚至带领我逃出困境。
我的大脑在慢慢地恢复中,内心的独白开始零星地出现了。可是躺在病床上的我,并没有意识到那些内心的声音可能再也无法完全恢复了,我只是觉得自己的内心深处少了些什么。
值得庆幸的是,在动脉瘤破裂后,我仍然可以思考,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思路比以前还要清晰。我的大脑还保留着复杂思维的能力,可是那些思绪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互交织、碰撞了,我的思想变得不那么深刻了。那不是因为我的大脑愚钝了,而是大脑将思维单纯的一面表现出来了。
就总体而言,这种内心的宁静对我很有帮助。我问自己:“我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由于听不到内心的独白,我几乎无从了解自己的病情。假如我知道自己得了脑中风,又患上了失语症,想必心情会很糟糕吧。
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叙述者了。
 《 one day 》
《 one day 》
05. 现在的我
十年过去了。在这几年间,我又经历过一次大手术。经过长期的语言治疗,我的语言能力恢复了一大截。可还有一部分语言能力永久性地缺失了,我不知道这占了多大的比例。
经历过这场大病,我可能跟五年前、或者十五年前的我不一样了。甚至在 50 秒内,我都可能变成另一个人。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脑损伤患者身上。其实每个正常人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说话的方式、思考的方式都会有所不同,就好像有很多个版本的自己。
当我们和别人谈论起自己的童年时,或者回忆以前的经历时,我们的大脑中都会出现那个以前版本的自己。只不过区别在于,脑损伤患者可以更为快速地在不同版本的自我之间切换。
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总是充满向往,希望一切按计划完美地进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迎来了下一阶段的新生活。我们像是缺少装备的战士,在生活的战场中摸爬滚打。
由此看来,生活的目标不应着眼于追求完美。也许顺其自然才是对生活最好的成全。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为生活的强者。
语言既是我的障碍,也是我的解药,我一直在练习写作。即使语言不再像从前那样流畅了,我相信我还是会坚持写下去。好口才是一种天赋,可有时,沉默也是一种智慧。
语言着实美妙,也只有寂静之音能与之相媲美。
点这里,让朋友知道你热爱脑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