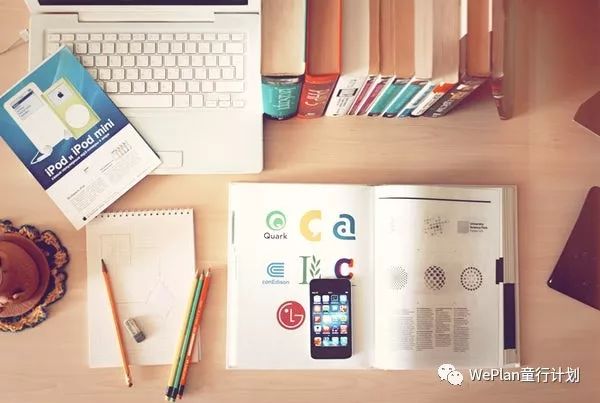那我是如何生成这种自我推动的梦想呢?
“我也没怎么特别培养,平时都不管她,她都是自己学的。”我母亲总是这样说。
我母亲说的话并不是藏着掖着,也不是假话,我父母确实从小不怎么管我,基本上任由我自己长大。
从小到大,父母没有检查过我写作业,也不会催我写作业。放学先在楼底下跟小朋友玩,写完作业看动画片和电视剧到十点多。不会做的题并不问父母,都在学校自己想办法解决。除了学校推荐的辅导班,父母不曾给我报培训班。高考报考专业父母也没有任何干预。
但我的父母是完全放养,毫不过问我的成长吗?或者说,放养就是父母的养育密码吗?
并不是的。
父母不管我,但他们做到了助推。
去年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泰勒有一本书叫《助推》,就是讲用一些无形的方式引导,让人不知不觉中行为被改变。
家庭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孩子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做到的。
父母对我的最重要助推是什么呢?回想我的成长经历,文学、物理的追求都是因为阅读。
父母最重要的助推就是带我阅读。

从我一两岁的时候,母亲就每天给我读故事。三岁开始,母亲开始一边读故事一边教我识字,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就让我自己读一段。这样不知不觉间,到了小学一年级,我已经可以独立阅读纯文字的故事书了。
在阅读方面,母亲并没有强求教育意义。她知道,兴趣才最重要。我在小学一二年级的全部阅读都是童话,读完了《格林童话》,读《红色童话》,还有《一千零一夜》。
三年级之后,母亲在预算很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常给我买书,例如《少年科学画报》,还有一套常看不衰的连环画版《中国通史》和连环画版《红楼梦》。
到了四年级我们跟随父亲去英国访学,母亲带我去的第一个玩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在那里,母亲推荐给我《简爱》。从这一本书开始,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宝库:是少年简装版世界名著,比原文好读。《双城记》、《蝴蝶梦》都是我那时候的最爱。我还看完了馆藏的所有克里斯蒂侦探小说。
后面的人生已经不用父母推动。我因为书而树立梦想,从书中学习,以读书来自我提升。
这个世界上,只要一个孩子掉进了书的海洋,他/她的一辈子基本上并不用担心走不好。
因为这个世界的智慧,都是用书来传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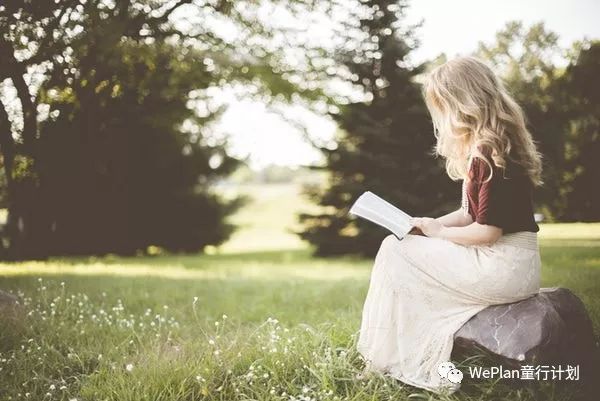
父母的助推,还体现在并不限制我的兴趣,让我广泛接触,自我选择。
我博士阶段为什么又转到经济学。
追溯源头,要追到小学五年级。我从小喜欢画画,五年级发现了日本漫画,开始临摹。很快,一类历史浪漫主义漫画闯入眼帘,先是《凡尔赛玫瑰》,让我了解玛丽.安东瓦内特,联系到《双城记》,让我对法国大革命充满好奇。然后我读到最喜欢的《花冠安琪儿》,看到传奇动荡的文艺复兴,随着冒险的女孩,一路遇到博学风趣的达芬奇,年轻浪漫的拉斐尔,还有教皇和私生子、骑士和艺术家,所有这一切,在少年心里种下文艺复兴的种子。
我感谢父母从来没有禁止我看漫画。通过漫画,我爱上历史。中学时最喜欢的就是追溯历史上真实的法国大革命和文艺复兴,常找相关的书,乐此不疲。
因为这方面的阅读,遇到令我追索多年的李约瑟问题:为何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在大学之后,开始阅读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波兰尼的《大转折》、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和《启蒙的时代》,开始思索人类历史上“现代化”的大转折,后来,越来越发觉经济历史研究中强烈的吸引力。再后来,我就选择了转读经济学博士。
正是父母的允许,让我得以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在我的心目中,
阅读类型并没有高下,只有类型中作品的优劣。
只要会读书、读好书,能从一切阅读中获得知识和见识的给养。广泛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各个类型之间往往产生奇妙的碰撞,产生跨学科思维。
跨学科思维,总在我意料之外给我帮助。高三去参加新概念作文竞赛的火车上,我痴迷于海德格尔的《人,诗意的栖居》,结果现场看到三维屏幕保护程序,就写了有关人的自我身份、对存在的认知、宇宙不确定性的文章,后来获奖。
在读博士期间,我去参加IMF北京办公室的面试,以物理引力场的概念阐述我对国际贸易的想法,也当场获得了专家认可。我写作《北京折叠》的最初灵感,是在国家大剧院听《布兰诗歌》音乐会,眼前浮现北京上空辽阔的灰色画面。其实所谓灵感,并不神秘,只是吸收的信息在头脑中相遇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