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村庄,如果没有矿产或旅游资源,那么有多少外出打工者,占比几何,通常由它与城市的经济地理距离决定。
距离近者,当地人依靠农副产品就可以获得发展机遇,土地也可能被征收,在城市化运动中从集体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距离远者,当地人往往通过外出打工来寻求机遇,而这其中又因距离之远的程度不同、农业结构或文化观念不同,有的外出务工起步早,有的起步晚。
匡村
(村名为虚构)
属于后者。它位于四川东部丘陵地区,距离省城成都一百余公里,是一个寻常村庄。两条山脉将它与其他村庄分开,而之间分布着居住楼、田地,并躺着一条水泥马路,人们由此通往外面。在这里,成年户籍约1100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靠常年外出打工谋生,所涉行业主要包括建筑、电子、服装和家具厂。
我来自匡村,在那出生,也在那长大,见证过第一批女性独立外出打工者离开村子,从那起看着身边的亲朋和小学同学,一代接一代地到城市打工。多年以后,自己也离开那里漂泊在城市。

重庆方言喜剧《山城棒棒军》描述了两段棒棒军进城打工史。图为该剧第一(1997)、第二部(2007)主演庞祖云。2008年10月6日,
庞祖云
因突发脑梗塞抢救无效病逝,终年67岁。
1995s
50后、60后与第一批留守儿童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范成大,南宋,《夏日田园杂兴·其七》
“每一天都做着,别人为你计划的事,你终于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
——甘萍,1994,《大哥你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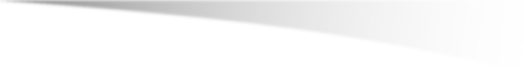
那是1995年、也可能是1996年的一天,村里马路边停着一辆中巴车。我就读的幼儿园也在马路边。园长,是唯一的教师。她走出来招呼我们站远点,不要靠近车,不要看热闹。
车上坐着几位村里妇女。天天见面的小卖部老板娘也坐在里面,靠着窗,好像吃着饼干。她叫素兰
(化名)
,生于50年代末,丈夫是匡村第4生产队队长。
车顶捆着棉絮。车外站着送行人。
车上的人就要远去,先到县城换乘,再南下到深圳。我后来知道,有人来招工,她们跟着集体进了深圳的服装厂。这是村里第一批单独外出打工的女性。

《山城棒棒军》第一部(1997)第2集,在等待巴士进城的人们。
站在马路边,我也渴望坐上那辆车,想象坐上它能去往任何一个地方,比如爸爸妈妈打工卖菜的成都。在此之前,1994年暑假,我第一次出远门,去了成都,而一去就对城市好奇,见到堵车兴奋,睡觉前也要数好一阵窗外的车鸣声。假期结束,回到老家,恋恋不舍,即便上厕所也会在脑海里去重现在城里的所见所闻。
总之,素兰去深圳了,然而半年后就回到老家,重新打理小卖部。我又可以天天见着她。自那年以后,素兰没有再出过远门。她和我奶奶关系很好。这两年,奶奶患上高血糖并发症,身体状况不比以前,素兰有时会来镇上找奶奶摆谈几句,她去过外省,不知有没有向从未出过省的奶奶讲起一些故事。
不过,村里比素兰更早外出打工的是中年男性。第一批是在80年代。他们在石厂、矿区干着纯粹的体力活。
不幸的是,最早外出的几位受当地黑恶势力控制,被卖给矿区,期间脑部遭遇创伤,偶然逃离后神智也大受影响。他们回家后,再也没外出打工,靠体力帮其他人收割水稻、麦子或油菜赚钱,这些人家一般是家里劳动力在外打工,在农忙季节需要请帮手扛、挑、抬。
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村里一批一批的男女开始离开,先是中年人,后是年轻人,先是男性,后是女性。如今看来,他们也有共同特征,其中之一是结婚生子后才出门。第一批留守儿童随之产生。这些80后孩子,没有得到后来一辈的溺爱,早早在家跟着爷爷奶奶做起农务。“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所谓寒门孩子早当家的说法,经常用来注释他们。
外部世界对于外出打工者而言是不确定的。然而,他们还是陆陆续续流动到城市,去那打工,去那挣钱,渴望改变生活现状。据赵树凯统计
(《农民流动三十年》,《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1期)
,恰巧是在90年代中期的几年间,农民工在规模上急剧扩张,达到了新的高峰。
他们不再像曾经那样为一个遥远的、抽象的、被计划的理想而活,就像甘萍在1994年唱的《大哥你好吗?》,“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而这同时意味着需要“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

甘萍演唱《大哥你好吗》(1994)MV画面。
2000s
70后与建筑行业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张俞,北宋,《蚕妇》
“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陈星,2000,《离家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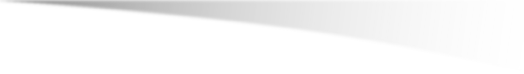
如果说在90年代,村里外出打工的方向还主要是石厂、矿区、服装厂、家具厂或到菜市场做生意,且这些行业的吸引力平分秋色,那么到了世纪之交,一个新的行业即将崛起,并迅速在此后十年内改变了他们的就业结构。
这个行业就是建筑。
在80年代,中国已经在深圳等城市开启了商品房探索之路。1980年,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深圳开工,次年深圳与港商合作建设的国际商业大厦在全国率先试行工程招标承包制。不过,商品房时代的兴起始于1998年。那一年,国发第2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而这意味着,一场以土地开发为中心的城市化建设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房改改变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财富分配,而于农村打工者而言,也改变了他们的就业
(2001年,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规定从次年3月1日起,一律取消包括赞助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等在内的收费)
。
村里从前在其他城市从事其他行业的,也纷纷在这个时候转入到建筑行业,进入工地,承受更繁重的、更高强度的工作,渴望能因此改善收入。有技术的去做木工、水泥工,没技术的去做杂工。同第一批相比,此时是70后、而不是50后或60后成为主力军。
生于70年代末的付丽
(化名)
最终也加入了他们。她刚嫁到村里不久,孩子也刚出生,但还是和丈夫一起去了工地。就在两三年前,她还在镇上过着令人向往的生活。父亲是镇上经营化肥规模最大的生意人之一,持有门面数家,属于当地高收入群体,远近闻名。
而工地上的身影,除了70后,也有其他人群,只是在村里的占比不高。更年长者,包括当年已经五六十岁的40后老人。不过,他们的去处并不远,70后跨省,他们就在县城附近。年龄大了,走不远。更年轻者,自然也有。他们是初中刚毕业、甚至没毕业的80后,村里马路边最熟悉的那位“大哥大”跟着父亲去了工地。读书期间,他是不少学生心中的“大好人”,上能爬树取鸟窝,下能潜水拿鱼,一到周末,要么邀请一群人到家里抓住手柄玩游戏,要么带上他们到山上用弹弓打鸟。捣蛋的事做尽,曾经风光无限。
虽然性格不同,家庭境遇不同,到了打工的年龄,他们都离家去了城市。工地是吸引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也是最受公共舆论关注的行业之一。这里的高工资也伴随着高风险。工钱难拿,安全难保障,在钢筋水泥间穿梭,轻则磕磕碰碰,重则伤脚伤身,恍如“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陈星在2000年的一首《离家的孩子》在此后数年令出门在外的人感触。“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2005s
80后与苦涩的恋爱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陶渊明,魏晋,《归园田居·其三》
“当你扔下我一个人说走就走,其实我也知道你很难受,只是这个世界把你我分两头,割断情思与占有,想起你我相爱的时候,相见只能在电话里头,我真的好伤悲好难受。”
——郑源,2006,《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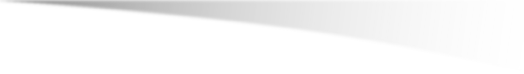
时间转到2005年,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过半。村里外出打工的80后渐渐增多,而不久前,他们还是第一批留守儿童。
他们进入的打工市场是浩瀚无垠的。的确,这期间,中国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增长,尤其在2007年创下了新世纪以来的GDP最高增速纪录:14.2%。制造业和服务业跟着飞速扩张,外贸订单也随之猛增。
村里外出打工的这些80后,除了工地,有的也进入到上世纪父母辈去过的服装厂、电子厂。而现在他们二十岁刚出头,一个像花一样的年龄。父母辈是在结婚生子后离家打工,与此不同,他们往往在十六七岁就出了门,以单身的状态打工。

由范明、潘雨辰、陈思诚等人主演的《民工》 (2004)剧照。
他们要恋爱,然而恋爱是残酷的。
在江苏常州服装厂打工的谢艳
(化名)
就哭着回家,向家人和亲人妥协,接受了一段相亲而来的婚姻——她后来的婚姻并非不幸福,可既然谈到婚姻,自然需要隐去与她的具体关系。她之所以要痛哭,是因为在外打工多年已经拥有相爱的人,如今不得不和他分手。
摆脱父母的影响和限制,去追求独立、自主,通常被认为是80后一代的特征之一。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想法、观念,更向往自己去选择、决定。而对于匡村来说,这一切终究要比城市来得慢。
就像前面所说,外面的世界在农村定义里是不确定的。他们更擅长于处理熟人关系。子女在外认识的人,在他们看来必然没有本地人可靠、可信,所以倡导交友要慎,恋爱不许。
这是一种扎根于骨子里的观念。村里也有和外地人恋爱结婚的先例,两人在工厂里认识,女方最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这一例子进一步证实他们的观念,并使之反复加固。
谢艳当然也反抗过。家里最后派舅舅到服装厂与她面谈,把她带回家。父母早年的打工拼搏经历,也形成一种压力,“得对得起他们”,无法直言,无法说不。
村里第一批留守儿童长大,外出打工,到一个更广阔的陌生人世界,是去改变生活,也是去建立不同于父母辈的陌生人社交,但即便遇见相亲相爱之人,也困难重重,“只是这个世界把你我分两头,割断情思与占有”
( 郑源,2006,《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我不知谢艳是否是唯一有此经历的人。要说回到村里的熟人社会,一切也已改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会种庄稼,无法在田地间寻求满足。所谓回不去的乡、进不去的城,也因此首先用来表述这一代外出打工者。
当然,“回不去的乡、进不去的城”一般被用来指当前城乡区隔。在当前的社会制度安排、生存压力之下,向前一步,无法融入城市并被完全平等对待,向后一步,无法再去适应家乡,生活和工作观念已变。
2010s
打工大半辈子与养老
“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
——白居易,唐,《燕诗示刘叟》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做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
——筷子兄弟,2011,《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