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中男性形态各异,即便披覆着强烈的道德教化功能,但是每个角色的特色和善恶依然有丰富的表达。

▼ 本文由豆瓣用户@苏美 授权发布 ▼
先开宗明义,假如一个人谈到聊斋,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它不过是一部落魄书生意淫美人的故事集罢了。那我会谨慎的设想:第一,他对聊斋所有的知识也许只来源于影视剧改编、道听途说以及有限的几个所谓名篇;假如上述这一条被证明不成立,第二条设想就更糟了,那就是他也许只能看到他想看的。这涉及到能力问题,至少在我这里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指控。所以此上两种推测,我都很谨慎。于是我突然意识到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他也许看到了假的聊斋志异,也就是说,选本选得很有倾向性,也就是说:它就是朝着固化“书生意淫美人”这个成见为目标进行的编选。这样的选本我没有看过,但是可以想象为了销量,出版社会进行怎样的操作。虽然从出版角度这样也无可厚非,但是实际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进行对话的文本不一样,鸡同鸭讲那是难以避免的。
聊斋的版本学研究不是我的专业,依比较通行(但未必准确,以及学界未必有定论)的说法《聊斋志异》分16卷共491篇。这些篇目中男性形象纷繁多样,当然了,我这里谈到的“男性”不包含男鬼、男神、男妖、男狐狸精(是的狐狸精也有男的,部分有双性恋趋向且极具吸引力),而仅仅是那些人间的男性,这些形象哪怕从今天的角度看也非常有意思。
《沂水秀才》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秀才在山中读书(套路),夜半来了两个美人(套路兼套路)。这两个美人含笑不语,一个美人,拿出一块白绫铺在桌上,白绫上写着一行草书;另一个美人则在案上放了一块大约三四两重的银子——这显然是道选择题。秀才选了银子。两个美女笑盈盈收起白绫,手拉手出门了,丢下四个字:“俗不可耐”。我们今天有强大的解构能力,可以轻松的把这道选择题里的道德压力消解掉,比如那块白绫也许是一方巨额银票;而更为直接的方式是拒绝答题:强烈要求加上你两姐妹的选项我再选。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的精神价值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商业社会溢出,身为(貌似)读书人在无人旁观的境况下面对这样的价值拷问究竟会如何抉择。这个故事的结局显然符合了我们心理那阴暗的部分:看,一个读书人的虚伪。但深夜到来的两位美女显然是正确回答的奖励品,她们代表的价值观至今都没有被摒弃(虽然很大程度上被遮蔽),那就是对男性高洁志向和满腹才华的倾心。我至今也好奇那方白绫上的草书到底写着什么,如果是诗文,两个深山女鬼会抄谁的诗。故事的结尾也还是套路:两位美女走后,秀才一摸袖子里的银子,渺然无踪。
和沂水秀才同样路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叫《嘉平公子》。这位公子出身世家,年方十七,风神秀逸,是一个颜值很高的翩翩少年郎。他去参加考试偶然路过一家妓馆,看见有个漂亮的女子冲他笑,接下来也是套路,姑娘夜半前来,两人缠绵枕席自不多言。但这姑娘话说得很奇特:“妾慕公子风流…区区之意,深愿奉以终身。”有一天冒着大雨前来,小脚上的锦缎绣鞋全是污泥,全身都湿透了,一片痴情可见一斑。当然,这位姑娘不久就被发现是一名早已死去的青楼女子。嘉平公子得知此事,拿来问她,她说:你想得到美娇娘,我想得到美丈夫,现在各自如愿,人和鬼又有什么分别?嘉平公子觉得她说的对。公子的父母得知此事当然不悦,但这位姑娘一篇痴情,他们想尽办法也赶不走这个女鬼,然而最终使女鬼离开的办法,却简单极了。有一天,公子写了一张便条,上面全是错别字。女鬼看了便条,回想起来冒雨淫奔的夜晚,她随口吟诗而嘉平公子居然接不下去,鸳梦一下就醒了,在便条后写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这个怎么也赶不走的痴情的女鬼自此渺无踪迹。嘉平公子当然是徒有其表的绣花枕头,整本聊斋中,鬼的世界总是下一等的,暗无天日,充满痛苦、煎熬和折磨,饮食度日也只能仰仗阳间的供奉,大部分书生和女鬼的恩恋都于“拯救”这个母题:为死去的女鬼昭雪的,迁坟的,从恶鬼手里救出的,带她去投胎的,给她一个容身之处的,大量的篇幅里鬼都处在被动、接受和报恩的立场,但嘉平公子确实整本聊斋里第一个被女鬼抛弃的人类。我们当然可以假设,这样故事无非穷且丑的的落魄文人借女鬼之口揶揄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秀才们,这完全有可能,毕竟用“羡慕嫉妒恨”也可以掩盖或者消解价值观取舍问题。但问题是,我为什么对这个故事如此心有戚戚焉?这样一个徒有其表、不学无术,全无趣味的人似乎充斥着视野,让人想到“满目疮痍”四个字。假如这是落魄文人的白日梦,那我也大胆忝列其中,就此落魄下去。
但是另一个叫王勉的书生,却在一个叫《仙人岛》的故事里活得非常幸福。这个书生有点才学,因此目中无人,把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挖苦了个遍,后来他走大运,遇上海难一番磨难居然娶了一位仙女为妻,但是呢,他的太太,这位叫芳云的仙女学问比他大,诗书词赋无不精通嘴巴还比他刁蛮,夫妻俩几次引用古诗文拌嘴,书生都力不能敌,还是太太笑眯眯的劝他:“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法也”,王勉的反应是“王大惭,遂绝笔”。在神仙的世界,男人有才学是一件不甚要紧的小事,在那个世界似乎有更为高蹈的价值可以追求,相比《嘉平公子》,以王勉这位才学不够嘴巴还刻薄的书生故事就没那么凄厉,甚至圆满,那么我们无法不问:为什么?为什么王勉可以在历经劫难后被仙人世界接纳,即便他带着人类的种种缺陷?答案只有一个:因缘。
这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词汇。聊斋中大多数女性的命运都归结为因缘,聂小倩遇到宁采臣,梅女遇到封云亭,瑞云遇到贺生。因缘的那一头连接的就是聊斋里那些男性。他们好端端的坐在家中读书(或假装读书)就会被花妖,狐仙,女鬼和仙女来搭讪,然后被迷惑、被侵害、被讽刺、被测试、被戏弄、被恳请、被托付,被爱或被抛弃。在人鬼仙的世界里,这些书生的形象并非如此完美,即便以当时的伦理道德来看大部分也都有相当的缺陷:懦弱无能(《邵女》柴廷宾),二三其德(《鬼妻》聂鹏云),朝秦暮楚《嫦娥》宗子美,为人吝啬《僧术》里的黄生,品格低下《丑狐》穆生。但同时,却又那么多惹人喜欢的书生形象,《巩仙》里一诺千金的尚秀才,《青娥》里单纯可爱的霍桓,《聂小倩》里坐怀不乱的宁采臣,《梅女》里有情有义的封云亭,《林四娘》里解人语的陈宝钥。书生们当然不只是坐在家里意淫女鬼,他们得读书,干农活,看小卖店,到日子得去赴考,得赡养父母,张罗家务,去庙里抄经,去开馆授学,他们也得有个营生。有些后来发达了,有些则一直落魄,有些娶了神怪,有些死掉且不自知。但是这些篇目中,好看的是花妖狐仙,而不是男性,在另外一些篇目中男性的形象就更加鲜活有趣了。
聊斋有一篇奇文叫《姚安》,说的是一个叫姚安的男子想要娶一个名叫绿娥美人,就把自己老婆推下井淹死了。娶回绿娥之后,两人感情很好,但是姚安是个妒男,怕戴绿帽子,当真将太太深锁房中,出门也要拿斗篷盖住头脸,但最终还是因为一次误会杀了绿娥,被人告到官府用尽办法才免于一死,回家来得了癔症,总是看见有精壮男子和死去的绿娥做些男女之事。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学上的强迫症和妄想狂了吧?本以为最后此人会因痴情而死,结果最后是气死的,因为家里被小偷偷了个干净。明清小说相比较唐传奇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强烈的道德教化色彩:喜欢美色从来不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丑事,这个基本价值观在聊斋里从来就不是问题,姚安遭受的苦痛究其原因是杀了原配,陈世美停妻再娶都是重罪,何况杀妻再娶。严格说,这不是一篇志怪小说,从现代心理学角度上来看,这是一篇细致描写精神病人精神世界的小说。另外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邵临淄》,说的是一位长期被家暴的丈夫不堪忍受,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身的权利,在一名县令的强力支持下,他的悍妇太太被打了三十大板屁股都被打烂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夫为妻纲的前现代社会简直匪夷所思,最逗趣的是蒲松龄还在底下吐槽,说:这位县令大人出手如此迅猛,是不是吃过女人的亏呀?
还有一篇文章叫《冤狱》,这个故事非常惊心动魄:朱生死了妻子,请托媒婆代为张罗续娶,恰好看到媒婆的女邻居很漂亮,就开玩笑说:哈,就她就行。媒婆说:你把她丈夫杀了我就给你张罗。朱生听明白意思,人家是有丈夫的,就哈哈笑说:好啊。这本来就是个陈请和回答是个玩笑话。却不料女邻居的丈夫不久之后真的被杀了。县衙捉拿了朱生和女邻居去,怀疑二人通奸,吃刑不住,妇人屈打成招。再来拷打朱生,朱生说了一段话,他说:妇人的皮肉哪里经得住酷刑,不过屈打成招罢了。现在她含冤待死,还背负通奸的恶名,就算是神鬼不辨是非,我一个大男人又于心何忍。我从实招来吧:是我想娶她为妻,把她丈夫杀死了,她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罪名我一人承担。
英雄救美的故事我们读过无数的版本,但是这确实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朱生并不真正认识这个妇人,这个妇人也完全不知道朱生的存在。两个人的命运在死牢里纠缠在一起。出手救美时,英雄总被赋予银盔素甲白马长枪的光环,他们救美的成本如此之低,低到我们总误以为那是每一个男人应当应分去做的。但在《冤狱》里却写得分明:救美的成本非常之高,不单要搭进性命,还要搭进名节。宁采臣搭救聂小倩有燕赤霞帮忙,封云亭搭救梅娘有鬼神帮忙,但这个朱生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面对的是必死的结果,他不是救美,而是救人,换做任何一个不美的人虽然动力会弱但最终我相信他依然会选择这么做。这是非常奇特的价值观。我经常在想,是什么阻止了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去作恶,毕竟他要死了为什么他不烧了博物馆的文物,掐死邻居的孩子,往街道上扔燃烧瓶导致百十辆汽车连环车祸——死亡之手已经扼住他的咽喉,人间的法律还能拿他怎么样?为什么不伤天害理,为什么不人神共愤?一个从小循规蹈矩的孩子,一个努力赚钱的小白领,一个中年困顿的丈夫,一个老年丧子的老先生,他走到生命的劲头,是什么在阻止他和全世界决裂把他曾经住过的街巷烧成一片火海?就因为那些满大街和他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朱生明白自己深陷冤狱,回家跟母亲要血衣,可母亲哪有什么血衣,人不是儿子杀的。朱生说:你给我血衣,我也是死,不给,我也是死。早死早解脱。母亲含泪走进内室,拿刀划开自己的胳膊,不一会儿拿出一件血衣来。
如果不是神鬼从天而降,痛斥昏聩的县令并指出真凶,朱生是一定要死的。故事的结尾是,写道被无罪释放的邻居妇人,既然已经死了丈夫,几年后也就被允许该改嫁,因为感念朱生的义气,就嫁给了朱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尾,虽然真正实现的可能性极小,但正因为如此,我就更加感念聊斋肯给它这样一个结尾,不料何守奇这个混账居然在文末批曰:“妇后归朱,似亦可以不必矣。”——请问这种政治正确的人凭什么来做文艺批评?
聊斋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早早就死去的男性,叫孟生。“生”是古代对男子的称谓,大约等于今天的“先生”,孟生就是指一个姓孟的人,这等于说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出现在一篇叫《乔女》的故事里,开篇第一段他就死掉了,后面的整个故事情节他都无法参与,但是所有的故事却又全部围绕着他展开的。这位孟生,在生前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对县里的一名寡妇乔女一见钟情,而且非她不娶,但这件事没有办成他就一病而亡。那么,这位乔女什么样的人物呢,值得他如此痴情。书上说乔女“……黑丑:壑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无问名者。”城里有个鳏夫,家里贫穷无力续娶,才勉强把这个丑陋而且残疾的乔女取走,三年后生了一个儿子后也死掉了。按照书中的描述,孟生遇到乔女的时候,她是一个黑丑、跛足、贫穷、带着一个拖油瓶儿子的寡妇。文中交代孟生颇有家资,妻子过世,儿子才满周岁,急着续娶,说了几家孟生都不满意,突然见到乔女,就非常高兴,暗中托人向乔女示意。乔女不答应,原因是:“饥冻若此,从官人得温饱,夫宁不愿?然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意思就是,我现在贫困到这个地步,跟了您就可以得到温饱,但是我残丑如此,唯一能够自信的,无非是品德罢了,如果再嫁等于一女事二夫,连德行也有亏。那您娶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一段的逻辑是个死胡同:如果你喜欢我就不许娶我;我也喜欢你所以我不能嫁给你。之所以这么拧巴只是因为一个德字。一女事二夫是德行有亏,夫死而守节这才德行高尚。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这当然非常荒谬,但历史自有上下文。孟生对乔女一见钟情的原因文中并无交代,只简单六个字“忽见女,大悦之”,我们无从推断孟生被吸引的原因,听完乔女这番言论,孟生“孟益贤之,向慕尤殷”,去向乔女的母亲提亲,母亲当然高兴,但乔女坚决拒绝了,乔母提出把小女儿嫁给孟生,孟生又坚决拒绝了。一个坚决要娶,一个坚决不嫁,坚持来坚持去,孟生就死掉了。
假如认为乔女封建思想重,那就想错了,后文体现的完全不是这样:孟生死后乔女前去吊丧,极尽哀思。不要说古代,就是今天一个寡妇去男人丧礼上极尽哀思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孟生的家财被村里的无赖劫掠瓜分,周岁的儿子乌头无人照管,朋友坐视不理,乔女就自己去县衙告状,她甚至没有合法的诉讼身份,但几番周折到底把孟家的失去的产业又要回来了,而后抚养乌头长大,请老师来教他念书,又帮助乌头积累家资,修葺宅院,聘娶了名门的女儿,帮他独立门户,最后溘然长逝。一个人的一辈子说起来寥寥数语,过起来一针一线一桑一麻,一寸光阴一寸灰。聊斋里那些花妖狐仙的故事当然引人入胜,但动人心魄的却总是这些现实感极强的作品。假如说有任何超现实的情节,那就是我们始终会问:为什么?孟生当初为什么“忽见女,大悦之”。这是一个极具想象色彩的人物,我们会怀疑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过或者真的会存在这样的人物,文中对他的生平和描述不过几十字,死得很早,却值得乔女用尽一生来报答。乔女在孟生死后有一段非常动情的表述,她说:我因为很丑陋,被世人看不起,只有孟生能看重我;从前虽然拒绝了他,但是我的心早已经许给他了。如今孟生死了,孩子还小,我认为我应当做一些事来报答知己之恩。——好一个“知己之恩”。乔女已经不是“女”而是“妇”,她的丈夫是那个死去的鳏夫叫穆生,她本应叫穆妇。孟生生前她没有和孟生说一句话,却在他的棺椁前掉过眼泪;她没有拿过孟家的一分家财,死后也坚决不和孟生合葬,但她却不顾男女大妨说过“然固已心许之矣”,好在蒲松龄也是通的人,把篇名定为《乔女》而非《穆妇》。日本人对纯爱故事非常热衷,像《情书》这样的电影或类似气质的文学成为类型片在东亚范围内拥趸颇多,但我窃认为《乔女》才算重量级纯爱文本,两个没有名字的人,并非基于荷尔蒙或生命的易逝感才短暂的互相成全,它是硬桥硬马在尘埃里打过滚淬过火,经历过两心相知、生离死别和漫长的人世艰难,一粥一饭,日升月落,它有信念,有重量,有坚持,携带的不是青春萌动或者霎那之间的激情四射,而是生活本身所有的琐屑和耐心,是真正的平静安宁持久——假如真有脱离性的纯爱,它在我眼中就是这样的。
女性声张自身的权利正是这几年的事,我们要求在政治和制度层面上对女性权利进行基本的保障,但是人所共知,女权成为人权的一部分之后,它的道路就极其艰难,只能渐渐在泛文化范围之内成为一种与男性敌对的情绪和腔调,从而摆脱了它强烈的政治色彩,演化为庸俗的性别枕头大战,似乎女性被压迫的根源是男性而非被男权思维固化了的一套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这里头荒腔走板的误读误解真是一笔烂账不堪细说。这种亢奋情绪在文学解读时会导致一种简单粗暴,最典型的莫过于认为《聊斋》不过是落魄文人在意淫美女——这种认识同时贬损了聊斋、男性以及女性自身。
聊斋中男性形态各异,即便披覆着强烈的道德教化功能,但是每个角色的特色和善恶依然有丰富的表达。我们看见有令人不齿的男性,也看到非常令人敬慕的男性。有些是落魄文人,但更有大篇幅的贩夫走卒,商贾掮客,卖梨者耍蛇人跑江湖打把式卖艺的。前现代社会,婚姻重于并不基于爱情,那些古人的爱情欲望是怎么排遣掉的只能从零星的诗词曲赋里揣摩,进入现代社会爱情成为高扬主体性的一面大旗之后人们迅速集结于此:我们对男性的想象突然无比苛刻——兼具前现代语境下的英雄气质以及后现代社会的专情道德。很大程度上我们都在脑海有一个范本,对照现实时义愤填膺怨声载道,我们不承认男性的千姿百态,不接受男性也必然拥有人性的弱点和阴影,不原谅在男性出现任何不满足个体想象的形态。这种英雄想象如此之理直气壮,我们甚至假装没看见宁采臣虽然坐怀不乱但是后来又娶了妾,忘掉了会有男人为了得到女狐狸精的钱财甘愿献身,我们甚至也看不到大多数的书生既非多么善良而且才情也相当一般。那些乐天知命的平凡人,那些不见不平提刀助人的义人,那些遭逢不公三下阴间状告阎罗的好汉,那些同样为女性不专情备受折磨的迷途之人,都被碾碎在这被构建了几百年的英雄想象之中。好在聊斋这本琐琐碎碎不入正统的故事集,因为毫无野心,反倒留下了那么多名姓模糊的、区别于黄钟大吕、家国天下的男性形象,那么日常可感,就像你在车站码头或者便利店随处可见的那些平凡人,各有优劣,各有哀愁,私人生活经不起任何显微镜似的观察和打量,正是他们和所有美好的花妖狐仙神仙鬼怪分享着世界,在时空深处一闪就熄灭,留下那么一段无甚要紧的离合聚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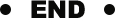
本文版权归 苏美 所有,
任何形式转载请点击【阅读原文】联系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