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田静。
我知道这几天大家看了太多负面信息,心里憋屈,都不想再看了。
其实我写得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所以停更了。
但是,我这两天看朋友圈时,不小心看到一个圈友的帖子,压抑的情绪又一下按耐不住。
本以为最近发生的事情,早已将我炼成铁石心肠。没想到,我还是没忍住,非得要为他们说上几句不可。
我相信你看了,肯定也会想要为他们打抱不平。
这场疫情,把人泾渭分明划分成了湖北人和外地人。
在舆论呼声中,湖北人从人人避而远之,变成了被全国争先善待的对象。滞留在各省的湖北人,都被妥善安排进了酒店。
大家可能完全没有想到,滞留在湖北的外地人却被人遗忘了,隐形在这场疫情热点中。
我看到的帖子,就是一个滞留在湖北的女孩写的,他们中有人住酒店都住到破产,走投无路去街上搭帐篷吧,又被到处驱逐,天天上演现实版【大逃荒】。
在女孩的介绍下,我找到500多个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他们排着队想要诉苦。
真是幸福的人都一样,不幸的人却各有各不幸。武汉政府无暇顾及,家乡政府又不敢轻易接受,他们一下变得里外不是人。
女孩告诉我说,她住酒店的这一个月,夜里哭过无数次。有时真想走回去,哪怕家在几千公里外。

“最后一粒药了。”2月10日一大早,李欣在微信群里告诉大家。
因为患有甲状腺,她出发前算好行程,带足了20天的药,药袋里一粒不多一粒不少。
而现在,李欣有苦难言, “最苦的还是肚子里的孩子。”
大年三十,武汉“封城”的消息还在备受讨论,李欣所在的村“封村”了,所有进出村子的道路全部封闭。
“凌晨四点左右入睡,早上九点左右起来的,心烦易燥一整天。”夜夜失眠的李欣甚至怀疑自己要孩子的决定。
她少了孕妈的期待和兴奋,一次又一次暗想,“
只能说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不该要鼠宝宝的,晚个一年半载也比现在怀着孕强。
”
肚子里的孩子已经18周了,按照计划,2月18日该做产检,她预约了上海的医院。但回家依旧遥遥无期。

回湖北之前,她专门去医院给肚中的孩子开了补钙的药,一天三剂。“医生不给多开,说过年吃的好,不能太补。”
但是谁也没有料想到,身在湖北疫区,过年没有大鱼大肉,她只得减少了剂量,改成了一天一剂,想能多撑一天是一天。
“这下更难走了。”2月10日,终南山团队发表新论文,称新冠肺炎的潜伏期最长24天,看到消息,李欣已经绝望。
同样觉得苦了孩子的,还有年轻爸爸天谬,他滞留在湖北的另一个村庄,女儿患有先天性甲减。
“
每个月都要到医院抽血化验,请医生调整药
。” 女儿一直在广州接受治疗,滞留地所有路封闭,乡镇卫生院都无法到达。
隔着电话,能听出来这个大男人的无奈,他说:“欲哭无泪。”
孕妇和婴儿被群友称为最需要照顾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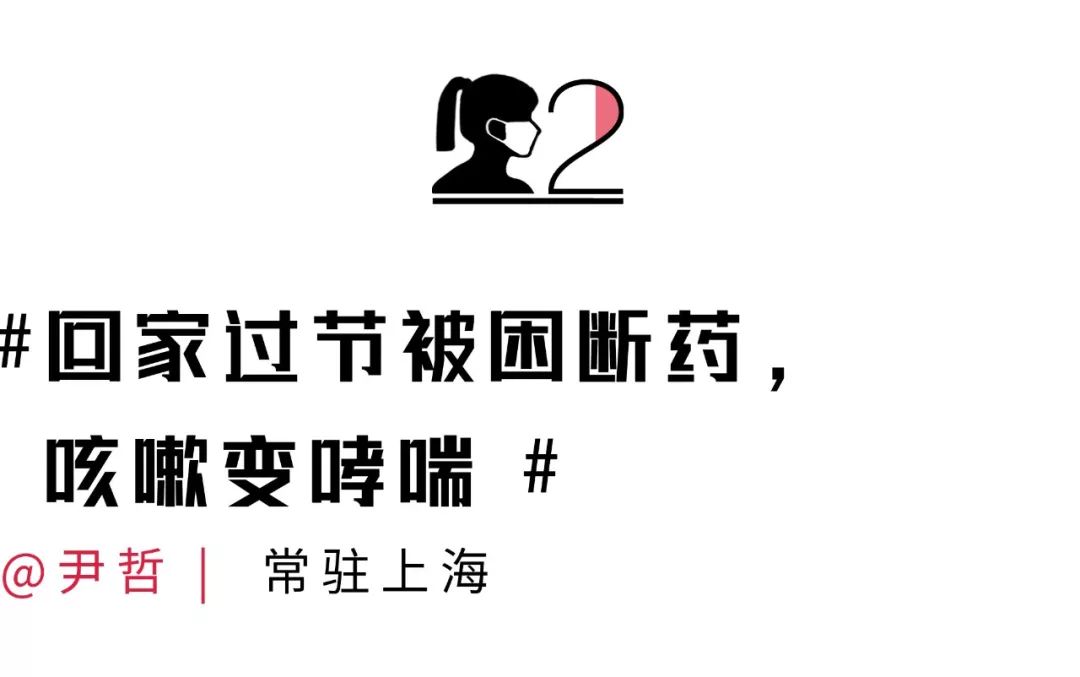
成年的尹哲不属于这个受照顾的范畴,但他是被困住的成年病患代表,一直面临缺药的痛苦。
回湖北咸宁之前,尹哲看到网上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一度想取消行程。但当时官方消息还是可防可控可治,家里老人也认为并不严重,要求必须回去过年。
到家第二天,武汉“封城”了,其他地方也陆续断了所有交通。
“刚开始的几天,城里出现了高价菜,一把青菜几十块。”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封城”逐渐升级成“封小区”。车辆不能出入,只能步行。
尹哲患有过敏性咳嗽,需要长期服用顺尔宁。“封城”后,他把带回来的一盒药降低剂量,隔一两天吃一粒,只坚持了近十天。

△ 这个药厂家叫舒宁安,国外进口叫顺尔宁
他跑遍了咸宁也没有看到一家开门的药店。他想请上海的朋友帮忙寄过来,但所有快递都不接湖北的件。
虽然断药不至于威胁生命,但会一直咳嗽,晚上没有办法入睡,严重的时候会成哮喘。
更让尹哲痛苦的是工作,他是进出口行业的一名销售,每天都要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跟踪生产、协调出货。
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干着急。
因为疫情,整个进出口行业受到很大影响。工厂没法正常投入生产,物流也无法办理出入境,空运成本翻倍。
加之多个国家航空公司停止了往来中国的航线,未来形势如何,尹哲有时都不敢往深里想。

比缺药更加窘迫的是,缺钱。
“他们身边没有多少资金,多几个人来,一个人就出不了多少钱,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12月10日,群里有人发动给学生和刚参加工作的人捐款。
祁红就是群里的学生之一,今年大一的她寒假去了西安旅游。1月19日,她从西安回家,途径武汉转机。
“打算呆几天再走,飞机票是23号下午的。”凑巧的是,飞机起飞前两三个小时——武汉“封城”了。
她寻遍武汉,找到了一家单价80元的宾馆。宾馆附近只有一家超市还在卖一些零食和方便面。
祁红匆匆屯了一些方便面,蹲在宾馆里不敢出门。半个月她没洗换衣服,天天吃泡面,就这样还是花了3000多元。目前,口袋里只剩下1000元了。
“第一次吃泡面吃到吐!”最可怕的是,她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在缺钱的阵营中,祁红还不是最窘迫的,一个被困的群友直接在酒店住到“破产”。
最后,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他买了顶帐篷住到了大街上。但这是他的一厢情愿,他被到处驱赶,四处流窜。
大家都佩服他有个好心态,天天上演着现实版的“大逃荒”,而没有原地爆炸。

听到封城、封路的消息,格桑也没有意识到她会一直滞留在疫区,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
直至1月23日,她依旧怀着期待在朋友圈写下:“想念云南的春暖花开,我想说我从湖北回昆明后,会不会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不久,格桑便接到了航空公司退票的消息。
格桑不死心,想能不能曲线救国,先飞到西双版纳,再回昆明。她乐观写:”保佑我能回家,昆明的家就我一个人居住,我保证不出门,不见人!”
随着疫情形势严峻,她哪里也去不了,酒店也开始下逐客令了。全市剩下5家继续营业的宾馆。“全是满房,订不到。”
唯一有剩余房间的是希尔顿,但价格贵到格桑承受不了——“七百多一晚。”
“谁让你出来的,我们不负责。”电话那头,110的言辞让格桑十分愤怒。
“我1月份就来的呀,老问我怎么这个时候出来,我愿意吗?我活该吗?”
善待滞留外地的湖北人成了主流呼声,全国媒体都在关注流落他乡的湖北人,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措施安排相应住宿和物资保障。
流落湖北的外地人却待在了遗忘的角落。
“我并不是要求政府怎么样,我只是觉得他们的帮助太形式化和表面工作,如果条件差的人怎么办?住桥洞流浪吗?”
朋友圈的网友知道格桑的困境后,“二话没说直接给我转账,要众筹给我去住希尔顿。”
格桑都一一退回去了,但大家的善意让她心生希望。格桑重新振作起来,在酒店免费开设线上化妆教程,以回报陌生好心的圈友。
最终政府出面协调,希尔顿愿意将房费从原件700多元降到500多元。
“短时间内还能承受,害怕一直住下去,耗不起,没收入还要还房贷。”

△ 十堰的希尔顿夜景
她们有个云南的小群,几个女孩甚至商议要走出湖北,这样窘迫的流落在外,实在太难了。
哭过多少次?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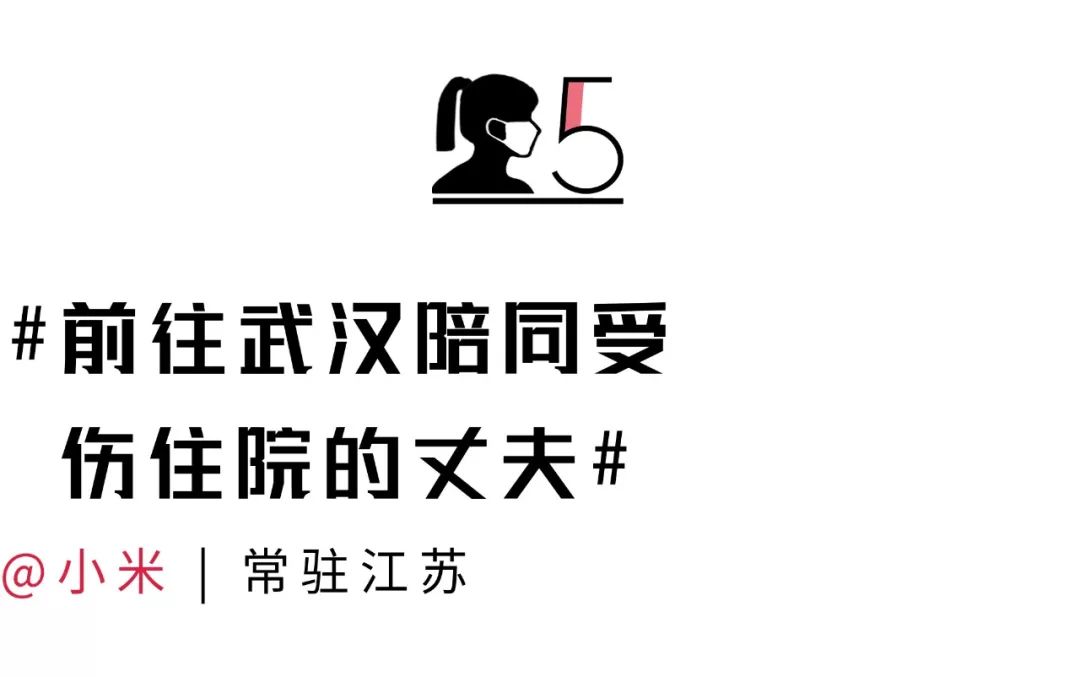
和格桑不同,小米一直没有找到住处,被医院收留在住院部陪骨折住院的丈夫。
夫妻俩每天分食一盒餐饭,两个人都互相推让,都想让对方吃饱一点。
“一下子回到饥荒年代的感觉。”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半个月了。
得知在武汉工作的丈夫骨折了,小米1月13日从江苏匆匆感到武汉。
武汉“封城”第二天,丈夫被医院提前停止了治疗,因为疫情,共用仪器会造成感染。
出院,似乎遥遥无期,钱像一股暗流不停地淌。

△ 小米被收留在骨科住院部,与病人同住
“医院可怜我一个人找不到住处,收留我在骨科住院部休息,非常感恩。”
在住院楼里,小米隔着门就能看见发热门诊人来人往,病毒似乎也随着这些人影四处窜动,他们不敢离开病房。
看着护士的口罩、护目镜和全套防护服,小米内心惊惧。
她数了一下,二十分钟,医院开出去三辆救护车,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好想回家,带丈夫一起回家……”

2月9日,武汉终于天晴了,刘小丽戴着米色的毛线帽,用蓝色的防护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带着12岁的女儿走出了宾馆。
“屋里快要发霉了,出来晒晒太阳消消毒。”这是她滞留在武汉的第18天。
她和女儿住在武昌区的一家宾馆,每天90元。
母女俩尽管已经是最节约的了,身上的钱还是不够,只能向江西老家的亲人借了一些。

△ 刘大姐出门散步拍到的躺在路边的人
1月22日,刘小丽辞掉了工作,从陕西西安出发,准备回江西赣州老家过年。西安有直飞赣州的航班,但“从武汉转机便宜好几百。”
对一名家政工作人员来说,挣这几百块钱不容易。
当天晚上,刘小丽的航班顺利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那时机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带口罩,照常工作,看不出丝毫异常。
为了方便搭乘第二天11:00从武汉到赣州的航班,她带着女儿在机场酒店住了一晚。
熟睡之时,一则通知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23日10点
起,武汉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凌晨2点发布的消息,一觉醒来,措手不及。”娘俩没能赶上下一班飞机。
为了省几百元路费,现在却像无底洞一样往里贴钱,刘小丽真的欲哭无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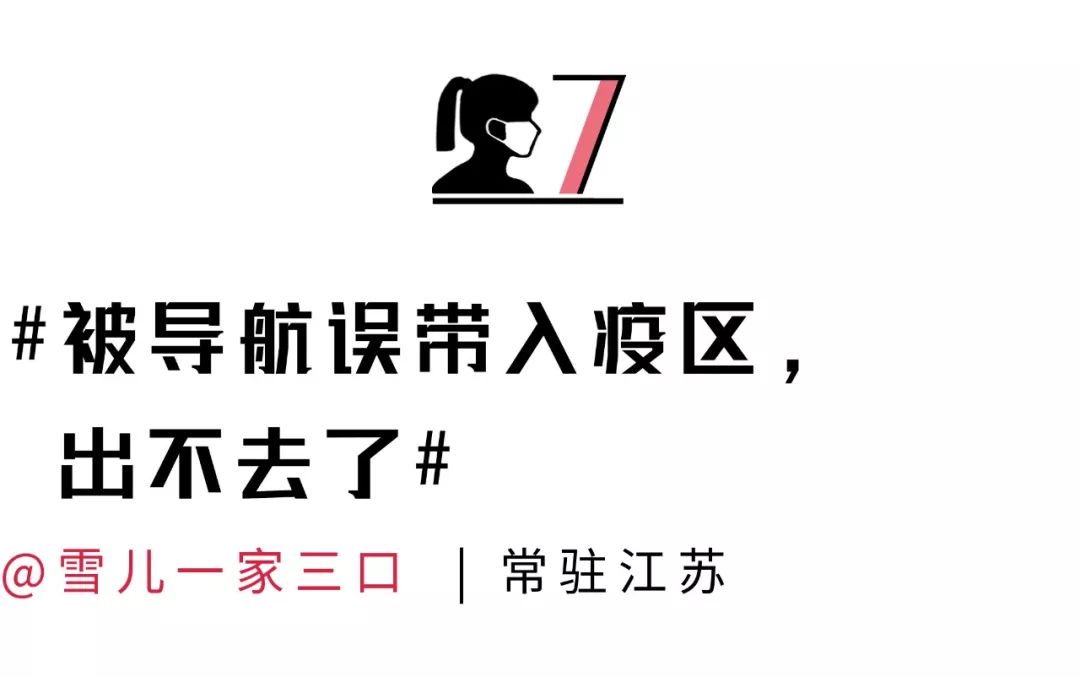
更倒霉的除了转机,还有雪儿一家遭遇的囧途。
“一路跟着导航走,被带进来武汉。”武汉“封城”第三天,雪儿和爸妈从江苏驾车回四川老家,闯入疫区便再也开不出去。
“没有商量的余地,所有求助电话都让自己解决,后来电话不接,偶尔接通也听到求助就被直接挂了。”她并不明白,特殊时期,没有人愿意冒风险承担责任。
雪儿快要哭了:“原来生活真的没有新闻上那么简单美好。”
雪儿和爸妈在找宾馆的路上走走停停。“在网上订了宾馆,开车到了目的地,都被告知不再营业。”
很多宾馆的答复是:“政府不让营业了。”
雪儿又拨通了报警电话:“找不到住处,也找不到吃的。”
对方的回复总是苍白又敷衍:“慢慢找。”

△ 被导航带入武汉的雪儿,每天能吃的也只有泡面
新闻告诉雪儿,口罩和防护服是全国的稀缺品,但是有那么多人捐赠;医护人员紧缺,但一批又一批伟大的医生赶往前线;缺病床,马上十天速成一家千张床位的大型医院。
武汉所缺的一切,在新闻里看起来都“不用担心。”
而新闻之外,年轻的雪儿没有想到,酒店也成了稀缺品,而且没有人可以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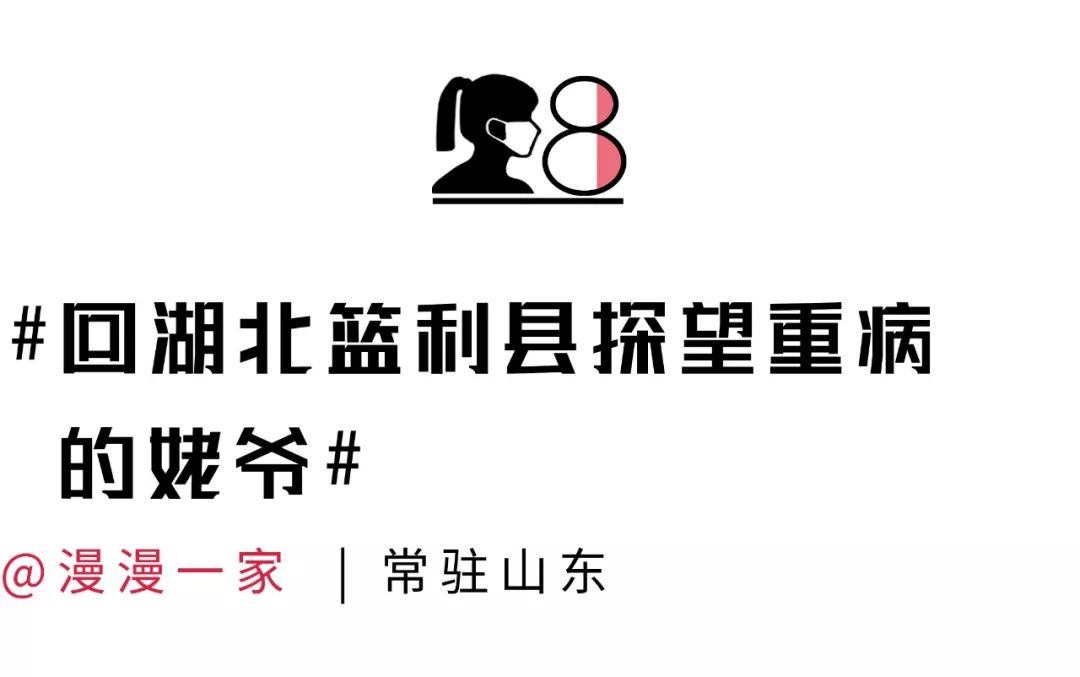
漫漫出发之前就跟妈妈说,湖北肺炎很严重,很可能演变成“非典”那样,尽量不去了。
但妈妈坚持:“你姥爷病了,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回湖北了。”
漫漫转念一想,这也是自己长这么大第一次去姥爷家过年,医生说姥爷很可能撑不过春节,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老人家。
1月22日,表哥、舅妈和漫漫一家从山东开车到湖北。路上车辆少得出奇,也没人戴口罩。
漫漫劝大家戴口罩,爸爸却说:“你看别人哪有戴口罩的啊,不戴不戴,不搞特殊。”同车的表哥也附和:“非典不也过来了,还怕这个。”
晚上,漫漫到达了母亲的老家湖北监利县的一个小村。姥爷躺在自己的房间,告诉别人身上哪里痛,但脸色还不错,还能说笑。
漫漫妈妈想哭,却没有哭出来。
姥爷不知道自己是肺癌晚期,因为大家统一了口径:“总是抽烟才生病的,把烟戒了,慢慢就好了。”
每天,一家子人都要去给姥爷送饭,陪他说话——都戴着口罩。
姥爷吃完饭就下逐客令,他害怕自己的病会感染给家人,事实是家人也担心万一患病会传染给他。
没想到,正月初一,姥爷家的小村“封村”了。

△ 姥爷村口的夜景
村子里的人也没有再互相来往。村口安排了专门的人看守,不让陌生人进出。身在疫区,所有人都闷头在自己家里,不出门也不做事。
“每天就是在家里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在门口坐着晒太阳,然后做饭。”实在憋得慌,就戴着口罩到房前屋后遛弯、摘菜,大胆一点的会去河边打鱼。
正月初八凌晨,姥爷走了。舅舅、妈妈和村里的长辈商量葬礼应该怎么办。村口零星几个人路过问候:“节哀顺变。”
天亮民政局的车把姥爷的遗体拉走了——要销户。
墓地里,舅舅抱着姥爷的骨灰盒,妈妈一直在哭。因为疫情,传统的葬礼仪式都省略了,送行冷清得让儿女们觉得不孝。
疫情带来沮丧,冲淡了亲人离别的悲伤。被困住的漫漫有可能参加不了研究生考试的面试,也参加不了应招的单位考试。

因为一家大型水泥厂委托公司做检测,小帕12月15日来到湖北,先后完成了在黄冈、宜昌、孝感的工作后到达黄石,疫情爆发。
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刷屏了。疫情的严重性并没有像病毒的名字那样快速被人们认识,公司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一切如常。
父亲打来电话让回家:“不行就辞职。”
大年初三,公司紧急通知员工停止工作,就地隔离。小帕滞留在了黄石市韦源口镇,还有一些同事滞留在湖北其他地方。
每隔12小个时,他们要在群里向领导汇报身体状况——有无发烧、咳嗽、腹泻、肌肉酸痛等症状。
“每天看新闻越来越严重,真的很慌,空调吹得脸上红扑扑的,还以为自己发烧了。”
小帕住在一个居民住宅改造的宾馆,这是方圆几百米唯一一户居民住宅。过年前几天,客人都回家过年了,老板也了回城里。
三层小楼,就剩下他一个人,孤孤单单,但好处是接触不到别人——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