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光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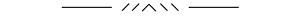
食物中的当代微观小史
文 |
西门媚
早上躺在床上,没头没脑地跟他说:“唉,可惜没小房子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替代小房子的地方。”
“是好多年了哦。杜姐就算再开一个店,也没法复制小房子。”他随口答应着。
晚上,坐在电脑前,忽然觉得椅子有点晃动。问他:“你觉不觉得有点晃?”
“没有啊?”
“再感觉一下……你看灯都摇了!”
“嗯,是在晃。地震了……嗯,微博上还没人说。”
“我刚刚在朋友圈说了,也有几位朋友在说。”
然后我们的对话就转成微信跟帖模式。
“4级?”
“不对,至少4.5级。”
……
“新闻出来了,7级,九寨沟。”
刚才在晃动最厉害的一瞬间,我们曾短暂地停止聊天,都安静地观察等待了一下,在想,如果晃动更厉害,就得采取避险行动了。
我就又想起了“小房子”。
2008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房屋摇动剧烈,我们冲下楼,在街边站了站,看着好多从四周楼房里下来的人,在街边犹豫不定。我们不用犹豫,直接步行去了“小房子”。
平时我们想起小房子的时候,一般就会想起杜姐,想起她的煎蛋面。有时候很馋,想吃她做的煎蛋面。
她做的煎蛋面非常香,油汪汪的,饱满略略有点焦香的煎蛋,配上红油、蔬菜,一闻着就食指大动。
在小房子泡晚了,饿了,经常就央杜姐煮一碗面。夜里来的人,有时一进门,就张口要吃面。好像他们不是来泡吧的,是专程吃面的。
吃了面,舒坦了,这才开始喝酒。
杜姐的面好吃,其实我也大致晓得窍门。在四川,能炼得一碗香辣的好红油,并不算特殊。但是,像杜姐这样做面的,已经很少了。
我知道那独特的配方,主要是猪油的功劳。
大家平时讲养生,讲吃得健康,素多荤少,少食红肉。在家里早没人吃猪油,只吃植物油。吃猪油简直太不政治正确了。
但在杜姐会熬一大罐猪油,给每一碗面里,都大方地挖进一大勺。
我们的身体还保留着原始的喜好,觉得这猪油汪汪的煎蛋面,真是香啊。
在杜姐这儿,是不要政治正确的。大家脱了政治正确的外衣,才会进到小房子,然后就沉溺在这里。
小房子在一个小广场上,是一套民居改造成的酒吧。改造得很简易,红砖墙,加上旧桌椅。桌椅被杜姐用各种花布包了起来。桌上、墙上,胡乱放些土陶罐什么的。说起来,跟一般酒吧并无多大差异。
但一进来,马上就放松了,人可以歪在那些简易的,又被花布重新包裹的沙发上。几个小间里,都是熟人出没。就算不是熟人,多来几趟,那些脸孔也就看熟了。
几个小间后面是个小厨房和卫生间。去卫生间的路上,总看得见厨房里的水池里,堆着没清洗的碗筷。
这是个不那么干净的小店。就如这里不讲究政治正确一样。只要克服怕脏的心理,你就能彻底放松。好比你去朋友家,朋友家如果一尘不染,作客就觉得拘束,会主动要求换上拖鞋,说话也不敢高声。如果朋友家有点杂乱,反倒让人放松,宜歪坐斜躺,宜高谈阔论。
小房子就是这样的地方。当然,更重要的是有杜姐这个“关键人物”。这个关键人物一点都不精明,还有点憨憨的气质,本也不是文化圈中人,平时最爱乐呵呵地笑,请大家尝她新做的小菜,像个邻家大姐,跟谁都不生分,都能搭话,但也不真正介入这些圈子,更不会卷入是非。我想象的沙家滨的阿庆嫂就是这样的人。渐渐地就聚集了成都文化圈、新闻圈的各色人等。这些圈子又细分各类小圈子,大家出现有不同的时段,所以,这里走马灯似的,龙蛇出没。从下午喝茶聊天的作家,傍晚喝酒连带吃饭的画家、设计师,晚上泡妞喝酒的诗人,到深夜下了夜班来此休息一下的报社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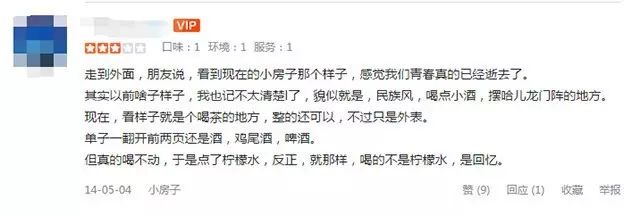
▲
网友对小房子的回忆
五·一二那天,我们到达小房子。小广场上的酒吧茶馆都还开着。就像平时一样,我们在小房子室外的茶座坐定,就看见诗人何小竹拎着电脑走过来。
他是我们的老友,那时,还算是邻居,住得都离小房子不远。他说,他在附近茶楼里写稿子,地震了,他第一个想到的地方也是小房子。
那个下午,小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小房子的常客们也都聚了很多,这些平时出现在不同时间段的人,都在这个下午来了这里。
既然是因为地震,也就不再讲究,不同圈子的人也围坐一桌。先是交流信息,信息都不足,连震中在哪里,多少级,造成了多大的危害都不清楚,猜测纷纷。每个人都拼命想给外面打电话,想报平安的,想知道家人朋友情况的,都打不通。每个人都很焦虑。
正在焦虑中,我们的老友阿多来了。地震之后,他迈开他的长腿,先是从杂志社回父母家看了看,父母平安,他又从莲桂路,走了六公里,就到了这里,他关心他的朋友们。
阿多外表看起来,总是那么不靠谱。他是媒体人,诗人,有才,诗写得好,聪明,过目不忘,但经常一本正经地说胡话大话,东张西望,神情恍惚,坐不住,像个多动症儿童,随时要走来走去。
他极好酒。小房子是他的根据地。他自己住得离这儿不远,白天有空就过来转转,很深的夜里,从外面回家,也忍不住,拐到小房子来看看,看看还有谁可以喝酒。
有一次他在小房子醉了。我们不放心他,要求送他回去。走在夜里的玉林,他仍高高兴兴。我们前面有一位驼子,正在打电话。那人黑衣,金链,一副黑道打扮。这种打扮的人,平时我们看见就绕行,两不相干嘛。但阿多醉了特别开心,他看不见那人的打扮,只看见了那人突出的驼背。他举起手来,大步向前,笑呵呵地想去摸人家的驼背。
在关键的时候,我们拖住了他。他仍笑呵呵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管着他过红绿灯,走人行道。到了他小区门口,他谢过我们,说,我到了,没事了,你们也早点回去吧。
“真没事?”“没事的。”
我们觉得他已经清醒,才放心回去。结果,第二天才知道,他在小区门口的花台上睡了一晚。
但这样的事情很少,他酒量好。我觉得他其实乐趣不在于酒,而在于跟朋友喝酒。
阿多因此成了小房子任何时段都可能出现的人。他打破了因为时间段形成的圈子划分。他好酒更好朋友的性格,让他成了小房子的灵魂人物。
他认识每一个小房子的常客,不止认识,还跟他们都做了朋友。
所以,地震来了,除了父母,他第二关心的,就是小房子的朋友们。
那一晚,弄不清地震情况,不敢回家,我们都住在了小房子。
小房子成了临时避震所。
小房子在之后连续好多天,也都承担着这个功能。就如小房子之前,也承担好多功能。
平时,外地朋友来了,我们往这儿带。自己闲下来,也随便就走到这里。不用相约,这里自会有朋友可以喝茶聊天。微型文化活动也在这里做,比如朋友间的签书会,读诗会。很不正式,但却放松自由。
那时的小房子,是成都民间生成的文化地标,在那里,随时可以看见成都文化圈的缩影。
但后来就没有了。我记得是2012年,小房子转出去了,杜姐不做了。没有杜姐的小房子当然不再是小房子。那个围绕小房子形成的风景,一天就消散了。这些年,城市变得更大,阿多、小竹,也都搬远了,再不是邻居,相聚很少。
(本文原标题:《2008,大地震、小房子和煎蛋面》)
·END·
大家
∣
思想流经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见 · 价值 · 美感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