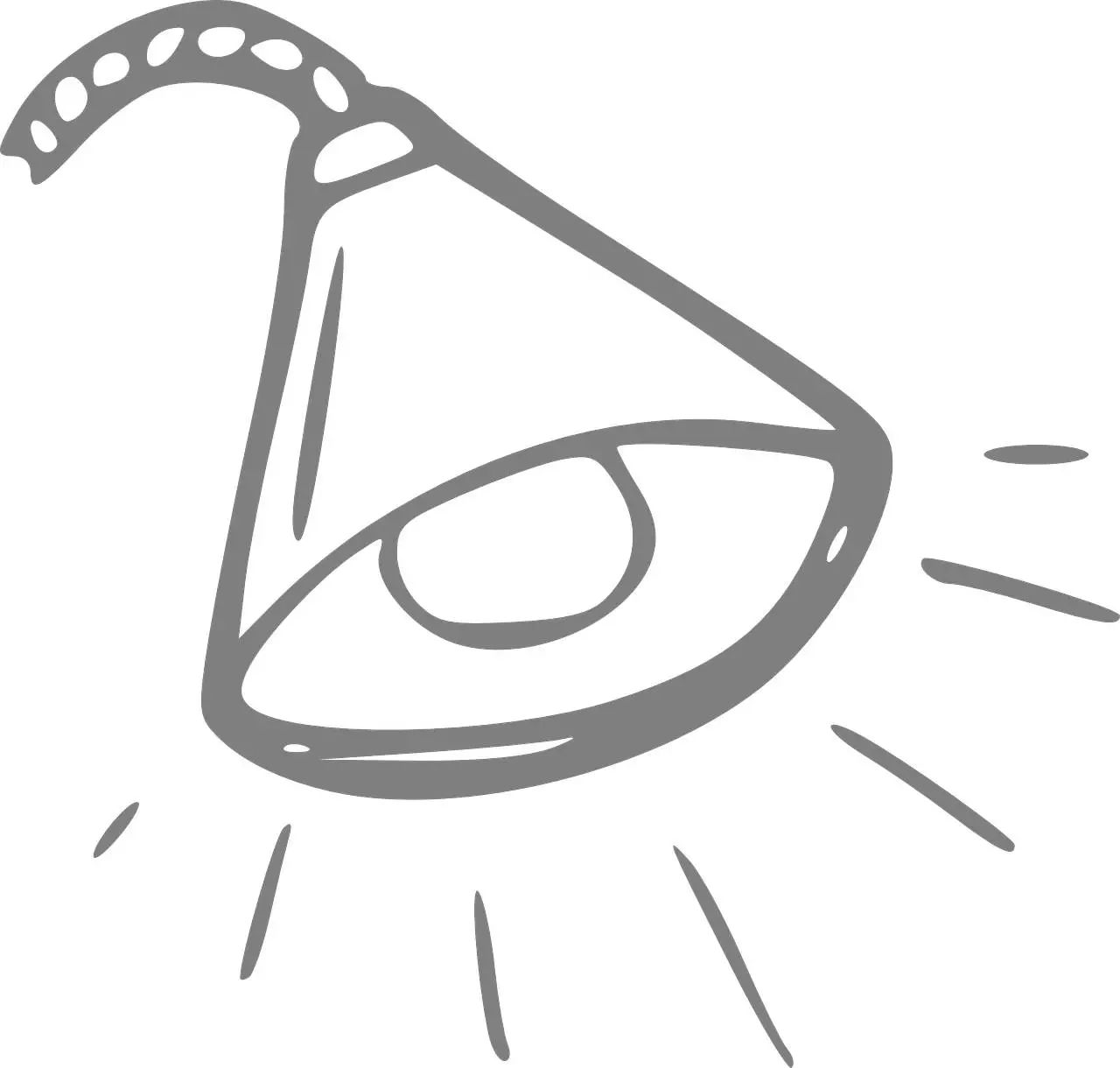专题导言
人类学发源于西方对“他者”以及作为自身镜像的“野蛮”“原始”的猎奇,后来在民族志方法的滋养下成为一门以实地田野调查为核心的成熟学科。伴随着诸文明体系下人们生活的日渐趋同,人类学再也不可忽视对影响全体人类生活的经济的关注。经济在人们的生活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经济学的价格机制原则适用于“未开化”的社会吗?何为“石器时代经济学”?人们在交换礼物的过程中,是否仅是出于理性的计算?财富集体所有,群体共享的团结经济到底能否实现?
“形式论-实质论之辩”作为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学术论辩,给经济人类学分支留下了分裂的共识以及多元化的学科探索路径。经济人类学是否盛筵已过(party is over) ?可以这么说。但是,经济人类学留下了许多在社会-经济总体视角下看待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视角,使得这一领域依然充满生机,从老树不断抽出新枝。
本期“经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将沿着韩可思(Chris Hann)给出的经济人类学系列关键词,以问题意识为导引,梳理经济人类学发展历史中的重要文献。从第一篇到第七篇文章构成对经济人类学基本问题意识的“他山之石”导引。从第八篇到第十九篇,分别围绕生计模式、工作、消费、礼物、贸易与市场、货币与以物易物贸易、信用与债务、产权、全球化、社会主义、道义经济和家户等主题选择介绍中国学者富有文化自觉并且以中国经验为研究对象的探索。选文标准:基于较为扎实经验材料形成的讨论,以田野调查作为方法,研究对象聚焦中国社会。
本专题最后一篇以费孝通先生对“人民的人类学”的思考作结,这也是走出“实质-形式”之争的经济人类学需要回应当下涌现的经济新现象时需要思考的关于“人类学何为”的文化自觉。
鸣谢
专题策划人:胡煌
韩可思(Chris Hann),人类学家,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其研究领域为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的经济组织、产权关系、公民生活等。
摘要
近一个世纪以来,经济人类学在社会文化人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口形成了一个相当连贯的领域。许多人类学家对经济学家的概念存疑,一些人类学家甚至对“经济”这个概念本身也表示怀疑。追求物质的生计总是嵌入(embedded)非物质价值和实践的更广泛背景中,不能被简化为功利主义的计算。然而,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坚持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公理是普遍适用的。本文首先回顾了该子学科有争议的历史。然后列出从业者将其知识系统化的一些主要类别。最后部分涉及经济发展议题,并建议在该领域工作的应用人类学家可以从经济人类学的经典资源中汲取理论灵感,尤其是卡尔·波兰尼。
历史与理论
“经济”一词源自希腊语
oikos
,表示以房屋为基础的家园。亚里士多德将这样一个有序的、自给自足的oikos视为与市场商业构成一组比较。鉴于这样的词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经济学已经将经济与市场商业的主导地位联系在一起。
如果经济人类学等同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关于人类生计的跨文化哲学,那么亚里士多德就应该被公认为奠基人。
这种分化的根源通常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准确地说是18世纪初。科学考察者、传教士以及其他冒险家在欧亚大陆以及海外帝国中记录的“他者”经济形式,最初构成启蒙运动关于进化分阶段理论的基础。这种情况一直在整个19世纪持续,到19世纪末,人们开始系统性关注劳动和物质文化。然而,在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和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这一代学者将长期田野调查研究方法设定成人类学的新标准之前,经济并没有被视为人类学理论化的主要对象,也没有经济学家参与其中。
这一局面发生改变首先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研究开始的,其第一个结果是以对普遍的“经济人”概念的直接攻击的形式呈现的。1921年,第一篇文章发表在《经济杂志》(
Economic Journal
)上。一年后,在一本专门讨论被称为库拉的礼物交换系统的书中,这一论点得到了更多民族志的支持。这部作品成为该学科最著名的专著之一(Malinowski,1922),但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对特罗布里恩园艺实践的类似的详尽的田野调查没有获得同样的认可(Malinowski,1935)。库拉的研究与博厄斯在他称之为夸扣特尔人关于夸富宴(potlatch)的田野工作一起,影响了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925/2016)对礼物交换历史的博学但特殊的调查。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他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继任者)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发表了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洋洲其他“部落”经济体的更严谨的研究。弗斯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由于他接受了行为经济学的普遍公理假设,因此他没有听从老师的号召,去发展一种秀异的“部落经济学”。虽然接受经济学家对其研究主题的锚定,即分析稀缺资源如何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进行分配,但弗斯丰富的描述表明,技术简单、非货币化的经济体与主流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体大不相同。
“经济人类学”一词于1920年代首次使用。在1940年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将其用作纲要的标题之后,它取代了早期的术语,例如“原始经济学”。赫斯科维茨著作的第二版与原版的重点截然不同,这引起了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尖锐批评。在随后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辩论中,理论上的争论达到了顶峰,回顾人类学历史这可以看作是该领域的黄金时代。虽然像弗斯这样的“形式主义者”坚持认为经济学的公理适用于任何地方,因为所有的决策都是关于分配稀缺资源的理性选择,但他们的反对者坚持认为不同类型的社会表现出独特的经济整合形式。“实质主义”学派的领袖是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区分了“经济”一词的两种含义。对他来说,虽然经济学的手段-目的关系最大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但
“经济”更重要的含义涉及在特定背景下人类需求的满足
。为了理解非工业形态经济的运作,将市场交换的主导地位作为唯一的一体化形式是不正确的,其他形式,如互惠关系、再分配和家计则更为重要。根据波兰尼的说法,
价格形成市场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成为主导
。这在19世纪英国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经济与社会的“脱嵌”(disembedding),这种病态状况只能通过“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来拯救。波兰尼受到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分析的影响,不过他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并且更为强调商品化扩张趋势而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见Polanyi,1968)。
形式主义者和实质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争论。波兰尼和他的一些追随者(特别是George Dalton)似乎愿意承认,实质主义者对现代工业经济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由于市场交换是整合的主要形式,这些经济可以留给经济学家(研究)。然而,
如今,经济人类学家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工厂和华尔街银行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与在部落或农民社区开展研究的可能性一样大
。该前提是所有经济活动,即使是完全依赖新兴数字技术的经济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相反地,人们普遍认为,至少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技术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对工业化之前的社会,甚至可以溯洄到对货币出现之前的社会的研究。
此后出现了几种超越形式主义-实质主义辩论的路径。一些人从欧洲现代经济学的前辈那里寻求灵感,从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在美国,一些人类学家更愿意让他们的“文化物质主义”不受马克思主义的沾染,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方法也蓬勃发展,从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对现代世界兴起的权力和经济的权力史研究,再到到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剥夺积累”和金融化风险的分析。与此同时,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等法国学者试图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方法与波兰尼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相结合。他们发明了诸如“世系生产方式”(“lineage mode of production” )这类概念,并展示了这种传统的地方性形式如何与全新的、占主导地位的商业模式“衔接”。对于批评者来说,所有试图概括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发明的概念,如异化、剥削、劳动价值理论和阶级,都因其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ity)而存在缺陷。整个范式被认为过于决定论;例如,尽管“奴隶制”很可能(作为认识论)很好用,但将奴隶制视为人类进化的一般模型的一个阶段是错误的(本体论)。西方人类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试图避免这种陷阱,以形成对苏联民族学所追求的正统观念的有效反对。
在不放弃深刻的普遍主义假设情况下,一种完全不同但同样复杂的研究经济体系的方法是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这在形式主义者的继承人中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见Ensminger,2002)。这些学者的创新在于强调经济制度的历史形成(或演变),这些制度为个体主体的决策及其“路径依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框架。然而,对于他们的批评者来说,尽管新制度主义学者可能已经认识到表面的多样性,并考虑到了其他经济学家所忽视的许多特征,但他们的工作仍然受到一种还原主义倾向的困扰,即参照经济节约原则(economizing principals)来解释社会文化差异(波兰尼称之为“经济学谬误”)。
与这些所谓的决定论方法相反的是采取更强调文化主义的立场,优先考虑当地的经济生活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经济思想史可以从其隐喻的角度来探索,这些隐喻在启蒙时代仍然以农业为主,正如重农主义者学派所体现的那样。十九世纪末出现的新古典主义综合只是另一种民间版本。当这种观点被推向极端时,分析家不得不优先考虑局部宇宙观(local cosmology)。例如,他们必须报告说,远非压迫性权力的人类群体也存在榨取剩余价值的财产所有者,或强调理性个体的效用最大化,许多部落经济的关键参与者是上帝或神灵,神圣通过使土地肥沃来奖励凡俗所做出的献祭(sacrifice)。如果根据群体的社会再生产来定义经济,那么可以说,宇宙观和亲属关系的重要性不亚于,为维持生计或在市场上出售而进行的消费和物质生产。
21世纪没有产生认识论上的共识。经济人类学中的实质主义者倾向于绕开形式主义者开展交流:有些人更喜欢与哲学或文化研究对话,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考古学、农业经济学或发展研究。形式主义者的继任者可能会与经济学学者保持对话,特别是在发展研究领域(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因为他们共享方法论技术(建模和定量分析)以及理论原则(Gregory and Altman,1989)。对于这个阵营来说,价值是通过价格机制确定的,主要目的是更有效地将社区与市场联系起来,而政治行为者的任务仅限于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相比之下,实质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则强调每个人类经济的整体嵌入(holistic embedding)。他们运用道德经济学等概念来质疑统计概括,并在对地方性信仰体系和社会关系的深描中建立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其中一些人对更抽象的模型都情有独钟)一致认为,“价值问题”不是通过价格机制解决的,而应将权力关系置于经济分析的中心。
经济人类学的核心主题
生计模式(Modes of Livelihood)
一种在经济人类学中组织知识的方法,可以追溯到进化论方法在该学科的环境(生态)子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并最强烈地持续存在的时代,是根据其成员获得生计的主要手段对社会进行分类,无论直接为了生存还是通过处置剩余来在现金经济中赚钱,或两者的某种组合。这本百科全书包含有关狩猎采集者、牧民、园艺家、农民、渔业、采矿业、非正规部门和产业工人的条目。这些类别显示出相当连贯的子领域,人类学家发现在这些子领域中,区分经济行为模式并探索与人类社会生活、技术和生态环境的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是有帮助的。可以说,鉴于服务业和金融业在当代世界劳动分工中的重要性,现在应该将服务业和金融业列入这一名单。子领域和主题之间已经发展出选择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ies)。例如,虽然劳动分工可以在任何经济构型中探索,但对共享和共产形式的研究与那些不大量从事投资或储存的狩猎采集者密切相关。虽然人类学家对各地的社会变革保持警惕,但在对农民、农民工和非正式部门的研究中,经济转型的主题尤为突出。
工作(Work)
构建经济人类学领域的另一种方法是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基本的分类范畴,如生产、消费、分配、市场、信贷、投资等。当然,这些是西方范式的术语,在非西方语境中应用它们时必须注意调整它们(Sillitoe,2010)。但是,只要一个人仍然意识到它们的起源,以这种方式进行就不算有害。大多数人类群体都有一些术语,我们可以将其翻译为“工作”,在目标导向的意义上,它与近似于游戏或休闲的东西不同。正如女权主义人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家庭内部的工作往往不被承认,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工作和其他活动之间的界限可能变得模糊。例如,万物有灵论的园艺学家可能无法区分为改变自然环境而花费的能量和在仪式中为确保必要的宇宙环境而花费的能量。即使在理论上有所区别,但在实践中,经济和仪式在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彻底纠缠在一起。大多数国家都有促进合作的结构化机构,从将布须曼人个人联系起来的
哈若(hxaro)关系
,到农民社会中更复杂的互助形式,在这种社会中,劳动行为与社会化和共处性密不可分。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其中工作、仪式和消费密不可分,将反映作家的理论取向。形式主义者和新制度主义者将强调合作在增加回报或减少努力方面的合理性,而实质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通过强调嵌入性和地方性来解释为什么分享和互惠是主导价值观。
图为《抵抗的魂灵与资本主义规训:马来西亚的工厂女工》(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书籍封面,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经济史学家卡尔·布歇尔(Karl Bücher)的研究强调了歌唱和“节奏”在完成物质任务中的重要性,这对年轻的马林诺夫斯基产生了重大影响。工作仍然是德语世界人类学研究的中心焦点(Spittler,2008)。格尔德·斯皮特勒(Gerd Spittler)开创了一种“互动”方法,从整体来看它的思想来源不拘一格,他关于工作的研究与强调生产方式首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具有选择亲和性。人类学家研究了从部落成员和农民到后福特主义工厂和二十一世纪初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不稳定”(precariat)现象,展示出在不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通过劳动过程榨取剩余价值过程。
消费(Consumption)
在经济人类学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消费的研究都被忽视了。消费这一议题在二十世纪后期开始显现出来,彼时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的辩论已经逐渐消失,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其所谓的经济决定论而被拒绝。如果消费被广泛地等同于社会再生产,那么可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亲属关系分类术语映射社会世界的方式可以被等同视作价格体系整合货币化经济的方式(Gregory,2015)。人类学家对消费模式的历史变迁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强调了青铜时代差异化高级美食的出现,以及糖消费在将大西洋两岸的新种植园生产形式和工厂工作联系起来方面的关键作用。虽然等级关系在这些历史著作中至关重要,但某些现代技术可能对其用户具有平等主义的潜力,人类学家在互联网研究中探索了这种可能性。人类学家一直关注美学和物质文化,关注从族群到青年亚文化群体中消费在表达集体身份方面的作用。通过探讨在现代商品经济中物品如何被占有以及“物的社会生命”在通过不同的“价值体系”(regimes of value)(Appadurai,1986)的研究,认识到大众消费如何受到营销、广告和品牌的影响只是研究的起步阶段。关注全球化的理论家们把重点放在消费实践上,往往是为了说明显然是普遍的产品是如何以独特的地方性方式被修改(modified)和挪用(appropriated)的。并非任何地方的人在啖食麦当劳巨无霸汉堡时有一致体验;人类学家已经表明,在世界区域之间以及各区域内部,“挪用”因当地情况而有很大差异。
礼物(The Gift)
除了生产和消费之外,还有广阔的经济生活领域,被贴上“交换”、“流通”、“分配”甚至“实现”的标签。从1920年代开始,自给自足的范式(亚里士多德最初的oikos的基础)让位于交换问题。在经济人类学中,任何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都无法避开1925年首次以法语出版并于2016年第三次翻译成英语的著作
Essai dur le don
(最新版翻译为《礼物:古代社会中的交换形式与理由》)(Mauss,1925/2016)。这本书是早期“摇椅上的椅人类学”的一个例子,跟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学生所从事的实地研究有所不同。莫斯不仅要展示他的博学,还要阐明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政治观点。他讲述了人类如何从总体性转向更个体化的呈现形式(礼物),然后再到现代市场和契约世界的故事,这是他的叔叔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eim)对劳动分工演变的早期叙述的阐述。莫斯借鉴了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以及布歇尔等其他摇椅上的学者)来证明,人类本性不仅仅是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即功利主义计算的“市场伦理”。“礼物的精神”(其典范是波利尼西亚人的
hau
概念)意味着它不能与捐赠者分开。它暗示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和事物并不像现代西方通常认为的那样整齐地分开。虽然一些人认为莫斯所暗示的利他主义捐赠的可能性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在Marshall Sahlins [1974]称之为“广义互惠”中),但他更好是被理解为无私和慈善捐赠等概念应该参考其历史背景来理解。莫斯渴望重新出现基于自下而上的团结的替代经济形式,例如合作社(cooperatives)。他很清楚,“慈善创伤”,个人必须工作,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模式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一样片面。然而,他未能证明重新发现贵族的奉献伦理,正如古式夸基特尔夸富宴或欧洲封建贵族热情好客的仪式和慈善事业所证明的那样,如何能够解决工业社会秩序中的团结(cohesion)和包容(inclusion)问题。
贸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s)
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波兰尼为首的实质主义者向形式主义者发起挑战,贸易和市场构成主要基础。他们认为,正如亚当·斯密所理论的那样,以利润为动机的商业并不是历史上贸易发展的主要方式。通过政治、外交和行政控制进行管制的长途贸易往往比通过市场进行的地方或区域交换更重要。尽管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有很多市场活动,但这些市场并不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的自发价格所形成的市场。波兰尼的一些学生通过民族志研究支持这种方法,例如,证明非洲殖民地的市场具有广泛的功能,超出了狭义的经济功能。价格通常是通过复杂的特定文化协商所确定,而这种交换只是一种“整合形式”。波兰尼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嵌入式经济中,更重要的形式是
互惠
(理查德·图恩瓦尔德和马林诺夫斯基首先使用的概念,并以分为两个部分或部分的平等主义社会为例)和再分配(如夸基特尔和其他部落社会所呈现的那样,酋长的工作是重新
分配
他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贡品或凭借他的职位所控制的货物)。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对贸易和市场的兴趣并没有减弱。与一些早期的实质主义者不同,尽管技术变革改变了国内和国际交易,但经济人类学家发现,研究复杂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塑造每一种交换行为的社会关系是有益的。在宏观层面上,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从20世纪最后25年开始)市场化的加剧,导致一些人认为,波兰尼的批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攸关。与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反,假设放松管制和私有化之后是国家的退出,这是一个危险的乌托邦神话。对于21世纪的全球经济和19世纪的英国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一样,现实情况是,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只有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才能实现。
金钱与易货贸易(Money and Barter)
从一开始,经济人类学家的另一个关键话题就是金钱。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主张将库拉(Kula)(特罗布里恩岛民的贵重物品)包括在内,即使它们不符合现代西方标准,即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交换媒介。波兰尼甚至更明确地挑战了经济学家的假设,即货币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易货贸易交换的低效率问题。与贸易一样,易货贸易需要被看作不仅仅是所需商品的经济交换;它通常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外交语境。民族志记录中充斥着货币用于衡量和储存价值而不是作为交换媒介的案例。实质主义者发展了“有限用途货币”的概念,与经济学家的“通用货币”相对立。即使是现代形式也被浸泡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它不一定像实质主义者所假设的那样侵蚀经济领域之间的界限。基斯·哈特(Keith Hart)(2000)和David Graeber(2011)等人最近的研究继续抨击经济学家的简化故事。两位作者都强调了政治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前者强调暴力在货币出现中的重要性,而后者则认为数字技术可以发挥解放性的功能。
信用与债务(Credit and Debt)
债务是经济人类学中另一个发展良好的主题,特别是在农民和非工业贸易和市场体系的背景下,在这些体系中,信任关系始终是核心。债务可能与生产性投资有关,但也与诸如奴役、对奴隶的剥削有关。随着二十一世纪初的全球危机,信贷和债务议题在人类学中变得更加地位显著。随着以衍生品交易为例的“元金融流通”(Gudeman,2016:19),金融领域已经失去了与生产和消费有用商品的“实体经济”的最后联系。人类学家在许多层面上探索了金融化,从华尔街的中央机构到旨在减轻全球南方贫困的小额信贷计划。鉴于负债对许多贫穷借款人的负面影响,早期对小额供资的热情已经减弱。然而,在某些条件下,促进“普惠金融”的政策可以产生有益的后果。政治经济学方法通过关注国际资本的战略和精英机构在多个层面上创造和管理债务过程,从个人到家庭再到主权国家,探索了债务在“普通公民”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
财产(Property)
财产权对经济组织至关重要,因此对财产权的研究对经济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十九世纪,财产权从公有机构向个人的转变是最有影响力的进化论理论的基石。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推翻了这些理论的简化版本,他们展示了个人和集体权利如何在包括现代西方在内的广泛社会中并存。这些见解是在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大量文献以及对游牧民族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只有在生产和消费中强调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社会才能有效运作。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集体化和中央计划的实验通常被认为由于这个原因而失败。然而,许多小规模社会已经发展出可行的公共财产监管机构(不要与开放获取相混淆),其效果与公地私有化一样好,甚至更好。虽然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无疑是功能失调的,并且只能通过计划之外的巧妙的非正式(或非法)实践才能幸存下来,但人类学家已经证明,在某些条件下,社会主义特有的“模糊”(fuzzy)财产关系可能比苏联解体后强加的私有化更有利于高效生产和社会福利。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人类学家已经将他们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包括知识产权,从高科技专利到品牌名称到传统的土著知识。他们关注各种新的“事物”,这些“事物”由于新的生物技术(例如身体部位)而成为可交易的财产对象。最后,人类学家一直对财产的继承机制感兴趣,从农村(农民)社会的继承策略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家族企业王朝。尽管优绩主义伦理很时兴,但在当代全球经济中,社会不平等仍然与财富的继承密切相关。
全球化(Globalization)
马林诺夫斯基(1935)在他最后一本关于工作和财产问题的专著的结尾处,对他没有充分关注特罗布里恩岛民所处的更广泛背景感到遗憾,他们长期接触白人商人以及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经济人类学家更加努力地将他们的民族志研究置于全球动态体系中,特别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剥削性帝国主义动态系统之中。作为对宏观层面研究的补充,对消费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全球产品和“现代性”本身如何被地方挪用的关注。
这些本地化进程越来越受到跨国公司精英们的主张推动。
广告和品牌推广对成功营销至关重要。旅游市场和遗产产业的惊人扩张就是这些发展的例证,这些发展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日益关注。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层面也是许多商学院研究人员感兴趣的。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和新兴的商业人类学之间有重叠的地方(见同名期刊)。
社会主义(Socialism)
没有人怀疑资本主义是冷战的赢家(即西方和苏联之间的竞争,以后者在1990 年代初的解体而告终)。在这次解体之前的几十年里,许多经济人类学家在可能接触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探索了它们独特的经济组织。东欧的大多数田野工作都集中在农村,关注集体农庄。研究表明,对中央计划指令的更成功的适应(例如1968年后在匈牙利发展起来的体系),恰恰是那些将社会所有制原则与物质激励和市场信号相结合的体系。对工厂的研究表明,异化和剥削问题可能与资本主义工厂(例如,使用计件工资制度)中发现的问题没有太大区别。然而,人类学家发展出的唯一普遍性社会主义模式是基于罗马尼亚的情况,罗马尼亚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下的一种异常压制的变体(Verdery,1996)。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考古癖。在“后社会主义”的混乱中,人们很快发现,即使消费者的选择和财产权在1990年后名义上得到了加强,但对于转型过程中的许多“失败者”来说,这在实践中并没有多少安慰。人类学家发现,前苏联的许多公民现在对失去他们以前所拥有的那种庇护而感到遗憾。在社会科学研究者调查的几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古巴和越南)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和地方实践中,这一点也很突出,这些国家自己声称在不断更新他们的社会主义,而没有谨慎地放弃它。更大的议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世界中,是否仍然有可能按照新自由主义市场资本主义以外的原则来组织经济。
图为《苏维埃生活的毁灭:后社会主义的日常经济》(
The Unmaking of Soviet Life: Everyday Economies after Socialism
)书籍封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本书是“后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社会丛书”(Culture and Society after Socialism)的第一本,共汇集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学者、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 (Caroline Humphrey)十篇代表性论文,涵盖易货贸易、消费文化诸议题。
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
道德经济是经济人类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感兴趣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和政治学家兼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之后。主流经济学家在考虑福利问题时倾向于将重点放在
帕累托最优
(在不降低他人效用的情况下不会偏离的条件)原则。但这种初始分配与规范正义(normative justice)无关。批评家倾向于借鉴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特别是那些源自马克思的传统,尽管马克思本人渴望的是对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有建设性的、科学的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那些援引道德经济学的人通常关注有关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特别是从属阶级将这些规范作为一种抗争和抵抗形式来维护的能力。有一种倾向(与一些早期的实质主义者,也可以说就是波兰尼本人的倾向相呼应)将前工业时代的整合社区浪漫化,而忽视其成员在多大程度上从事商业活动或以其他方式效用最大化。道德矛盾是非正式部门中许多活动的特征:例如,苏联的布拉特(blat)是一种“人情经济”,并不总是很容易能区分出其中对关系的工具性操纵和真诚的友谊。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决策的道德背景,而另一些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个人决策的道德(或伦理)维度(Brown and Milgram ,2009)。虽然该领域的许多研究都与社会学研究有关,但与经济心理学也存在持久的联系。一些经济人类学家对情感在激励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感兴趣,包括嫉妒和贪婪等“负面”情感提供的驱动力,这些情感(经常被断言)可能成为创新和发展的障碍。
家户(Households)
在波兰尼的经济人类学的早期版本中,他将“家庭”作为第四种整合形式(除了互惠、再分配和交换)。尽管这最终被放弃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归入再分配的范畴),但从早期开始,对这一层次经济生活鲜明特征的研究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的主要关注之一。在俄国农业经济学家A.V.恰亚诺夫的启发下,人类学家意识到,主要以满足其成员的生存需求为导向的农民经济的生产动力与寻求市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同。根据恰亚诺夫的说法,革命前俄罗斯农民家庭的关键解释变量是每个家庭中工作者与消费者的比例波动。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974,41-148)扩展了这一原则,提出一种“家户生产模式”,并将其应用于广泛的部落社会。后来的研究表明,人口不平衡可以通过家庭外部机制来平衡和补偿,大多数部落和农民社会表现出结构性的不平等,特别是在财产分配方面。文化取向的经济人类学家表明了,强调节俭和自给自足愿望的经济“家户模式”的重要性,即使这与农民融入更广泛的市场和国家权力体系的现实越来越矛盾。通过观察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并不总是与亲属关系完全一致),人类学家打开了主流经济学家倾向视作黑匣子的东西。人类学家阐明了包括“自我剥削”倾向在内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在手工业环境中,而且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都可以给家族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女权主义者一直强调父权制对家庭的统治,不仅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还有老年男性对晚辈的统治。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对家庭的关注仍然像以往一样重要,在后社会主义社会中尤为重要。裁员时,妇女往往是最先失业的,而女性的韧性(resilience)体现在,女性加强家务劳动来取代以前在市场上购买或由国家提供的服务。
经济人类学的应用与“发展”
(Applied Economic 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