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
翻译:李晓红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ohistory
一百多年前,也是一个春日的夜晚,香榭丽舍剧院里灯火通明,男士衣冠楚楚,女士们身着优雅,在略显闷热的大厅里摇着扇子,小声交谈。所有人都很兴奋。人们一连几个星期都在谈论俄罗斯芭蕾舞公司为巴黎的新演出季准备的艺术享受——舞剧《春之祭》。演出阵容自然十分强大:由佳吉列夫导演、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神的孩子”尼金斯基担任舞者。
舞剧开演了。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那是俄罗斯远古时期的祭祖仪式,一个肃穆的异教祭典——一群长老围成一圈坐着,看见一位少女被要求跳舞直至跳死。她是他们用以祭祀春天之神的祭品。
但这部芭蕾舞剧却惹怒了当时近乎半数的欧洲知识分子,甚至还没看完便生气地离场,而另外一半人则拍案叫好。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中剧烈下挫的不和谐音、尼金斯基充满挑衅甚至色情意味的怪异舞步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芭蕾的想象。对于佳吉列夫而言,艺术不是要教化或是模仿现实,它首先要激发震撼与惊异。
百年之后,当人们回顾那个喧嚣的夜晚,完全可以将它视作时代的象征,看成世纪的分水岭。通过这样的轰动性事件,艺术和历史彻底被改写了,人类进入了新的纪元。
《春之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影响和余波,敏锐地发掘出历史的秘密。从 1913 年斯特拉文斯基和尼金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的首演,一路写到 1945 年希特勒的死亡,作者借助普通人的生活和言论、文学作品以及重大的社会事件,记述了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人们观念的急剧转变,以及对文明历程造成的巨大影响。尾随他的思路,我们得以在 20 世纪初法国巴黎的沙龙里逡巡,在西线战场上痛哭流涕。在午夜穿越回二十世纪初的巴黎,你会偶遇毕加索、阿波利奈尔、郁特里罗、莫迪里阿尼、马蒂斯......以及他们的自由与疯狂。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文化和叛逆
如果说在1914年之前,欧洲先锋派自我形象的核心是处于交战状态的精神的思想,那么德国作为一个国家最能代表那种思想;而如果说正在兴起的现代审美意识的核心是对于被视为19世纪主流的那些标准的质疑,德国又最能代表那种叛逆。
德国的政治体制是把君主制和民主制以及中央集权和联邦制综合起来的一次尝试。它的大学因为所做的研究而受人仰慕。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整个国际劳工运动都唯其马首是瞻。它的青年运动、妇女权利运动甚至同性恋解放运动都搞得轰轰烈烈。这些运动大量涌现的背景是生活改革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出现的广泛的社会改革运动,提倡回归自然、健康饮食、戒绝烟酒毒品等。该运动对于其他国家的类似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译者注]
。而生活改革运动,顾名思义,就是要重新确定生活的方向。这不但是说基本的生活习惯,还包括生活中基本的价值观。据1907年的统计数据,从事有报酬劳动的德国妇女达30.6%。如此高的比例,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无出其右。柏林、慕尼黑和德累斯顿都是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心。毕加索在1897年就说过,如果他有儿子,而这个儿子又希望成为艺术家,那他就会把他送到慕尼黑而不是巴黎去学习。罗杰·弗赖伊(Roger Fry)在其1912年第二次后印象主义画展的目录导言中,显然是把后印象主义与绘画中普遍的实验方法等同起来。他写道:“后印象主义画派盛行于——有人几乎会说蔓延于——瑞士和奥匈帝国,特别是德国。” 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易卜生和蒙克(Edvard Munch)在德国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更受欢迎。在装饰艺术和建筑领域,相比于法国和英国,德国对实验方法更为开放,更乐于接受工业,并以之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审美意识。例如,在英国文化界的当权者一边倒地批评水晶宫的时候,洛塔尔·布赫尔(Lothar Bucher)在1851年报道说,德国民众为之心驰神往:“它给看到过它的人留下的印象是又美又浪漫,以至于在德国偏僻村舍的墙上都挂着它的复制品。”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批评者在批评香榭丽舍剧院时,是如何把它和德国的实验方法以及非历史的态度(ahistoricity)联系起来的。德国的建筑师、手工艺者以及作家们推动的运动,“事实证明非常有力,”有批评者认为,“以致在思想和建筑领域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风格,而不仅是少数个人的某些革命性言论和行为。”。在现代舞方面,伊莎朵拉·邓肯和埃米尔·雅克-达尔克罗兹正是在德国创建了他们的首个学校。佳吉列夫在自己的西方巡演中偏重于巴黎,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巴黎毕竟是他想要征服的西方文化的心脏,而他在德国的几个演出季,虽然受欢迎的程度一样,可人们更乐于接受。《牧神》于1912年12月12日在柏林开幕演出之后,他打电报给阿斯特吕克:昨天在新皇家歌剧院的开幕演出大获成功。观众要《牧神》再来一个。请求了十次。没有抗议。全柏林都来了。施特劳斯、霍夫曼斯塔尔、赖因哈特、尼基施、整个分离派的人、葡萄牙国王、大使和朝臣。给尼任斯基献了花环和鲜花。媒体反应热烈。霍夫曼斯塔尔在日报上发表长文。皇帝、皇后和皇子们礼拜天时都来看了芭蕾。跟皇帝谈了很长时间。他非常高兴,并对公司表示感谢。巨大的成功。
可见,1914年之前,德国社会的基本风尚在于寻找新的形式——不是从法则和有限性的角度,而是从象征、隐喻和神话角度来说的形式。1899~1900年,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在巴黎学习美术。他经常去卢浮宫临摹。一天,就在他快要临摹好提香的《德阿瓦洛斯肖像》(Allegory of Davalos)的时候,身后一个陌生人评论说:“你不是拉丁人。从你画的人物的性格的强度就可以看出来。”Emil Nolde, Das eigene Leben (Flensburg, 1949), 238不管诺尔德在其回忆录中所讲的这个故事是否属实,它都充分反映了德国人在世纪之初的自我理解:在他看来,德国人远比他们的邻居们更具精神性。“德国人的创造力从根本上来说不同于拉丁人的创造力,”艺术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写道,拉丁人是按照对象在自然中存在的那样来获取其形式的。德国人是在幻想中根据自己特有的内在洞察力来创造其形式。看得见的自然的种种形式,只是作为象征为德国人所用……德国人不是在外表中,而是在更远处的某种东西里寻找美。
德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广泛地代表着民族的先锋渴望——渴望摆脱英法影响力的“包围圈”,摆脱由大英治下的和平以及法国人的文明所强加的世界秩序,即在政治上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被法典化的秩序。
虽然德国某些方面的人士认为德意志文化正在遭受浅薄、任性和追逐短期效应的侵害,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去加以巩固,就像朗本和张伯伦等人建议的那样,虽然在所有的等级中都存在相当程度的焦虑,一种理所当然会令各级政府和领导人感到担忧的情绪,但强烈的自信、乐观和使命意识,即对德国人历史使命的信念,仍然是存在的。认为改革的浪潮是比它任何具体的、在某些情况下不可接受的部分更大也更有意义的东西,认为改革的浪潮构成了民族的心脏和灵魂,这样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当诗人斯特凡·乔治的两个门徒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和弗里德里希·沃尔特斯(Friedrich Wolters)在1912年坚持认为同性恋中并不存在任何不道德的或反常的东西时,他们就表达了上述的观点。“相反,我们一向认为,在这些关系中可以发现某种本质上有助于整个德意志文化发展的东西。”这种观点属于一种信奉“英雄化的爱”的文化。
一战前夕,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规模实际上是最大的。早在1898年,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就认为有必要在帝国国会就该问题发表演讲。德皇侍从中的同性恋甚至在1906年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决心曝光此事之前就已经众所周知。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在德国领导了修订民法典第175节内容的运动,而截至1914年,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名的有3万名医生、750名大学教授以及另外的数千人。到1914年,柏林约有40个同性恋酒吧以及(据警方估计)一两千名男妓。这并不是说德国人全都欢迎或准备公开宽容同性恋——他们没有——而是说该运动在德国的相对开放性的确标志着一定程度的宽容,并且这种宽容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另外,同性恋以及对它的宽容,就像很多人提出的那样,对于曾经被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的瓦解,对于本能的解放,对于“公共人”的衰落,实际上也对于整个现代的审美意识,都具有核心意义。
在世纪末的德国,性解放并不只限于同性恋者。总的来说,当时又开始强调身体文化,强调不顾社会禁忌和约束的对于人体的欣赏,强调要把身体从紧身内衣、腰带和乳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世纪更替之后活跃起来的青年运动,醉心于“回归自然”,沉湎于未必放纵但肯定更加自由的性行为,这成了它对被认为是压抑和虚伪的老一代人的反抗的一部分。19世纪90年代,自由的身体文化——裸体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成了健康热的一部分,该运动提倡长寿饮食、自种蔬菜和自然疗法。在艺术领域,对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反抗更为激烈:从弗兰克·韦德金德描写露露的两部剧作开始
[即1895年的《地精》(Earth Spirit)和1904年的《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作者原本是打算将它们作为同一部戏剧的。露露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后沦为妓女。——译者注]
(它们赞美那位妓女,因为她是叛逆者),到施特劳斯的莎乐美
[指理查德·施特劳斯根据王尔德的悲剧《莎乐美》创作的歌剧《莎乐美》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她砍掉了施洗约翰的头,因为他拒绝满足她的情欲),再到托马斯·曼的早期小说中被压抑的但又暗流涌动的性本能,艺术家们利用性来表达他们对于当代的价值观和侧重点的幻灭感,甚至用来表达他们对于一种生机勃勃的和遏制不住的能量的信念。
文学艺术中的性主题涉及一定程度的暴力,这在德国比在别的地方更明显、更持久。这里又一次用对暴力的迷恋来表现对生的兴趣,对毁灭的兴趣——毁灭也被看作一种创造行为——以及对作为人生一部分的疾病的兴趣。在韦德金德那里,露露是被杀的;在施特劳斯那里,莎乐美杀了别人;在曼那里,阿申巴赫死于病态的气氛和未能得到满足的性渴望。德国早期的表现主义在它的主题、形式和色彩中有一种暴力的基调,这种暴力的基调要比在立体主义或未来主义中表现得更为强烈。马里内蒂(Marinetti)的未来主义宣言鼓吹毁掉纪念馆和博物馆,并且烧掉图书馆,而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创办了一份名为《爆炸》(Blast)的杂志来表明自己的意图,但在这些努力中,明显有夸张的表演甚至玩笑的成分。在德国的表现主义者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和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那里,暴力更多是表达了深层的精神上的兴奋,而不是一种肤浅的表现形式。他们的外表有着和小男生差不多的天真和魅力,没有一点儿暴力的痕迹。“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理想必须穿上刚毛衬衣
[用动物的毛织成的贴身内衣,在某些宗教传统中会穿着它来作为赎罪和忏悔的手段。——译者注]
,”马克写道,“如果我们想摆脱我们欧洲人的糟糕的品味所带来的疲惫感,我们就得饲思想及理想以飞蝗和野蜂蜜,而不是历史。”
对原始主义的迷恋,或者换句话说,想要和原始的德意志精神建立联系的渴望,影响了德国的许多阶层,尤其是德国的中产阶级。青年运动就充满了这样的联系。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回归自然,摆脱纯粹形式的和虚假的城市文明。它敬仰“体操之父”雅恩(Turnvater Jahn),他在抗击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在德意志各邦成立了许多体操协会,他自己年轻时也一度住在洞穴中,后来还穿着熊皮行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在世纪更替的政治以及一般的著述中,德国人关于部落起源的记忆也不断被唤醒。在对派去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军队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讲话中,德皇号召要回归匈奴人的精神。1914年7月8日,左翼自由派在柏林的重要喉舌《柏林日报》开始连载卡尔·汉斯·施特罗贝尔(Karl Hans Strobl)的小说,名为《就那样,我们奔赴了赫尔曼战役》(So ziehen wir aus zur Hermannsschlacht)。该报一节一节地刊登这部小说,直到8月战争爆发。小说的名字指的是公元9年那场著名的战役,当时,切鲁西部落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在现今汉诺威北部的森林打败了罗马将军瓦鲁斯(Varus)率领的几个罗马军团。建成于1875年的高大的赫尔曼雕像,现在仍然伫立在条顿堡森林中。除了马尔克和马克,还有许多艺术家通过缅怀原始时代的人而找到了灵感。1914年年初,在一次南太平洋旅行期间,埃米尔·诺尔德说:原始时代的人生活在自然中,与之融为一体,并成为整体的一部分。我有时候这样想:他们是仅存的真正的人,而我们却相反,是畸形的木偶,做作而且自高自大。他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那种帝国主义的整个进程感到遗憾:他感到,太多实质性的东西都被毁掉了,取而代之的只是虚饰。
国内外的很多人都被德意志文化中冒出的泡泡迷住了——也有一些人被激怒了。在德国中产阶层之中,并没有多少人欣赏韦德金德的戏剧、马尔克和马克的艺术,或者“身体文化”以及城市青年玄奥的唯心主义。工人阶级,不用说,跟资产阶级的波西米亚人也不太合拍。但有趣的是,这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大部分德国人对于创新、复兴和变化的普遍认同。外国观察家也有类似的反应。出生于西班牙的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写下如下文字时想到的主要就是德国,他写道:各个政党和民族在其中彼此对抗的、为英式自由所不容的精神,并不是慈母般的,也不是兄弟式的,更不是基督徒式的。他们的勇武和美德就在于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想要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那是一种十分原始的渴望。他贬低德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他视之为强调私德且在公共领域中循规蹈矩——这样的态度在他看来正是德国的社会和道德发展落后的原因。不过,冷嘲热讽之余,他也意识到德国事情的关键是活力:“德国人的道德想象……在于对生活的爱而不是智慧。”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对德意志文化颇有好感。到1913年2月,施特劳斯的《厄勒克特拉》他已经听过两遍,对此,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心醉神迷。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对于施特劳斯作品中总是存在的庸俗,就让他们去说吧——对此,我的回答是,一个人越是深入德国的艺术作品中,他就越是明白,他们全都因此而蒙受损失……施特劳斯的《厄勒克特拉》真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斯特拉文斯基所说的“庸俗”大概是指作品中“原始质朴”的方面,同时也是指作品必然给公众带来的挑战。另外,如果说德国的许多现代艺术都关心根本性的东西,那言外之意就是说,包括创造者和消费者在内的整个德意志文化,与实验和新奇还是比较合拍的。要做到“原始质朴”,就要反抗让人感到窒息和无聊的规矩,反抗无意义的惯例,反抗不真诚。所有这些在德国人对于文化的理解中都非常重要。就算单个的德国人对于变化的态度并不总是明确的,这种文化也极大地促进了变化。
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领域比在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目标中更让人印象深刻。在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咄咄逼人的态度中,德国对于盟友、中立者或敌人的焦虑、希望和利益,几乎是一点儿也不理解,尤其是在跨入新世纪之后。结果,英国对于德国人的海上野心的担忧,法国对于德国人的殖民地要求的关切,还有在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从阿尔萨斯到俄罗斯边界的中欧关税同盟的问题上,俄国对于德国人的假设所抱有的戒心,这些在德国几乎得不到同情,无论是在权力走廊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
1896年,德国政府公开采取被称为世界政策的新政策,它和到当时为止一直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完全不同。世界政策并不是德皇周围一小帮智囊靠阴谋诡计强加给德国人的对外政策。它反映的是一种广泛的得到众多知名知识分子和公共团体支持的想法,即德国要么扩张,要么衰落。这种政策上的转变,连同相关的海军建设计划和大肆扩张殖民地的做法,自然要引起外界对于德国人长远意图的担忧。不过在德国国内,外界的质疑却只是被理解为变相的威胁。考虑到德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作为统一民族国家的时间还不长,还有既缺乏安全感又刚愎自用的性格,德国人开始感到担心也不无道理。他们担心,以英国这个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Albion)为首,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当中,目的是包围并制服德国,同时也一并制服创新、精神、刺激和冒险。英国人所标榜的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以及自由主义伦理,完全是世界级虚伪的说辞——在德国,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英国是一个决意维持其国际地位的国家,它决意傲慢地保持对海洋的控制权,决意专横地不让任何其他国家拥有建设海军、推行帝国政策的权利。鉴于英国奉行的对外政策,它有关法治、民主和正义的声明显然是骗人的东西。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德国人往往把自己的国家看作进步的解放力量,它会给世界的权力安排带来新的诚实性。相比之下,从德国人的角度看,英国是极端保守的力量,只想要维持现状。
对于这个迅速崛起而且来势汹汹的德国来说,1888年29岁登上皇位的德皇威廉二世是个合适的代表。关于他,瓦尔特·拉特瑙说:“从来没有哪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人,如此完美地代表了一个时代。”威廉不仅体现了他所统治的那个国家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还在幻想中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
在现实中,他是个温柔得有点娘娘腔的男人,非常容易激动。他最亲密的朋友都是些同性恋者,而他之所以被他们吸引,是因为他在他们那里可以找到在界限分明的官场上和以男性为主的传统家庭生活中找不到的温暖和关爱。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以至高无上的军事领袖的形象示人,应该是男子汉气概、强硬和大家长式刚毅的典范。然而,虽然他对德国政府和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虽然他已是7个孩子的父亲,但他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作为统治者还是作为父亲,似乎都不太满意。内心中孱弱与强力的对峙让他无所适从,于是,他就采取了和该民族集体相同的做法:没完没了地演戏。伯特兰·罗素认为德皇首先是一名演员。说到威廉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的职务,伯恩哈德·冯·比洛侯爵(Prince Bernhard von Bülow)认为,那是威廉自己想要扮演俾斯麦的角色。
喜欢演戏,讲究排场,沉湎于幻想,威廉的这些特点很多人都谈论过。他的注意力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因此,给他的简报必须精练而富有戏剧性。他不安分的天性需要持续不断的游玩和刺激;他是和传统的旅行者相反的现代观光客。他最亲密的朋友菲利普·奥伊伦堡侯爵(Prince Philipp zu Eulenburg),一个很有造诣的诗人、音乐家和作曲家,认为他首先是个艺术家,只是在社会环境和父母的压力下,才不得已过着服务公众的单调生活。威廉喜欢艺术,尤其是盛大的场面。他对于歌剧和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其专业程度每每令内行人士都非常吃惊。虽然他的趣味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但他至少偶尔也会容忍实验,对俄罗斯芭蕾舞团尤为钟爱。
德皇和宫廷对于舞蹈的兴趣有点古怪但又意味深长。军事内阁的首脑迪特里希·冯·许尔森-黑泽勒伯爵(Dietrich Count von Hülsen-Haeseler),穿着芭蕾舞裙,在德皇和召集来的客人们面前——观众往往有男有女,但皇后从不参加——表演令人钦佩的单足旋转和阿拉贝斯克舞姿,这样的场面显然并不少见。有一次,这样的表演成了许尔森最后的演出。1908年,在威廉的另一个密友兼对外政策重要顾问马克斯·埃贡·菲尔斯滕贝格侯爵(Max Egon Fürst zu Fürstenberg)的家中,许尔森在跳舞的时候因为心脏病发作而突然倒地身亡。“
对于这样的娱乐,人们或许会当作孩子气的胡闹,当作应该在营火旁表演的滑稽短剧而一笑了之,但是从德皇的性格及其民族文化推动力中的诸多矛盾来看,许尔森受人称道的表演却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即便是不考虑许尔森事件中的性意味,人们也可以说,威廉虽然在公共领域中把艺术看作培养社会理想,特别是教育较低社会等级的手段,但在他的私生活和个人的感受力中,却倾向于从活力论的角度看待艺术。
不过,威廉感兴趣的并非只有艺术,他对于新技术也表现出难以餍足的好奇心。在1906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宣告“汽车的世纪”即将来临,而且还敏锐地预言说,新的时代是“通讯的时代”他在自己身上和自己的兴趣中看到了德意志灵魂的形象。在德意志的灵魂中,目的和手段、艺术和技术,都融为了一体。艺术史家迈尔-格雷费(Julius Meier Graefe)发现,德皇的身上综合了腓特烈·巴巴罗萨
[即“红胡子”腓特烈一世。——译者注]
和现代美国人的特点。这样的见解正确暗示着,对威廉而言,历史并不完善,它不过是听由巨人般的自我摆弄的玩物。所以毫不奇怪,H. S. 张伯伦关于历史是精神而非客观实在的观点会让威廉感到激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威廉把它建在柏林市中心以纪念自己的祖父——连同穿过动物园把西区和菩提树下大街连接起来的胜利大道,显示出他的历史意识的完全神秘的性质。特奥多尔·冯塔纳的反应和迈尔-格雷费的相似:“皇帝让我喜欢的就是他与旧事物的彻底决裂,而皇帝让我不喜欢的则是他那种矛盾的复古愿望。”
当时在艺术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倾向,把天启和返祖现象作为自己的核心主题——那是原始的东西与超现代的东西的结合,再加上势必造成的对历史的否定。德皇的思想尽管缺乏深度,但努力的方向差不多。现代艺术变成了事件。德皇也喜欢装作他是个事件。
施利芬计划——德国人用来应对两线战争的唯一的军事战略——进一步反映出幻想以及对浮士德时刻的痴迷在德国人的思想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该计划准备经由比利时发动快速进攻,在法国北部向左急转并攻占巴黎,此后就可以集中全部资源对付俄国。该计划期望以法国北部一次重大战役为基础,在欧洲取得全面胜利。这个就像出自瓦格纳手笔的宏大计划,把有限的战术冒险抬高为总体的想象。这是把自己当成银行主管的赌徒的战略。
注定执行施利芬计划的那个人,继施利芬之后担任总参谋长职务的赫尔穆特·冯·毛奇,性格上也存在德皇的那种分裂。毛奇对于艺术的热情要远远超过他对于军事问题的热情。他懂绘画,还会拉大提琴。他私下里曾经承认:“我完全生活在艺术中。”
当时他正在把梅特林克的《普莱雅斯和梅利桑德》(Pelléas et Melisande)译成德文,据说,他总是带着一本歌德的《浮士德》。
战争即文化
1914年8月,大部分德国人都从精神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正在卷入的武装冲突。战争首先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以德国的领土扩张为目的的阴谋。对于那些思考这件事情的人来说,这样的扩张必然是胜利的衍生物,是出于战略的需要,也是德国人自我彰显的伴生物,但战争并不是为了领土。直到9月为止,政府和军方都没有具体的战争目标,有的只是战略与想象——认为德国的扩张是存在意义上的而不是形而下意义上的想象。
认为这将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是为了先发制人,对付德国周围敌对国家的侵略性企图和野心,蒂尔皮茨和毛奇那样的人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可这些辩护性的理由虽然经常被提到,却总是被归于德国人傲慢的大国意识,即他们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这两个方面,实际的方面和唯心的方面,并不像许多历史学家在争论战争的目的时所暗示的那样互不相容;两者都是战争前夕德国人个性中的基本成分。
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和布尔战争中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规模较大的战争必然需要漫长的、旷日持久的和激烈的厮杀,但很少有战略家、战术家或计划的制订者,无论是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对于未来的冲突除了迅速解决之外还想到过别的可能性。在19世纪,尽管军方越来越重视规模和数量,重视作为群众现象的战争,但各个国家对于战争的理解仍然是运动战、英雄主义和速战速决。铁路会把士兵迅速运往前线;机枪会被用于进攻;威力强大的战舰和火炮会干脆利落地击垮敌人。不过,物质虽然重要,战争仍被看作——尤其是在德国——对精神的最大考验,而且,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对生命力、文化和人生的考验。1911年,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在一部两年内就出了六个德文版的书中写道,战争是“赋予生气的原理”。它是高级文化的表现。 “战争”,一个与伯恩哈迪同时代的人写道,实际上是“人为了文化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不管是被看作文化的基础还是被视为进入创造和精神更高阶段的踏脚石,战争都是一个民族的尊严和自我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就像特奥多尔·霍伊斯(Theodor Heuss)说的,德国人对于自己的“道德优越性”“道义力量”和“道德上的正当性”深信不疑,而他还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绝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对于同属左翼自由派的康拉德·豪斯曼(Conrad Haussmann)来说,战争是个意志问题:“在德国,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意志,就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意志。”当然,这场战争需要倾举国之力,但正因如此,才需要每个德国人的努力。“既然在我们当中没有俾斯麦,”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宣称,“我们每一个人才都必须是俾斯麦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8月4日在国会发表了有关战争拨款问题的声明,其中甚至有“文化”这个神秘的词,社会主义者早先曾经把文化和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却用它来象征每一个德国人的事业。社会主义者在声明中说,这是有关在需要的时候保卫祖国、反对俄国专制制度的问题,是“保障我国的文化与独立”的问题。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谈到了保卫文化并借此“解放欧洲”!“所以,”《开姆尼茨人民呼声报》(Chemnitzer Volksstimme)写道,“我们此刻是在保卫整个德意志文化,德国人的自由意味着反抗残忍而野蛮的敌人。”
关于国会就战争拨款问题的实际投票,社会民主党议员爱德华·戴维(Eduard David)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站起来计票的时候,政府、其他政党还有旁听者的巨大热情令我永生难忘。”之后,他和他的孩子一起沿菩提树下大街散步。他那天心情极为紧张,以至于他不得不强忍泪水。“孩子和我在一起让我好受了一点儿。要是她不问那么多没有必要的问题就更好了。”小孩子的问题直截了当,显然威胁到了这天事态发展所唤起的幻想。
对于慕尼黑的艺术家路德维希·托马(Ludwig Thoma)来说,战争是可悲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8月1日,就在他去火车站的路上——因为他正打算去泰根塞——一群人聚集在车站前面许岑大街的街角处,有人在宣读动员令。“压力一下子释放了,”关于自己对形势的反应,托马写道,“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紧接着,面对这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如何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换取为人类工作和创造价值的权利,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而对于那些搅乱了和平的人的强烈的仇恨,使其他想法都搁到了一边。”
德国辛辛苦苦地劳动并取得了成功,却招来邻国的羡慕和嫉妒。托马义愤填膺。全国各地都显得心有同感。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是同性恋运动的领导者,他绝对不是个会欣赏自己国家的官僚权贵的人。对他而言,战争是出于“诚实和真诚”的缘故,是为了反抗英法的“吸烟服文化”。至于有人说英国是自由的故乡而德国是暴政和压迫的国度,希施费尔德回答说,英国在上个世纪就迫害过它伟大的诗人和作家。拜伦被驱逐出境,雪莱被禁止抚养自己的孩子,还有奥斯卡·王尔德被投进监狱。相反,莱辛、歌德和尼采在自己的祖国得到的是赞誉而不是羞辱。
如果说随着战事的进行,英国、法国和美国会出现千禧年的观念,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终结所有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民主”,那么在德国,人们的心态从一开始就是天启式的。在协约国,人们的看法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性质,就像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承诺的“适合英雄居住的家园”一样。然而,对德国人而言,千禧年首先是精神上的事情。托马的希望是,“在经受了此次战争的痛苦之后,将会出现一个自由、美丽、幸福的德意志”。
所以,对于德国来说,战争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它是为了追求真实,追求真理,追求自我实现,追求先锋派在战前就已经开始倡导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先锋派抨击的那些东西——物质主义、平庸、虚伪和暴政。先锋派抨击的这些尤其和英格兰有关。所以当英格兰在8月4日参战之后,它自然就成了德国最痛恨的敌人。愿上帝惩罚英格兰甚至成了很多战前是温和派的德国人的格言。
对许多人来说,战争还意味着解脱,从庸俗、约束和成规中解脱出来。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属于那些陷入战争狂热最深的人。教室和讲堂空荡荡的,因为学生们真的都跑去当兵了。8月3日,巴伐利亚各大学的校长和理事会向学子们发出呼吁:同学们!缪斯女神沉默了。现在的问题是搏斗。这场搏斗是强加给我们的,因为德意志文化受到东方野蛮人的威胁,因为德意志价值观遭到西方敌人的嫉妒。于是,条顿人的怒火再一次熊熊地燃烧起来。解放战争的热情迸发了,圣战开始了。在基尔大学的校长向学生们发出呼吁之后,男生们几乎全都参了军。
把战争与解放、自由联系起来,说它是解放斗争或争取自由的斗争,这在当时很普遍。对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来说,战争意味着“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与琐碎”;对弗朗茨·绍韦克尔(Franz Schauwecker)来说,它是“跳出生活度个假”;对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来说,制服、杠杠还有武器,就如同春药一样。《柏林地方报》(Berliner LokalAnzeiger)在7月31日的社论中说,在德国,人们如释重负,这很可能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但那种自由首先是主观的,是想象力的解放。战后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对他认为是1914年战争领导者的那些人大加挞伐,但当时他也跟其他所有人一样陷入了8月的狂热。他兴高采烈地——这一点他后来显然是想隐瞒的,他在1929年出版的《1914年7月》(July 1914)那本书中说群众是“上当受骗的人”,并谈到了“欧洲大街上集体的天真”——写了篇文章,名为《道义的胜利》,刊登在8月5日的《柏林日报》上:“哪怕是谁都不敢想象的大祸临头,这一周在道义上的胜利也永远不会被抹杀。”
对路德维希和其他许多人而言,世界好像一下子变了。“战争,”正像恩斯特·格莱泽(Ernst Glaeser)后来在其小说《生于1902》中说的,“让它变得美丽了。”瓦格纳和佳吉列夫等具有现代趣味的人试图在艺术形式中实现的浮士德时刻,此时对整个社会来说已经来到了。“这场战争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的享受。”格莱泽笔下的一个人物说。格莱泽的这些说法并不是事后杜撰的。在德国士兵从前线寄出的书信中,把战争和艺术联系起来的比比皆是。“诗、艺术、哲学,还有文化,这些就是这场搏斗的全部内容。”学生鲁道夫·菲舍尔(Rudolf Fischer)坚持认为。弗朗茨·马尔克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战争之后仍然认为战争是个精神问题:让我们在战后依然做个战士……因为这不是一场像报纸和我们可敬的政客们所说的抗击外敌的战争,也不是一个种族反对另一个种族的战争;它是欧洲人的内战,是反对欧洲精神无形的内部敌人的战争。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也有过类似的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是生的问题,不是死的问题;它是对活力、能量和美德的肯定。战争是艺术问题。“我认为战争总的来说具有相当高的道德价值,”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从资本主义单调乏味的太平日子中拽出来,这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是件好事,而在我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在一个由经受过死亡考验并了解紧张又活泼的军营生活的男人们组成的民族中,会发现更大的价值。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一个17岁的青年,在离开家乡加入他的团的时候,也对被他视为创造的行动,对“新时代的雏形”心驰神往。这个新时代还在沉睡的上帝的精神中,他但愿自己可以为创造这个新时代贡献一臂之力。
1914年7月和8月,德国上演了它的《春之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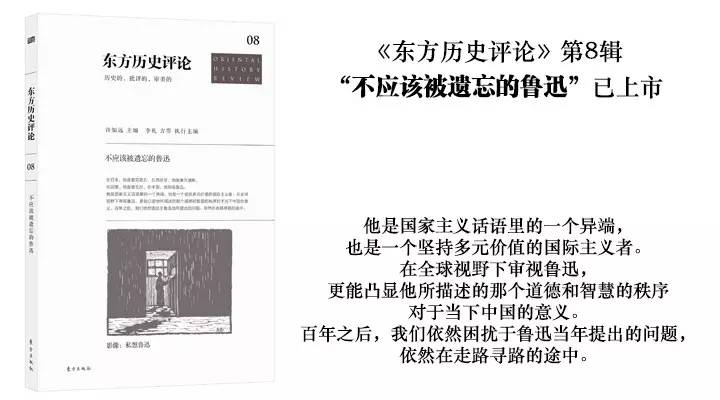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
|
李鸿章
|
鲁迅
|
聂绀弩
|
俾斯麦
|
列宁
|
胡志明
|
昂山素季
|
裕仁天皇
|
维特根斯坦
|
希拉里
|
特朗普
|
性学大师
|
时间
|
1215
|
1894
|
1915
|
1968
|
1979
|
1991
|
4338
|
地点
|
北京曾是水乡
|
滇缅公路
|
莫高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