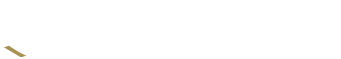
“记者的身份像古时的‘驿胥’,又有几分侠客精神。” 王瑞锋说自己在年轻时有一股想改变世界的劲,现在更追求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哪怕一句话,一个共鸣,就足够了。比起立竿见影地惩治不义,这种触达人性的力量是持久的。
本期传媒客厅,王瑞锋向传媒君讲述了他闯荡“江湖”的见闻,也为大家解答了诸多疑惑:记者是一个各领风骚三五年的职业吗?为何文字报道在影像更为流行的时代是重要的?特稿写作是否存在类型化现象?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王瑞锋揣着一张火车票和一沓现金,肩背迷彩包和“锅碗瓢盆”,在火车上站立了
一夜
,北上做新闻。凭着脸皮厚、敢吃苦、不要命的闯劲,2011年4月,新京报成立调查暗访组时,他应聘并开始了游走“江湖”的生涯。
早年做调查记者时,他像一位在不同身份、不同地点间切换的游侠:暗访救助站期间,他扮成流浪者模样横躺在雪地里;和
调查对象
周
旋,他用过各式各样的的假名片,像是北京XX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王凤兵;北京7·21暴雨,他独自徒步20多公里抵达河北野三坡重灾区报道……

▲2018年,出差中的新京报记者王瑞锋坐在马路边吃午餐,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
摄影 / 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2013年,他被派往
雅安地震灾区报道,一待25天,有次在没有充足休息的情况下写稿,等到交稿时,才发现两个小时内已不知不觉吸完两包烟,后一阵反胃,从此戒了烟。
“写稿的过程像生孩子,每一个字都痛,写完之后才会有种
解脱
”,
他形容
记者是一个焦虑的职业——采访焦虑、写稿焦虑、遣词造句焦虑,一直处于焦虑状态,只能靠自己来调节。

▲采访期间,记者注意到王瑞锋磨破的鞋子。
摄影 / 新京报记者张一川
“35岁以后能去做什么呢?
”
谈
及未来的计划,
王瑞锋有些迷茫:
”
白发记者在国外很多,在中国很少。“
一些来自现实的压力和诱惑,让国内媒体行业的人才流失与迭代速度变快。
曾经的同行渐渐离开了这个行业,不少去到高薪的互联网企业,也有人抛来橄榄枝,他开玩笑说:“要是马云非要让我去给他接班,那咱可以考虑。”
然而,新闻唤起的热情似乎是
不能
以惯常眼光估量的。
虽然脚步已经踏遍大半个中国,王瑞锋还是喜欢“跑来跑去”的状态:
“一线能更直观的感受到整个中国的变化,看见普通人的爱恨情仇,我想在一线继续做下去,不舍得离开。
”
Q:
您怎样定义记者的职业呢,要
有哪些技能和品质?
A: 中国的古代驿站有骑马送信的“驿吏”,记者不是吏,吏已经是有官职身份了。我把记者定义为“驿胥”,驿本身是传递信息的,胥是古时候一种半官半民的小差役。如果做调查的话,就更偏向侠客一点,当然你也可能官商勾结搞敲诈勒索,那就是很坏的那种。
我认为做记者,最重要的首先是人品正直,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就是不能对证据调查不够就掺一些合理想象,这容易出大麻烦,要下足功夫,对每一个新闻当事人负责。
Q:您已经做记者十多年了,突发、暗访、调查都有做过,早期的经历对后来有何帮助呢?
A:
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的话,最好是一个多面手,什么类型的报道都得做,从业经历丰富了之后,再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面,成为在一个领域里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型记者。
做突发、暗访的经历,帮助我积淀了大量采访经验,锻炼了随机应变的能力,为后来做调查夯实了基础,
不然可能会出现采集不到核心信息的情况。
Q:
有句话说“记者最宝贵的两个品质:
敏感与抽离。
敏感产生共情,抽离让你成为上帝。
”您认同吗?
A:认同。抽离是为了保持报道和采访的客观性,不能因为同情当事人,就在写稿时不加甄别,对他所有话一门心思相信;敏感能够让你更深入的挖掘人物内心。在做
《为父追凶25年》
那
篇报道时,两姐妹在坟头哭,我也一起哭得稀里哗啦,但写稿时会冷静克制。这需要自己找到快速调节转换的方式。我很同情你,但是你说的每句话得有证据才行。
A:这要靠证据链。有物证,肯定先相信物证,如果是口证的话,那就三人交叉信源。特稿里边我们有时会把信息源隐去,这种题材就决定了只能这样,但涉及到一些很核心的细节是需要证实的,是需要证据的。
Q:
一般什么样的细节会被您选进文章里?
有什么技巧吗?
A:特稿需要营造一个气场,用足够多的细节来围绕主题运行,
留下
与主题丝丝相扣的细节。像电影的每一帧镜头都是有用的,特稿中的细节要么是展现他人物性格,要么是和接下来的情节相关。
对细节的捕捉上,主要是靠敏锐的观察,留意到一些特别之处时,尽量穷究采访对象,不能凭自己感觉。筛选细节的过程就像炒菜,那些无用的细节就相当于是菜根或者要丢掉的菜叶子,略
去无用的细节,剩下有用的细节。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特稿记者,顶多算一个正在学习的小学生,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
Q:目前特稿是否存在类型化现象?比如选题以杀人犯等为常见题材,以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为背景进行归因。
A:关注社会的失范现象是新闻的职责,特稿写作也遵从新闻的大规律。
记者虽然不能像警方一样定性犯罪的直接原因,但我们希望通过文字给大家尽可能的还原一个人可能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深渊的。
最终把一些事实呈现给大家,去探究一种反社会型人格的形成原因,共同反思怎么去弥补,防止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A:
避免“模板化”写作,主要是要找到切入的角度。有时,虽然同题材的稿件脉络是一个类型的,但你最终是要靠细节来打动人的,靠细节来体现差异,而每个细节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A:通常我会考虑一个选题是不是大众普遍关心的、关系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它能不能反映出我们的法治、机制、体制等普遍性的问题,或者是引起人共鸣、共情的故事。在报题时,我就会考虑好为什么要做这篇报道,开始时会有一个判断,操作过程中也会有新的发现。
Q:
您认为特稿的独特价值体现在?
为何它在影像更为流行的时代是重要的?
A:特稿能够产生叩击一点回声四方的效果,像往你的心海里边扔了一个小石头一样,存在潜移默化的力量。看完这篇稿子之后,读者的心灵能够有一个小小的、真正的触动,哪怕这一句话让读者觉得很开心,或者是小伤感,产生共情,我就非常满足了,就觉得这稿子很值。
特稿采访追求的细节非常细致琐碎,通过记者的观察来获取的。文字就像一个个小石子一样,扔到河里冲刷完之后沉下去的那一批,而影像就像一眼能看到的波浪。
Q:
剥洋葱开始将深度报道结合视频呈现,您认为视频化的表达方式有何优势?
A:我认为视频和文字的受众是两波人。视频的优势是直观,不需要描写,甚至不需要提问,一个镜头过去,大家都知道了。视频
也
可以和文字结合报道,现在剥洋葱已经在做这样的尝试,效果很不错。
▲广西白马镇的鬼火少年(上):玩摩托车成为他们排解无聊的出口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 X “我们视频”联合出品
▲广
西白马镇的鬼火少年(下):那台鬼火代替了所有人在陪伴我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 X “我们视频”联合出品
A:我会和采访对象建立起信任关系。像采访骑自行车的老师,他开始是不信任我的,对我也不屑一顾。我就弄辆自行车,跟他天天一块骑,他会感觉这个人也不容易,就会聊上两句。
Q:
作为记者,经常免不了进入危险的现场,接触大量边缘与弱势群体。
如何平衡和疏解自己的心态呢?
A:只能靠自己排解,我自己的话就是喝喝酒,写写散文、打油诗,玩游戏。刚入行做突发新闻时,看到一些悲惨的现场会有冲击,但后来做得
久了是不是就不震惊了?
不是,是心软了,见到苦难的东西不忍心看了。
新闻反而先把自己给融化了。
Q:
有哪些敬佩的新闻人呢?
在您的印象中,现在的新闻业
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A:我喜欢南方周末的那批老派记者,南香红、李海鹏、叶伟民、杨继斌那些老前辈的作品,无论是特稿还是调查报道,都是非常经典之作。
新闻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
年,新闻业目前虽然凋零,吃得还是青春饭,也算有人前仆后继,带着镣铐舞下去。
Q:近年来有哪些满意的作品呢?
您可以谈一谈喜欢的
稿件背后那些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