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日子。很多人期望拜登击败特朗普,让美国“拨乱反正”,但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美国走到今天这样子,并不是特朗普的锅,而是资本主义自身出了严重问题。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只是资本主义弊病爆发的一个结果而已。
资本主义当年也是眉清目秀的屠龙少年,它所打倒的封建主义,依靠混弄人的一套“君权神授”鬼把戏,掩盖了土地的不平等占有,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严重的阶级不平等。
这套鬼把戏集大成者,就是横行欧洲千年之久的天主教。
资本主义
虽然号称“
自
由
平等人权
”
,本质上又是另外一套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人剥削人的游戏,它一方面要靠漂亮的口号来忽悠劳苦大众来为自己火中取栗,另一方面又不能真的给大家带来
“
自
由
平等人权
”
,还不能像封建主义那样用宗教来明晃晃地忽悠人。
因此,它必然
需要一套
更加高明、更加隐蔽的忽悠人的骗术。
当年克伦威尔不知道欺骗才是核心竞争力,真的用自由平等人权来发动群众,打造出战斗力爆棚的“新模范军”,结果思想觉醒的人民大众要争取自己的权力,把克伦威尔等人吓得够呛,整出一个无比纠结拧巴的“英吉利共和国”,仅仅维持了短短十年就覆灭了。
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苦心研究骗术,终于完成了上位。
其本质与天主教那套也是换汤不换药,
不过资本代替了上帝,
经济学与法学代
替了天主
教会,用隐性的阶级分层代替了
封建等级
。
此后
几百年,资本主义
摧枯拉朽,
摧毁了一切旧制度,
骗术也变得越来越高级,甚至把苏联都给忽悠瘸了,后者
主动解体,引颈就戮
。
但是,这套骗术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一是需要能通过技术进步持续做大蛋糕,虽然蛋糕分得并不合理,但是只要穷人手里的蛋糕依然在持续变大,就不会穿帮。
二是要全世界都要相信这套骗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利益分配机制,实在不行就从外面吸血以自肥。
这套把戏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渐渐玩不下去了。让骗术破产的,就是无神论者的大本营,战天斗地“专治各种不服’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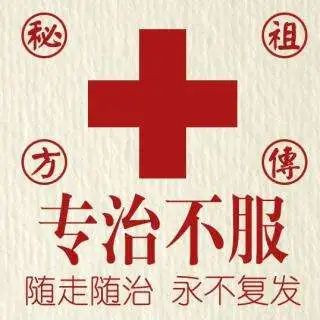
本来美国转移产业链到中国是为了让中国人做牛做马,养活美国的上等人,但是中国维持了独立自主,也保持头脑清醒没有中圈套,反而要推动自身产业升级,反超美国。而美国为了便于实行骗术,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自身早已产业空虚,只剩下高大上的高科技和金融,把大量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美国人抛入深渊。之所以这些人教育程度堪忧,原本也是骗术中的一部分。
这群陷入困境的美国人主要是内陆和五大湖区的白人,他们高呼回归传统的口号,梦想恢复昔日荣光,将特朗普送上台。
特朗普上台又能怎么样呢?美国的根本问题是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要想解决问题,只有先解决资本主义。于是特朗普只能一方面做做动作让他的选民相信他在兑现承诺,另一方面继续忽悠来圆谎。
于是美国变得日益分裂,一部分人信川普得永生,另一部分则视之若仇寇,双方互相仇视敌对,愤怒与日俱增。
特朗普看到了问题,但是找不到解决之道,拜登则干脆掩盖问题,当做其不存在。
回到过去继续忽悠中国,那是不可能了。特朗普这几年折腾下来,已经彻底撕破脸,刀子都掏出来在面前比划半天了,再收回去说我们继续维持友谊,三岁小孩都骗不了。彻底撕破脸军事进攻或者金融洗劫?中国已经严阵以待,再说以美国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这种折腾。
工业化+技术升级+忽悠,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竞争力。如今身体已虚,就剩口花花地忽悠了。但是忽悠又忽悠不动了,只有应了熊彼特生前最后一次演讲的标题“长驱直入社会主义”,才是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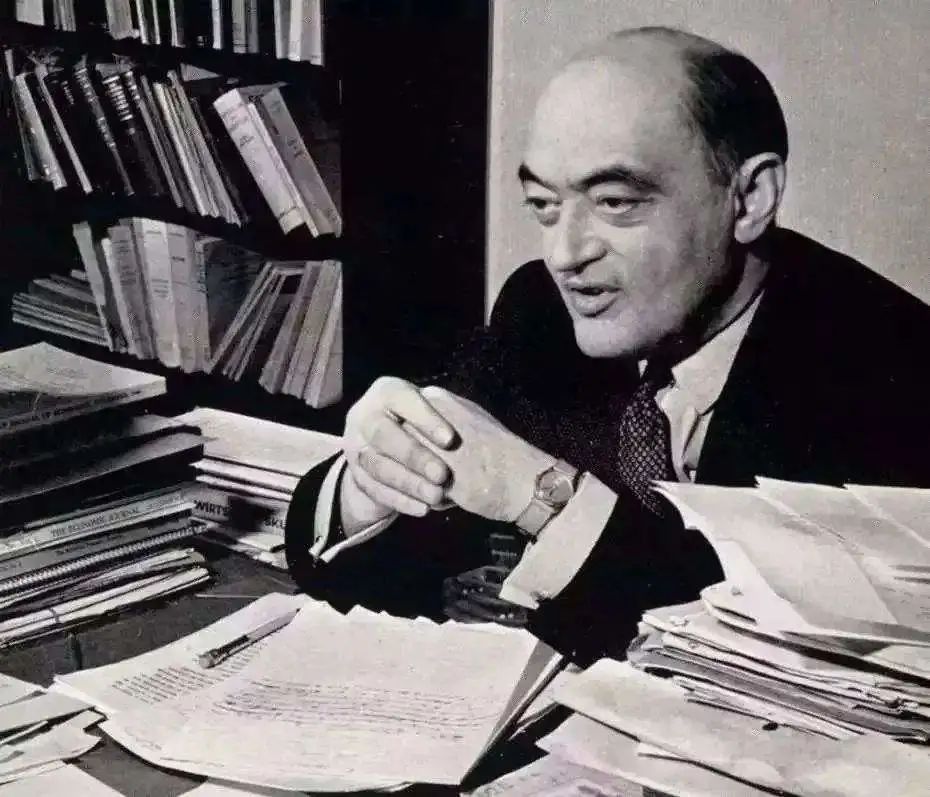
演化经济学创始人熊彼特
资本主义因忽悠成功上位,最后也会因忽悠破产而寿终正寝,走完一个历史轮回。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号称英国资本主义革命的成功标志——光荣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如果用几句话来表述英国光荣革命的缘起,大概是这样的:
国王:要信仰自由,反对宗教迫害!
国会:我们反对,一定要迫害异教徒!
于是爆发了革命。
革命完成后,国会说:我们革命的成果,是实现了信仰自由……
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们“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的光荣传统……
自从亨利八世为了迎娶小三安妮·博林,于1530年开启英国宗教改革大幕以来,英国的宗教纷争断断续续,到詹姆斯二世即位的1685年,差不多已经进行了150年。
对比欧洲各国同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出,宗教改革是一个漫长、痛苦并充满曲折和反复的过程,表面上是关于信仰的大变革,但内里的驱动还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即更高效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工商业化)。大陆上的宗教斗争要比海岛激烈得多,法兰西和德意志由于封建贵族势力强大,新教势力总体上归于失败。只有自古以来是工商业聚集地、从未形成王权国家的荷兰,新教势力通过艰苦卓绝的80年荷兰独立战争,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才取得成功。
英国这个海岛国家,宗教改革(生产方式变革)呈现不同寻常的特殊性。通常情况下,封建国王维护的是土地贵族的利益,因为国王自身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地主,是封建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但是在英国都铎王朝时代却不是这样。一方面,自1215年《大宪章》确立的贵族自由传统,使得贵族叛乱在此后几百年间越演越烈,终于在1455年至1485年的玫瑰战争达到最高潮,都铎王朝的国王首要考虑的事情成了如何削减贵族势力,杜绝叛乱的发生;另一方面,英国需要应对大陆上强大竞争对手(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的挑战,发展经济实现富国强兵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在这种特殊环境下,都铎诸王(除玛丽一世之外)成了封建国王中的异类,他们背叛了固有的阶级利益,选择了主动消灭封建贵族(包括世袭土地贵族和天主教会修道院)发展收益更高的工商业的做法,使得新教势力(资产阶级)迅速增长,天主教势力(地主阶级)大幅削弱。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以国会为阵地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长,国王的权威也不断增强,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王权达到历史的顶峰。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逻辑,在外部压力减退之后,手握强大权力的国王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接下来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压可能会危及自身统治的资产阶级,法国的君主发动对胡格诺派的战争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英国历史在这里恰好又发生了一次转折。
都铎王朝在权力达到顶峰之时自然绝嗣,一个弱小的且原本与英国敌对的国家(苏格兰)的国王坐上了英格兰王座。想像一下,如果北宋王室绝嗣,把与宋王室联姻的云南大理段王爷请到开封当皇帝,北宋国民对其能有多少尊重。
更何况,詹姆斯一世的母亲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在英国被囚19年,整出多少幺蛾子,英国从上到下都烦得透透的。这一重大变故,使得资产阶级主导的英国国会有机会、有动机也有能力,掌握政治主动。
斯图亚特诸王作为弱势的封建国王,在强大的英国国会面前显得格格不入,国王与国会的纷争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主线。
这一时期又恰好赶上北美殖民地的开辟,英国采用了主动向北美输出人口的办法来释放内部矛盾。但即使如此,虽然英国具有岛国这一先天地理优势(外来入侵的可能性很小),仍然爆发了伤亡惨重的内战。可以想见,如果英国不是岛国无法排除外来势力干涉,再没有北美这个“减压阀”,各方势力都要在岛内决出高下,英国内战还不知道得有多惨烈。
英国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工商业化),是如此地曲折并充满戏剧性,天时、地利、人和、运气缺一不可。
同时代的明朝资本主义程度更深,导致民富国穷,政治上陷入党争,虽然工商势力实质上掌握了政权,但最终被外族入侵灭了国,成为工商业化转型失败的反面教材。
十七世纪末期,英国终于基本将代表封建势力的天主教消灭殆尽,眼看宗教改革(生产方式变革)就要获得最终的胜利,可以说就差最后一哆嗦了,却正赶上詹姆斯二世这个以法国为榜样、信奉天主教且不愿妥协的国王,因此,宗教改革的最终之战不可避免地上演了,这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还要从“钢铁直男”詹姆斯二世说起。

詹姆斯二世
詹姆斯二世亲眼目睹了哥哥查理二世的执政历程,国会两党之间丑陋的党争,还经历了辉格党对他的刺杀,再对比法国路易十四的执政历程,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像路易十四那样加强王权,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忠于王室的陆海军,才是一个真正的国王应该做的事。
他本来就是军人出身,曾在法国名将蒂雷纳手下战斗,亲自指挥两次英荷战争,以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已成为他的思维定势。在他看来,如果国王手中有了坚韧而锋利的宝剑,那么喋喋不休的国会,无法无天的辉格党和气急败坏的清教徒都会俯首听命。既然法兰西可以排除一切内部纠纷,团结在太阳王的周围变成欧洲第一强国,英国也能通过同样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时代,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第一强国,并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输出地。欧洲各国都在有意无意地模仿学习法国的成功经验,就如同今天的世界各国都在有意无意学习模仿头号强国美国一样。
其中,普鲁士将法国经验与本土实际相结合,成为其中最出色的一个学生,在十八世纪中叶变成欧洲列强,在十九世纪又发奋向英国学习,打败了法国这个老师,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直到一战爆发前,普鲁士德国甚至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模仿的对象。俄罗斯也通过大力学习引进法国经验而成为另一个列强,夹在这两个国家中间的波兰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嗨,导致三次亡国。
英国的詹姆斯二世也想引进法国的先进经验,却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今天的美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阴暗面也不少。
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也是同样的道理,其最大的阴暗面在詹姆斯执政同年出现
了
。
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将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的主张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废除,因为他觉得胡格诺教徒不听号令,实在是法国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应当予以驱赶。
早在法荷战争期间,路易十四就对胡格诺教徒暗地里与荷兰人之间的那些小动作颇为不满。因为荷兰人普遍信奉的宗教与胡格诺教徒同属新教加尔文宗,许多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与荷兰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侵略荷兰,荷兰自然也要千方百计针对法国搞颠覆活动,路易十四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不安分的异教徒臣民与自己的敌人站在一边。
财政大臣柯尔贝虽然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充分认识到胡格诺派教徒多半都是商人与手工业者,对于法国经济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一直力劝国王辩证客观地看待这件事情,宽厚对待胡格诺教徒。

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
但是,随着1683年柯尔贝离世,胡格诺派的最后一个保护伞消失,路易十四终于决定对国内的异教徒下手。
路易十四因此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可能比他犯的其他所有错误都要严重,彻底葬送了法国的国运。这是今天的中国也要深深引以为戒的。
随着胡格诺派的大举出逃,使得法国经济遭受重创,而其他国家迎来了一轮经济发展,这些人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军人、学者、作家、商人、工厂主、技术工人等等,他们将法国最好的技艺以及对祖国的满腔愁恨,带向了欧洲乃至世界各地。
驱逐胡格诺教徒,使得路易十四成了舍己为人的“活雷锋”。
荷兰建造了数千栋房屋容纳前来投奔的教友,借钱给他们重建事业,给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既拉动了荷兰的经济,又增加了一大批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普鲁士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颁布《波茨坦诏令》,引来了2万多胡格诺难民,以至于首都柏林有1/5的人说的是法语,这些人将在未来为这个小国的崛起作出无法估量的贡献。
可能也正是收留胡格诺派难民以及犹太难民对本国造成巨大利好的历史,使得今天的欧洲各国对于接受难民这事颇为积极。然而时移境异,今天的欧洲难民与欧洲属于不同的文明,并且欧洲难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难以解开的死结。
路易十四的愚蠢举动,导致人才技术财富大量流出法国,固然糟糕,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法国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
荷兰人仇视法国不假,法国胡格诺派与荷兰人基于共通的资本利益暗通款曲也并非空穴来风,但是,荷兰商业寡头所代表的资本权力与威廉三世所代表的政治权力之间同样存在尖锐矛盾。
本来这个矛盾如果善加利用的话,有可能使得荷兰陷入内斗,路易十四的举动反而帮了威廉三世一个大忙。
荷兰议会在1672年将最高政治权力授予威廉,那是在外有敌国大军兵临城下,内有暴动民众以死相逼的紧急情况下,所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当危机过去,一部分荷兰商业寡头又故态复萌,与威廉三世为代表的奥兰治派再次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
荷兰是当时欧洲头号商业强国,商业寡头的势力比英国同行要强得多的多,而且在第一次无执政时期(1650年-1672年),他们已经尝到了掌握国家权力的快感,食髓知味之下岂可轻易放手?
威廉三世的为人,既不如他的叔爷爷莫里斯亲王那么强势,也不像他的舅舅英国查理二世那么圆滑变通,很难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而且他在政治上稍有举动,就会引发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强烈波动,进而导致社会动荡,更令他投鼠忌器。
例如,当格德兰省授予他格德兰世袭领主之位的消息传开后,阿姆斯特丹的股市因此崩盘,民间怨声四起,使得威廉只能拒绝领主之位,改为担任格德兰省的执政。
虽然荷兰也有看到国家大局而鼎力支持威廉的商人,例如加斯帕·菲格与安东尼·海因斯等人(这两人都是在1672年扶他上位的重要助力,说白了就是类似吕不韦那样的角色,安东尼·海因斯后来一直担任荷兰大议长),但大多数商人都是只看眼前的商业利益而不顾国家命运之辈。
特别是最富裕的荷兰省,更是商业寡头的大本营,他们坚持自己的自由判断和决策的权力,拒绝受执政的节制和调遣,因此奥兰治派和商人派的摩擦频频出现,威廉三世又走上了威廉二世曾经走过的老路。
后世一些历史学家对此深感惋惜,他们认为只要威廉坚持彻底的宪政改革,将荷兰转变为更加有效率的中央集权体制,荷兰就有希望实现中兴,而不会迅速走上霸权终结的不归之路。但实际上这只是部分历史学家的一厢情愿而已。以当时的荷兰局势,如果威廉三世坚持这样做,下场不会比詹姆斯二世好多少。
对当时的法国来说,想办法挑动荷兰的商人派与奥兰治派内斗,甚至煽动荷兰省独立才是上上之策,而不是着急对付国内的胡格诺派,相反,应该给他们更好的经商条件,鼓励其与荷兰省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更增荷兰省的离心。
荷兰省占荷兰共和国全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若奥兰治亲王失去对荷兰省的控制,荷兰也就歇菜了。如果地缘政治高手黎塞留尚在人世,他一定会采用这样的策略。
在中美斗争的大背景下,中国高调建立海南金融自贸区,推动金融开放,与美国的一部分金融资本建立利益纽带,也是基于同样的政治智慧。
直到1684年之前,威廉三世都和荷兰省议会处于尖锐对立之中。但是1685年,詹姆斯二世上台与路易十四废除宗教宽容两件大事,使得威廉三世一下子拨云见日。哪怕是再短视的荷兰商人也能意识到,法国恐怕又要对荷兰动手了,英国也会对荷兰采取敌对态度,只有依靠威廉三世才能对付路易十四,因此荷兰国内斗争大为缓和。
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迫害胡格诺派教徒,不仅使得法国元气大伤,也使得英国人对自己的天主教国王的猜忌进一步增强。
虽然詹姆斯二世宣布他坚持宗教宽容,欢迎胡格诺派教徒来英国安居乐业。但是路易十四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活靶子,辉格党人只要略作宣传就能使英国人相信,这只是詹姆斯的权宜之计,如果他的统治稳定下来,一定会效仿路易十四的举动。
来到英国的胡格诺教徒向教友们大倒苦水,倾诉他们在法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得英国人进一步确信,必须要有所行动,否则就只能在弥撒和火刑柱中做出选择。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公众舆论的风向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民众被洗脑得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政府无论做什么,哪怕是为民众谋福利的好事,都可以引申到政府有什么罪恶或者不可告人的企图。
舆论武器被用到极致,黑的可以变成白的,白的也可以变成黑的。
辉格党逃亡分子和他们曾经想扶上位的查理二世私生子蒙默思,此时都聚集在荷兰。威廉将这位表弟待为上宾,可是查理二世驾崩噩耗传来那天,威廉立即对蒙默思下达逐客令,这意思很明显:大兄dei,时候到了,赶紧回去抢王位吧!
蒙默思的性格有点像他的父亲查理二世,在荷兰好吃好喝的住着,有衣食无忧的生活,有美丽风情的情妇,已经快要达到“乐不思蜀”的境地了。
被威廉三世驱逐后,蒙默思本来想去德意志继续混吃混喝,但是他周围的这些人可不答应。蒙默思的周围,都是曾经参与策划暗杀查理二世以及约克公爵詹姆斯的狂热辉格党分子,他们怂恿蒙默思“为你的权利而斗争”。
此外还有一个狂热的失意分子,是王政复辟时期被苏格兰议会砍了头的苏格兰阿盖尔伯爵第八之子阿盖尔伯爵第九,他也琢磨着报父仇,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土地。

阿盖尔家族的家徽
(该家族目前仍然存在)
对于一向爱财如命精打细算荷兰人来说,花这么多钱供养着这些逃亡分子,不是吃饱了撑的,而是要让他们替自己“火中取栗”。国王驾崩权力交接之时正是人心惶惶形势不稳的时候,这些逃亡分子正好可以物尽其用,回到英国把局势搅得再乱一点才好,这样荷兰人才方便浑水摸鱼。
当年,查理二世和阿盖尔伯爵第八带着大军去英国,妄想接收权力,被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打得全军覆没,差点命丧英格兰;如今,他们的儿子和一小撮追随者分乘三条小船返回英格兰,梦想着如同当年亨利·都铎(亨利七世)回国夺权时那样,全国望风归降,荣登大宝之位。
可他们却打错了算盘,詹姆斯二世是合法继位的国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恶行,当年的理查三世是杀了自己的侄子篡位惹得天怒人怨,英国人还不至于仅仅因为国王信仰天主教而起来谋反。恰恰相反,包括一部分头脑还算清醒的辉格派在内的政界上层人士及一般的贵族、乡绅,都对蒙默思起义抱敌视态度,他们心里清楚,私生子如果能够夺位成功,英国将陷入比玫瑰战争更加混乱的情况。
别忘了,仅查理二世就有十五个私生子,这要一个个都来主张继承权,那还不乱了套!
“这是他们所预想到的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中最坏的事,因而他们希望将蒙默思的反叛尽快加以彻底击败。”
蒙默思等人在波特兰岬角的莱姆里季思港登陆,聚集了几千叛乱人马,詹姆斯二世派遣自己的亲信老丘吉尔率领临时召集的民兵前往平叛。蒙默思叛乱反倒使国会中反对国王的辉格党进一步陷入不利局面,议员们不管是不是心里反对国王(其中不少甚至与叛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必须公开宣誓与国王同生死共患难。
由于英国没有常备军,临时召集的民兵作战很不给力,幸好还有一支小型的皇家骑兵和冷溪近卫团作为核心。在老丘吉尔的出色指挥下,王军最终获得胜利,经过无情的追击和大规模的屠杀之后,叛军溃败,老丘吉尔也借着平叛的机会收获极大的威望,詹姆斯二世对他的信任进一步巩固。
蒙默思在断头台上宣布:“我是作为英国国教的新教徒而死”。他身边给他做临终圣事的教士回答:“如果你是英国国教的教徒,就必须承认服从王权的原则是正确的。”随后,法官杰弗里斯被派到西部地区处理俘虏。他绞死了二百多人,并将大约八百人流放到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殖民地。
威廉三世非常乐于见到这一切的发展,他没有阻止蒙默思自投罗网前去送死,甚至促成了这一切。
蒙默思死不足惜,他不过是荷兰人投石问路的棋子而已。如果情况乐观,蒙默思成功夺权,那么英国就会有一个新教国王,荷兰在蒙默思身上投资不少,而且蒙默思受亲荷兰的辉格党控制,他必然亲荷兰远法国,成为荷兰对抗法国的忠诚盟友;
如果蒙默思兵败被杀那更好,詹姆斯二世年纪大了活不了多久,威廉和妻子玛丽,就是接下来英国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换句话说,通过这一招“借刀杀人”,扫除了威廉入住英国宫廷的障碍。
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是,老丘吉尔借着击败蒙默思,获得了詹姆斯二世牢不可破的信任,“那件事”就更有把握了。
詹姆斯二世自己也清楚时间紧迫,他已经五十二岁了,身后又没有跟他一条心的继承人,要想在英国复兴天主教信仰,一切都得争分夺秒抓紧进行。他趁着平叛的机会,将原来被清洗出去的信仰天主教的军官重新召回军队,并对国会说,为了维持国内治安,防止蒙默思叛乱这种事情再度发生,必须保持一支强有力的常备陆军。
国会最厌恶最畏惧的就是常备陆军,有了常备陆军就没有民主,这是英国清教革命期间留下的惨痛经验。但是,他们现在没有任何借口反驳,因为一旦反对,国王只要下令追查他们是否与这桩叛乱有联系,恐怕没几个人是清白的,所以国会只得火速同意拨款七十万英镑来加强陆军,以免国王借题发挥。
在得到拨款之后,詹姆斯立即关闭了这届国会。
詹姆斯的下一步的目标,是建立一届忠于国王的国会。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人不到总人口的3%,这一方面说明英国的民主只是精英们的专利,另一方面说明,想要操控选举其实并不困难。
在乡下,靠各郡总督和地方法官基本可以控制选举,城镇的选举则由市政机关来控制。拒绝帮助他组成保王国会的总督相继被免职,市镇自治机关和地方法庭也遭到清洗,代替他们的是忠于国王的人,其中主要是天主教徒或不信奉国教的贵格会教徒。
这些人以前饱受打击,是国王给了他们平等的机会,因此他们十分忠于国王。
詹姆斯二世随后对政治机构进行了大换血。他建议枢密院废除《宣誓条例》和《人身保护法》,时任枢密院院长的哈利法克斯指出,这种做法会触犯一系列法律,于是他丢掉了院长职务,甚至失去了枢密院成员资格,善于见风使舵的“骑墙派”森德兰伯爵罗伯特·斯潘塞接替了他,而那位双手沾满叛乱者鲜血的法官杰弗里斯出任掌玺大臣。
詹姆斯多次撤换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并建立了一个教士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防止圣公会教士进行反对天主教的说教。与此同时,国王扩充了他的军队,到1688年秋天,詹姆斯建立了一支四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