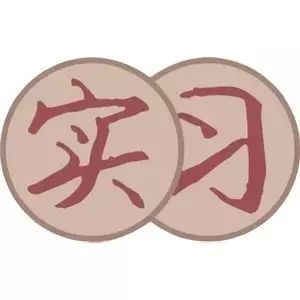在写作此书较早的版本时,我本人是作为相当专一的功利主义者来这样做的。
在我看来,既然功利主义的原则表达了普遍仁爱的立场,任何拒绝功利主义的人必定是无情的,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具有仁爱之心的;不然,就必定是概念混淆的牺牲品,或者是不加思考的传统思维方式的追随者,或者可能是某一宗教性伦理学体系的信徒,而这种伦理学体系借助形而上学的批评就能够推翻。
无可否认,功利主义确实会产生与通常的道德意识相左的结果,但我倾向于采取这样的观点:
“通常的道德意识太过糟糕。”
也就是说,我倾向于拒绝这样一种通常的方法论,即通过查看其如何与我们的特定场合的情感相合,来检验一般的伦理原则。
毕竟,有人可能会感知到如下一些内容。什么是道德的目的?(回答这个问题是要做出一个道德上的判断。认为有人能够在不做道德判断的情况下回答“什么是道德的目的”这个问题,是要容忍自然主义的谬误,也就是从“实然”中推断出“应然”的谬误)假定我们说——因为它肯定至少有诱惑力的——道德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全体的幸福;那么,看起来马上就会推断得出,
我们应当拒绝任何与功利主义原则相冲突的推定的道德规则,或者拒绝任何与功利主义原则相冲突的特定的道德情感。
不可否认,在特定情形中,我们确实会有反功利主义的道德情感,但或许应该尽可能地不去考虑它们,因为这是由于我们在儿童时代经受的道德训练所致。
(
这种思路的缺点在于,赞同功利主义的一般原则可能也是由于道德训练所致。即便仁爱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内心态度,这种考虑因素至多可能具有说服力,而缺乏任何清晰的理论依据。从道德态度的自然性到其正确性的论辩,将会犯自然主义的谬误)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相比于特定的道德戒律,功利主义的一般原则可能会向我们建议更多的东西,这恰好是因为它很普遍。
因而,我们可能倾向于拒绝这样一种伦理性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意味着,在特定情形下,应当借助自身的反应来检验一般原则。
与之相反,我们可能逐渐感到,在特定情形中,应当参照最一般的原则来检验我们自身的反应。与科学相类比并不适合,因为声称观察性的陈述比此类陈述所检验的理论更具有坚实基础,这样的说法并不远离事实真相。
但是,为什么更为特定的道德情感要比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更值得关注呢?
如果我们接受不可知论的元伦理学,则在伦理与科学之间不应进行类比的看法,便显得颇为似是而非。
功利主义者将参照一般原则来检验他的特定情感,而不是参照他的特定情感来检验一般原则。
现在,当我具有某种倾向来采纳这种观点时
(假如不具有这种倾向,我本来不会有动力去陈述与捍卫作为规范伦理学体系的功利主义)
,我同时也感觉到存在相反的倾向,也即,我们有时应当通过自己对一般原则在具体场合的适用的感觉,来检验一般原则
(我有点像摩尔回答史蒂文森那样,他一方面感到自己正确而史蒂文森错误,另一方面也感到自己错误而史蒂文森正确。我的犹豫不决可能更难以解决,因为在我的情形中,它是涉及感觉的问题,而不是理解力的问题)
。
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功利主义可能产生一些非常可怕的后果,这一点并不难表明。
在一篇非常清晰而简洁的探讨性评论文章中,麦克罗斯基
(H. J. McCloskey)
考虑过这样的情形。
假定一个小镇的治安官只有通过“陷害”并处死(作为替罪羊的)一个无辜之人,才能够预防严重的骚乱(在骚乱中,数以百计的人会被杀死)。在这种现实的情形中,功利主义者通常能够认同我们对此类事务的正常的道德情感。
他会指出,存在发现治安官弄虚作假的可能,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削弱共同体对法律与秩序的信念与尊重,这样的后果将比数以百计的居民痛苦地死亡要糟糕得多。
但正如麦克罗斯基随后指出的,他能举出这些反对意见都不适用的情形。比如,人们能够想象,治安官可能拥有很好的经验性证据,证明他不会被发现。因此,反对的意见,也就是认为治安官明知他所“陷害”的这个人将会被杀,而他只是或然地相信,除非他陷害这个人,不然骚乱将会发生,便是不成立的。
类似于麦克罗斯基这样的人可能总是如此来强化他的故事,我们于是不得不承认,如果功利主义是正确的,则治安官就必须陷害这个无辜者。
(麦克罗斯基也很有说服力地提出,规则功利主义也包含类似的令人反感的后果。也就是说,一个不公正的惩罚制度可能比公正的惩罚制度更为有用。因而,即便规则功利主义能够与行为功利主义清晰地相区分,一个功利主义者通过从“行为”模式后退到“规则”模式,也将无法避免其理论带来让人反感的后果)
现在,虽然一个功利主义者可以主张,发生像麦克罗斯基所设想的这种情况,从经验来讲不太可能,但麦克罗斯基会指出,出现这样的情况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如果这名功利主义者拒绝不公正的行为(或制度),他就显然在放弃他的功利主义的立场。
麦克罗斯基评论道:
“但就我所知,在当代的功利主义者中间,只有斯玛特乐于采取这种‘解决方案’。”
在此,我必须提出温和的反对意见。麦克罗斯基对“乐于”一词的使用,无疑使我看起来成为非常应受斥责的人。
即便在我处于极为功利的情绪之中时,我也并不乐于看到功利主义的这种后果。
不过,不管多么不乐意,功利主义者必须承认,他得出了可能使自身陷于不正义状况的结果。
我们希望,这只是逻辑上的可能,而并非事实上的可能。在希望如此时,我并没有与功利主义不一致,因为任何不正义都会引起苦难,因此只有作为两恶相权取其小时,才能将这样的不正义予以正当化。功利主义者被迫在两恶相权取其小的情形越少出现,他就会越愉悦。
人们不必将功利主义者想成那种不仅不能信任还要踢他一脚的人。
作为一个未经专业训练的社会学观察的问题,我该说,一般而言,功利主义者要比通常可信的人更值得信任,而那种害你的人很少是功利主义者。
我们很可能不喜欢并且害怕这样的人,他在麦克罗斯基所设想的那种情形中,能让自己去做正确的合乎功利主义要求的行为。
虽然在这种情形中,这个人可能做了正确的合乎功利主义要求的行为,但他的行为将表明他的强硬和缺乏敏感,而这会使他成为危险之人。
必须记住,人们既有自利的倾向,也有利他的倾向,如果这样的人被诱使去犯错,的确,他可能会实施非常错误的行为。
功利主义者记得人可能具有的道德弱点,他可以十分坚定地对这类人表达偏好,尽管他们不总是能让自己去做正确的合乎功利主义要求的行为;同时,功利主义者也可以十分坚定地让自己与这样的人交往,尽管后者在极端的情形中,由于太敏感而无法按功利主义的方式行事。
不,我并不乐于得出,麦克罗斯基确定地声称功利主义者必定会得出的结论。
但我也不乐于得出背离功利主义的结论。
因为如果这样的情形,即不正义是两种罪恶(就人类的幸福与苦难而言)中较小的那个,确实发生了,那么,反功利主义的结论同样令人难以接受,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必须选择更大的苦难,或者是要大很多的苦难,比如像数以百计的人们遭遇痛苦的死亡。
为了逻辑一贯,功利主义者还是必须接受麦克罗斯基提出的挑战。让我们期望,他所设想的那种可能性仅仅只是逻辑上的,从来不要成为现实。
无论如何,即使我已经建议,在伦理学中应当通过一般的内心倾向来检验特定的情感,麦克罗斯基的例子让我还是倾向于认同相反的观点。或许,期望能够存在一种在所有方面都合乎我们天性与情感的伦理学体系,的确是期望过高了。
在一个人身上存在相互冲突的内心倾向,这绝对是可能的。不可能存在合乎我们所有内心倾向的伦理学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如果这样的理论是功利主义理论,则有时实施不正义的行为可能是正确的,这一点会让一个受正常教育长大的人感到极不满意。
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理论不是功利主义理论,而是具有道义论因素的理论,那么,它也会蕴含不令人满意的内容,也即,有时不应该防止那些可避免的苦难(或许是非常大的苦难)。
人们可能认为,某种按罗斯的思路提出的折中论,对功利因素与义务论因素进行平衡,它可以提供一种可接受的妥协方案。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平衡”不太可能:我们很轻易就能感觉到,有时会被拉向这边,有时会被拉向那边。
人们如何能在一方面是严重不正义的行为,另一方面是数以百计无辜者痛苦死亡之间,进行“平衡”呢?
即使我们忽视纯粹自利的态度,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待自己就和对待他人一样没有偏向,也仍可能并不存在让所有人都满意,甚或让一个人在不同时间都满意的伦理学体系。
这可能与科学颇为相像,也就是没有科学理论(包括已知的与未知的)是绝对正确的。
倘若这样的话,则世界比我们所认为与希望的要更为纷乱无序。但即便世界并不纷乱无序,人们的道德情感却可能如此。
基于人类学的依据,极为可能的是,这些情感存在某种程度的纷乱无序。
无论作为孩子还是作为成人,我们可能经历了众多不同的道德训练,这些道德训练无法轻易地彼此相容。
与此同时,在可能的选项之中,功利主义确实有它的吸引力。由于对手段与目的的问题持经验的态度,功利主义与科学的禀性相符合,它能够灵活地应对变动的世界。
然而,最后这个考虑因素与其说是正当理由,不如说是自我劝诫。
因为如果灵活性是一种劝诫,这都是因为灵活性有它的效用。
✲ 本文节选自「功利主义」,〔澳〕J.J.C.斯玛特,〔英〕伯纳德·威廉斯 著,劳东燕、刘涛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