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2017年4月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届时“北京放映”单元将放映近500部中外佳片。前两天在北京的电影迷朋友肯定都经历了一场抢票运动,1分钟破100万票房,5分钟300万元,15分钟500万,加上“是枝裕和”、“安东尼奥尼”、“速度与激情”套票,总票房已突破600万元,创下北影节新纪录。
我们为什么去看电影?并不是为了高雅艺术,而是为了短暂的逃离。下面的文章选自美国著名影评人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的《垃圾、艺术和电影》( Trash Art and the Movies),在这篇文章中,她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对自己喜欢看的东西感到羞耻。

我们为什么去看电影?
Why do we go to the movies?
作者:宝琳·凯尔
Pauline Kael
译者:爱斯基摩人
我们一般喜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很享受,而这种享受跟我们对艺术的认知并没有太大关系。电影,即便在童年时代,所回应的问题,也与学校和中产阶级家庭代言的官方文化价值观不相同。在电影里,我们体会人生的高潮和低谷,而David Susskind(美国电视电影制作人,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和说教影评人还一边责备我们,面对那些有益的“现实主义”电影时还不领情——比如《阳光下成长》(A Raisin in the Sun,1961),我们应该从这部电影上堂课,那就是黑人家庭可以跟白人家庭一样枯燥乏味。
电影观众会看到大量的垃圾电影,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追求一种正确的电影方法。在电影中我们期待一种不同以往的真相,一些让我们惊讶的、被我们当成有趣或者尖锐的,甚至惊人的东西,也许是惊人的美丽。即使在平庸的电影和恐怖电影中,我们也会有所收获——在1967年的喜剧电影《Enter Laughing》(1967)里美国名演员何塞·费勒(José Ferrer)用稻秆喝酒,斯科特·威尔森在电影《冷血》(In Cold Blood,1967)里的表现。(注释:《冷血》:根据美国作家楚曼卡波堤著名的报告文学拍摄而成。导演采取黑白纪录片式的纪实手法,忠实地观察可以说是一个极其详尽和细腻的犯罪个案纪录。两名冷血罪犯如何在一个堪萨斯州的农家犯下冷血的灭门血案,直到两人被警方逮捕直至处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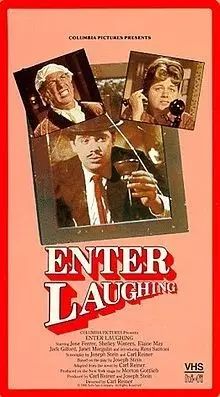
深深印在我们脑海里的,还包括:托尼·兰德尔(Tony Randall)在奇幻电影《博士的七张脸》(The Seven Faces of Dr Lao)中惊讶的表情;基南·怀恩(Keenan Wynn)和莫伊娜·麦吉尔(Moyna MacGill)在《时钟上》(The Clock,1945)坐在长餐桌边上;约翰·W·巴博(John W Bubbles)在电影《月宫宝盒》(Cabin in the Sky,1943)里的舞池上,在《璇宫绮梦》(DuBarry Was a Lady中,1943),金·凯利(Gene Kelly)抑扬顿挫的发表”I'm a rising young man”,还有在《成功的滋味》(Sweet Smell of Success,1957)里,托尼·柯蒂斯(Tony Curtis)说“avidly”。
虽然导演肯定是负责作品的人,但真正让我们起反应,并记住很长时间的,正是电影中的人的行为。表演者的艺术对我们来说永远都很新鲜,他们也永葆美丽。我们从中得到了那么多东西——在《温柔陷井》(Tender Trap,1955)中为宽银幕设计的镜头,在《The Luck of Ginger Coffey》(1964)中,报社的独特气氛。我们需要撒谎吗?就像说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是一个伟大的演员,因为她的表演让她成为一个明星?还是我们认为她是好演员因为她令人难以致信的迷人,而且是世界上最棒的模特?有一些美妙的时刻,比如《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安吉拉·兰斯伯里(Angela Lansbury)唱《小黄鸟之歌》(Little Yellow Bird),没有哪个朋友不喜欢这个小女孩和这首歌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瞬间:在《风尘双侠》(Saratoga Trunk,1945)里,当科特·博伊斯(Curt Bois)对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说:“你很漂亮,”她说:“是的,不是很幸运吗?”这些东西比起老师给我讲的真实和美丽的,离艺术要更近。不是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作品往往不好(就像我们以后经常发现的那样),而是老师教导我们要欣赏的东西,其目的一般是如此虚伪,是美化的和道德主义的,那些其中可能的快乐时刻,纯洁的和颠覆性的东西都被遮盖了。
由于媒介的摄影性质和便宜的入场价格,电影并不是从模仿欧洲的高档文化中吸取动力,而是从偷窥表演、狂野的西部秀、音乐厅、连环画中——都是粗糙和常见的。早期的卓别林仍然看起来令人惊讶地猥亵,包含浴室笑话,醉酒和仇恨。而拔枪射击的西部片绝对不符教师的正统艺术观念——在我的学校时代,更多地喜欢死板的诗歌和“完美比例”的雕像,多年来,又从漂亮的故事转向“好品味”和“卓越”——这可能比布道和小雕像更有毒害,因为彼时你很清楚你要反对是什么,也就更容易反抗。当然那些也正是我们要从电影那里躲开的。
整个星期我们都渴望星期六下午和“圣所”——坐在电影院里,隐匿自我,只是享受,不用负责,不必“好”。也许你只是想看看屏幕上的“那个”人,知道他们不会回头看你,他们不会对你感兴趣,当然也不会批评你。
也许电影中最强烈的乐趣正在于此:它非美学,避开在官方(学院)文化中需要正确回应的责任。而这可能也正是发展审美意识的最佳和最常见的基础,因为带着责任去关注和欣赏是反艺术的,它使我们焦虑于乐趣,无心去回应。
远离监督和官方文化,在电影的黑暗中,我们不被索求,我们孤独一人,从责任和约束中解放使我们能够发展自己的美学反应。无人监督的享受可能不是唯一的,但它可能会是唯一的一种。脱离责任是所有艺术乐趣的一部分,而这是学校无法认可的。我不喜欢为“路演”电影买票,因为我讨厌把电影当成某种场合。我不想提前几天被定死; 我喜欢去看电影的偶然性——当我想去的时候,就去。简单的想看一部电影的心情。
电影中我们体会一种相对自由的感觉,这种自由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意大利式西部片中达到极致。它们摆脱了文化价值的束缚。我们可能想从这种消极美德之外获得其他的东西,但我们非常清楚从童年时那些吸引我们走入影院的东西:赌徒,以及守卫走过时那些傻瓜在旁边嘀咕的脏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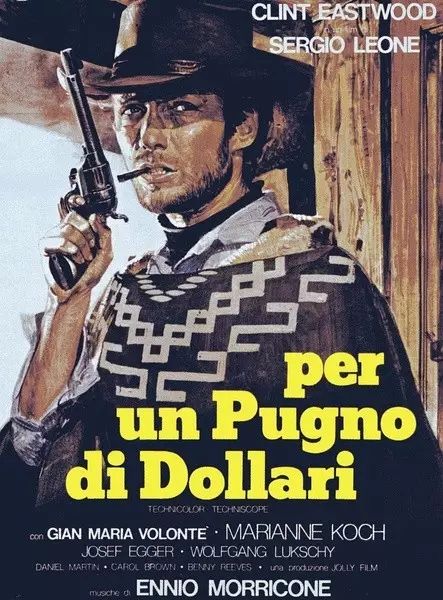
电影的吸引力在于犯罪细节、刺激的生活、邪恶的城市、无情和野蛮的语言;正是城市女孩的肮脏的微笑,诱惑英雄远离那些小公主。什么让我们把电影放在第一位,开启一段别样的、受禁止的或令人惊讶的经历,活力、腐败和不敬,是如此直接和直白,与我们所被教导的艺术相去甚远——后者让人感到安全,似乎看几部外国电影就更有品味。
一个经理告诉我,他很失望,因为他的孩子选择去看《邦尼和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1967),而不是和他一起去看《严密监视的列车》(Closely Observed Trains,1966)。他认为这是缺乏成熟的标志。我认为他的孩子们做了一个诚实的选择,不仅因为《邦尼和克莱德》是一部好电影,而且因为它更接近我们,一些并不直接与我们相关的特质让它变成我们想去看的电影。

但可以理解的是作为美国人,我们认为在外国电影中能看到更多的艺术。艺术仍然是老师、淑女和基金会所相信的,文明的,精细的,经营的,严肃的,文化的,美丽的,欧洲的,东方的:这些都不是美国的,美国电影更加不是。
不过,如果那些孩子们选择了《狂野街头》(Wild in the Streets,1968),相比较《严密监视的列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诚实和带有说明性的选择,哪怕《狂野街头》在某个程度上是很糟糕的电影。这部电影用一种直接的方式打动年轻人,即使很轻率。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是去寻找丝毫的刺激,甚至是少年时期,我们接受成年人的精致的文化标准,如果我们没有丝毫突破“好品味”的冲动,那我们可能并不会真的在意去不去看电影。我们可能会成为时不时看部美国电影放松一下,而当人们想得到更多时,会发现法兰高·齐费里尼的《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1967)色彩多么丰富,多么有艺术感,就像几十年前,他们看到《红菱艳》(The Red Shoes,1948)时的感受,后者的导演迈克尔·鲍威尔, 艾默利·普莱斯柏格是那个时代的法兰高·齐费里尼。
或者,如果他们喜欢从关于腼腆人的异想天开的电影中得到一些舒服的感觉,那么可以去看看类似《富豪之家》(Hot Millions,1968)这类的电影,这类虽然背景是二战看起来却像是在一战。电影观众感到参观聋哑家庭朋友那种体面和美德,这是一种让电影回到教室的方式——变得温文尔雅,老师们和评价家们也开始不停地问,为什么美国不能制作出这样的电影。
作者宝琳·凯尔(Pauline Kael),1919年6月19日出生于美国。非常著名的影评人,在相当大范围内被认可为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影评人。她的特点是诙谐、尖锐、一针见血且固执己见。在1967年到1991年间她为《纽约客》(New Yorker)写作。她的影评写作影响了后来的许多重要影评人,如Armond White和Roger Ebert。
注:如需转载,请注明译言公众号(yeeyancom)和作者、译者、原文地址信息。参考原文: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01/sep/05/artsfeatures.arts

扫描二维码关注译言,获取优质译文资源,享受优质便捷的即时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