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2017余额:121天】
 点击上方
蓝字
,快快关注我们吧
点击上方
蓝字
,快快关注我们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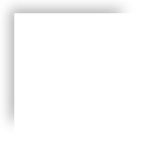
学生
 换汇季
换汇季
02/09/2017 人民币兑英镑
8.53
以上信息由CurrencyCo提供
最新汇率请联系
官方微信: huobi_2015 |
电话: +44 (0) 207 287 7112
从2015年英国第一家中英双语幼儿园横空出世起,庄可为(Cennydd John)和他的这家Hatching Dragons幼儿园就已经分不开了。
相关媒体闻讯而来,不仅以“老外教中文”为吸睛点,介绍了这家幼儿园的独特之处,更是将庄可为本人称为“传说中才有的爸爸”——毕竟,他就是为了让自家儿子以一个更轻松的方式学汉语,才萌发出创办双语幼儿园的想法。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Hatching Dragons Barbican幼儿园的第一批孩子已经毕业,第二家位于Twickenham的分园也在9月初开学。
为了进一步了解他和中国文化之间深厚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作为一名英国人推广中文教育,侨报记者对庄可为进行独家专访。

庄可为在他幼儿园的办公室中
拍摄:吴敬冰
英国侨报(以下简称为“侨”):您为何给自己取名“庄可为”?
这其实是我的老师为我“赐名”。因为John听起来像“庄”,“Cennydd”的发音接近“可为”。由于我本身就对道教很感兴趣,能冠以庄子的姓让我十分开心。“可为”的意思是“有所作为”,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中文产生了兴趣?之后又为什么想要学中文?
为什么不学中文呢?(笑)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学习第二语言。那时是1995年左右,可供我们选择的语言很有限。当时法语最为流行,亚洲语言既神秘又非主流。但我还是选择了学习日语。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开始研读日本的历史和文字——一种唐代时从中文引进的汉字。在我看来,日文在某种程度上是起源于中文的。我因此决定“弃日从文”,也开始读有关中国的书。
2001年,我如愿以偿地考进了爱丁堡大学,学习“现代汉语研究”(Modern Chinese Studies)这一专业。这门课程从某方面来讲非常有趣,因为它就像是历经多年但从未更新过似的,教授的都是些非常古老的内容。
它虽能另我接触不少“论语”,“韩非子”等中国老祖宗们留下的瑰宝,却也同时使我对相对现代的中国一无所知。
所以,当2002年我第一次前往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时,我真的闹了不少笑话。我称大家为“同志”,结果大家都说,我听起来像他们的老爸。

侨:后来您有再去过中国吗?有感觉到什么变化吗?
中国的变化确实太快了,快到几乎不可能让大洋彼岸的任何一家教育机构把相关教材及时更新。我第一次动身前往中国时,心里真的很忐忑——在网上能搜到的相关信息太少,我也只能把一切都往好处想。
但我发现上海其实是一座和教科书里所描述的完全不一样的城市,这让我眼界大开。后来我也去过中国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在2012年,我的儿子出生 。十年前上海还只有三条地铁线,但十年后这座城市变化大到我都几乎找不出熟悉感。
其实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发展速度快,利弊就会显现出来。周围环境的变化,会让人们很容易逐渐迷失,忘记了自己是谁、属于哪里、该干什么。
2010年我住在北京鼓楼,那里有漂亮的传统楼台、古亭、四合院——虽说不够现代化,但有着一种浓厚的历史沉淀感。住在那块儿的大伙天天打照面,邻里间其乐融融。
我知道在目前的北京,这样的地方已经几乎屈指可数了。参天大楼拔地而起,城市居民们都住在一个个小单间里,也鲜少往来沟通。诚然,钢筋水泥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但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要遗忘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和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中国的多样文化,养育了一个个独特的个体。中国的文化一直吸引着我,所以我觉得自己想点办法,把中国“搬”到英国来。

侨:从您把中国“搬”到英国来,建起第一家HatchingDragons幼儿园起,不知不觉间两年就已经过去了,您认为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这期间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师资,也就是打造我心中理想的教师团队。作为整间幼儿园的负责人,我首先是一个管理者。照顾幼童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员工们不仅需要时时刻刻将目光锁定在幼童身上,更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任务——哄孩子入睡、换尿布、日常记录等等。这些都是很繁琐的工作,但我需要确保他们完善地执行每一项工作。
同时,为了让幼儿园整体以最优水准运作,如何照看孩子、如何教育孩子、如何编写孩子的成长纪录等等,这每一项都需要员工们互相协作,保持一致性来进行工作。每位员工的个性、特点、擅长的领域各不相同,这也需要管理者来一一协调。
其次,我也是一个教育者。和中国文化、中文打了小半辈子的交道了,我很清楚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许多十分有意思的传说、故事、寓言,它们都是教育孩子的最佳文本——它们能真正开启孩子的创造力之门。
但目前在幼儿园中,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寥寥无几。所以,我首先需要让员工们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神话故事的精彩绝伦感同深受,让他们也像我一样,提到兴头上了就汗毛倒竖、兴奋不已。在这之后,他们才能够以这股热情进一步地感染孩子们。
同样地,在英国文化的这一方面,我也需要首先带领中国员工更深一步地了解英国文化。这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随着事业的发展,第三、第四分园的开园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我希望招聘更多相关人才。
而若时间允许,我将继续投入到“教育”这个本职上去:通过这些年当“中国通”的经验,以及作为英国人的本土优势,整理编创出最适合孩子们学习的中国文化小故事。
山海经、关羽也好,亚瑟王、格林童话也好,正是这些有趣的故事,这些可以不断增加不断丰富的内容,才是HatchingDragons幼儿园最大的竞争力。

侨:似乎在幼儿园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家庭的孩子们?
是这样的。我见过不少完全不会讲中文的British-Born Chinese(英籍华裔)小孩,他们几乎已经失去了与中国之间的关联。但他们的父母还是很渴望孩子学好中文,借此留存一丝和中国的牵连。
我觉得语言和文化认知是紧密相关的,因而生活在英国的外来家庭中,不同年代成员间产生文化差异也是在所难免。
当中国家长将自家孩子放置于一个英文环境中任其成长时,他们就应该预料到孩子逐渐西化的未来。
但有方法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吗?有的,让他们在双语学校接受教育,不分国籍、不分信仰、不分皮肤的颜色,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可以接触两种文化。
即便他们已经在文化认知上将自己定义为西方,这也不代表他们不再会为中国文化而触动——就像金发碧眼的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一样。我希望家长们明白,如果孩子认定自己属于英国,就让他属于英国,这并不会妨碍他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反之亦然。

侨:英国政府现在正大力鼓励年轻人学习汉语,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号召?
是的,现在有很多英国人开始学习中文了。不过确切地说,政府是表示,学校可以选择开设中文教育项目,而不意味着“必须开设”。
从学校的角度出发,如果学校希望学生取得好成绩,那校方势必不会冒着风险雇佣他们并不熟悉中文教师,来教授学生一门出了名难学的外语。
目前只能说,将中文列入教学大纲是值得称赞的第一步,但想改变现状,这还远远不够。
前几年政府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2020年前培养出超过5000名能够流利使用普通话的英国人才。
然而,至少在我看来,新任领导班子在对移民政策紧缩的同时,也降低了成功培养中文人才的可能性。如果政府不及时调整、放宽相关签证政策,这些真正的汉语人才,都只能被拒之门外。
我也参加了该计划的现场发布会。当时我问教育部的工作人员,为了填补中文技能的缺口,政府有哪些具体的措施?毕竟,同时拥有英国长期居住权及良好中文教学能力的人才并不多。他们的回答居然是——“我们希望有更多英籍的中文技能者来担起这一重任”。
然而,全英上下究竟有几个能讲流利的中文、同时还拥有教学资格的英国人呢?在我的反问之下,他们沉默了。
所以,政府的用意肯定是好的,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采取一些其他行动。在我看来,有一点毋庸置疑,中文教育得从娃娃抓起。若政府能重视早期双语教育,那么五周岁左右的孩子们是有能力掌握基础中文。
若这些对中文、对中国文化燃起兴趣的小家伙们都向校方要求继续学习汉语,校方也一定会随之改变自己学校的课程设置。从这个角度讲,我创建HatchingDragons幼儿园的初衷,也就是希望自下而上地促成对英国小学乃至更高层中文教育体系的改变。

侨:关于中国文化在英国的推广,您有什么建议吗?
关于文化推广,我想用美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来做为例子。美国文化以流行音乐、电影、小说等等为载体,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人们会花大量时间听美国音乐、看美国电影,主动了解美国,我觉得这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再以英国为例。我听说不少人只是凭着一腔对哈利波特的喜爱,就决定只身前往英国旅游或者学习。
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让我们这些“歪果仁”一听一看一了解,就能为之兴奋,萌发兴趣,进而想要深入了解的东西呢?
我们Hatching Dragons幼儿园现在所做的,就是将多面的现代中国,展现给英国的下一代,激发他们对于中国的兴趣。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在接触这些神奇的故事后,不会对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产生浓厚的兴趣。
只是我一个人的力量相当有限,但若能有更多人、更多组织致力于向西方介绍普及中国的“软实力”,我相信中国文化在英国的推广一定能越做越好。
(本文作者吴敬冰;文章翻译、整理自被访者口述,并不代表本报观点。图片由受访者供图,转载请注明
作者
和
出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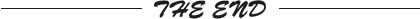
官网:http://www.ukjs.net/
微博:英国侨报
This news is sponsored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