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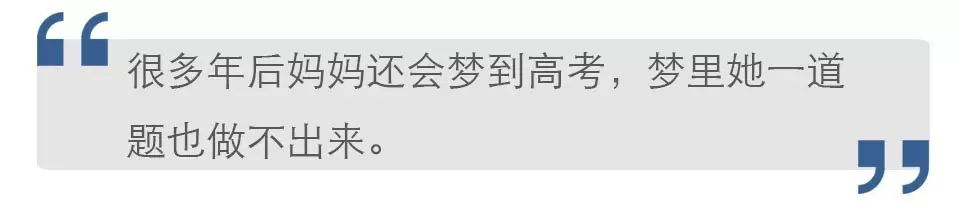
某天,有个媒体朋友在微信里寻找
1977
年的高考考生,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他们要做一期讲述高考故事的节目。我说我认识,就是我妈,但是她没考上。然后那个朋友发给我一个流汗的表情,意思大概是“哥我忙着呢,你和我逗闷子呐?”
后来他们的节目推出了,很多其他媒体也都推了类似“我的高考故事”的栏目。但这些故事看来看去,都只有成功者的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似乎叫“我成功的高考故事”更合适。毕竟考虑到当时较低的录取率,忽略庞大分母的高考故事,是有所偏废的。
如果我们去关照一下那些没有跨过高考龙门的人,以及他们后来的人生故事,也许能更全面地理解社会局势对个体命运带来的决定性影响,才能更全景地回望一个时代。
我妈的故事是这样的,她考了两年,都因几分之差没有考上,于是回到生产队务农,后来嫁人,最终成为一位怀抱遗憾的农村妇女。后来她总是梦到考试,别人都交卷了,只有她一道题都做不出来。
一直到我十几岁都还听她回忆这样的梦境。一考定终生,对那时候的女性显得格外坚硬无情。
如果时代再晚十年,录取率再高一点,也许她后来就不至于沉浸在遗憾的梦境中了。
所以当我读到媒体那些对高考的感恩故事时,更能理解我母亲的执念。其实这些感恩和执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如果改变命运的路只剩下一条,它当然会变得异常瞩目。
我不觉得这需要被感恩,感慨一下足够了,可能反思更为必要。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人们缅怀四十年前的一项重大政策改革,因为它真实地改变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对此,有这些诚挚的感情可以作证。
我发现代际差异这种划分真的是所言不虚,当朋友圈那些
60
后在感恩高考的时候,
80
后却在纷纷转发一个段子:祝考生们努力拼搏,但四年后你们会明白,改变你命运的主要还是酒量、胆量、颜值,还有你们村是不是拆迁。
段子这种亚文化博人一笑之余
,
往往在荒诞之中却也传达着些什么。
“我的高考故事”里,
77
年考生笔下的大学生活流露着一种瘦硬清新的气象,物质简朴但意气风发,个体命运已改变,他们信心满满要改变国家。而我的大学生活似乎没有这种气质,我记得刚上大学时,校园中最流行的口头语是“郁闷”,虽然谈不上颓废,但满满的都是不振奋。与之相伴的是歌手朴树忧郁哀伤的《那些花儿》。同学里,印象较深的是两个大一就退学的,记得其中一位叫王大强,四川人,从一入学就沉湎于打游戏,几乎就没有上过课,后来终于被学校劝退。另一位同学从入学军训时就表现出举世混浊我独清的孤傲,大概觉得穿统一发的军装太泯然众人,竟别出心裁自己搞了一套裁剪精致的服装。后来他认为这个大学让他失望了,愤然退学复读。
两个性格乖张的学生,当然无法代表一代大学生的风貌。但这其中的问题是,面对高考,人们的态度从昂然变得况味复杂起来。虽然整个考试仍然具有隆重的仪式感,但叩拜者的信仰已经不那么虔诚了。前几天和大学舍友吃饭,他说当初不应该去读研究生,早三年工作说不定已经在北京买房了。过了一会,又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感觉自己工作太忙好久没读书了。没有读研究生,但依然在北京无房的我,默默飘过之余不禁想到,这也许正代表了当下人们对高考的全部态度:
一方面仍然尊重知识的神圣性,对于书籍这种知识的古老载体怀有由衷的敬意。而另一方面,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条则开始有些犹疑。
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
提供了更丰富的改变命运的机会
,
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也更大了。对高考的揶揄
,
或许正是对社会进步的侧证。
漫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出身成为人们冲不破的顶棚。“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于是隋唐振刷制度,科举应运而生。它让人们看到一种确定性,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有才能,就能改变命运。
四十年前重启高考
,
与科举当然完全不同
,
但是它同样给无数寒门子弟提供了一种允诺
,
提供了梦想以及实现梦想的机会
,
也给国家的振兴提供了人才保证。
那天看媒体报道毛坦厂中学的陪读现象
,
其中有一张母亲给孩子送饭的照片
,
又让我的小资情调沉渣泛起。记得高考成绩公布后
,
姥姥跟我妈说了一句
“
没白费了每天辛苦做饭
”
。无数的母亲在厨灶间的费心打点
,
在考场外的翘首企盼
,
都是缘于对这份允诺的信任。四十年后
,
人们仍然怀念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
,
因为人们对伟大改革的期待
,
永远热烈。
(文/于永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