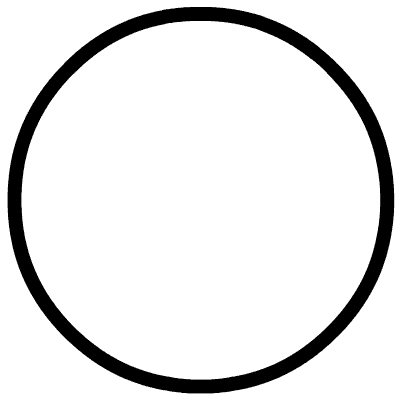作者 | 侯明明 编辑:学妹

我的嫂子,也许可以不为过的说,在我从小到大的过程中,隐隐约约有精神的指引作用。她和我哥哥结婚后就外出打工,虽然后来得知他们在某个城市里摆摊卖书,但是相对于九十年代落后、贫穷、封闭、无知的农村乡下放羊娃来说,那已经是非常新潮、时尚,充满好奇感、新鲜感以及诱惑力的。
每次逢年过节,嫂子回来以后,我都会急匆匆的、充满期待的跑到他们屋里寻求一种外来物品的冲击感,这种外来物可能是一本没有见过的小人书,也可能是一支想都没想过的玩具枪,更可能是嫂子给我讲时尚的“城市方言”。嫂子时不时的甩出两句,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爽朗的歌声不断撞击泛黄的草坯房,又萦绕在耳畔,久久才能散去。

这样一来,哥哥嫂子回家便成了我心中最大的希冀。
从他们走后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数着过去的日子,那时候也许对数字不是很敏感,也或是年幼童真,每天一本正经的翻着挂在墙上的日历,一开始妈妈把日历挂的有点高,就央求妈妈把日历挂的低点,每天翻看着那一页页泛黄的日历,心理充满了期待的喜悦。
这种期待连续循环了几个春秋,直到某年的一个暑假,嫂子突然从城市回到了农村,直接问我愿不愿意跟她去城里呆一个暑假,我顿时就像《海上钢琴师》里的男主角一样,又是欣喜又是忧虑,欣喜于对城市里的期待,却恐惧于城里环境的陌生,一张“无知之幕”挂在了我的眼前,向前一步是不知下的期待,向后一步是退却下的不甘。我是否能够通畅的和城里的孩子沟通交流?他们会不会鄙视乡下人的无知与没见过世面?一系列的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只感觉一股向前和一股向后的劲在那里较劲,弄的自己全身上下不知是喜悦还是痛苦。嫂子见我犹豫了,就开始说,城里有各种游乐场、大超市……来吸引我的注意,再加以爸妈的怂恿,我最终决定还是跟嫂子去城里转转,体验一下嫂子、哥哥的城里生活,感受一下城里人的日子过法。
那年模糊的记得,
自己好似7岁
。

之后,嫂子城里的生活被我看的一览无余,那种神秘感顿时苍白乏力。
其实,嫂子和哥哥一直在城里路边摆摊卖书,也是城市里较为底层的生活,依然生活不易。还时不时的与城管做游记斗争,万一哪天消息不灵通,很可能把所有的家当都搭进去,但是我没有听到嫂子的一句怨言,只是认真在做。
记忆最深刻的不仅仅来自于朱自清笔下的父亲《背影》,还有嫂子骑三轮车带我去卖书的弓背,也许今生难以忘却。
嫂子身材瘦弱,却有一股大劲,几百斤重的书,外加一个我,上坡的时候,都不叫我下来,自己闷声把“我们”拉上去,显得“轻车熟路”。
卖书时,中午吃的是盒饭,两个菜,一份米饭,对我来说已是非常满足。嫂子却不满足于此,趁着吃饭的机会,偷偷带我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赏鱼,哇,哇,0型的小嘴一直喊个不停,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五颜六色的金鱼,虽然在农村也经常到村后边的河里抓鱼,对鱼的种类也是非常熟悉,但是这次我被迷倒了,眼花缭乱,完全没有见过。欣喜若狂的我,开始伸着小指头点数,“一、二、三……”“嫂子,我数到哪里了,他们怎么又游回来了……”看着我那股认真劲,嫂子摸摸我的头,笑着说,“傻孩子……”

和嫂子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特别是晚上去广场上看歌舞表演,嫂子常常边看边对我说,“
咱们农村人以后就应该吸收点城里人的文化熏陶,人活着得有点追求,有点个性。
”我那时,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只顾上看节目了,却也没有真正体会到嫂子的用心。
快乐的时光总是匆匆,转眼暑假就要过去了,一切还是需要回归,回归那个平静、平常、熟悉的乡村。
回到乡村,期待嫂子的再次回家。
仍然数着日历,仍然充满期待。但这一份期待不再仅仅是清单里列举的外来物品,而是嫂子那份恬淡的笑容以及她带给我的那份舒心。可惜的是,在记忆中,却有好几年没有嫂子的印记,后来问起长辈,妈妈才提醒我,那几年嫂子一直没有回家过年。
期待的日子过久了,或者是造成期待的疲惫,或者是日积月累之后的历久弥香。高一那年,终于爆发了,嫂子说她要和哥哥回家过日子。我听到后,先是欣喜,却不知也有哪来的顾虑。
一番谈话之后,才知道,其实,自从我上初中以后,嫂子的生意一直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做此类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市场的需求却渐渐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城市市容管理越来越严格,经常东躲西藏,那根本不符合嫂子本性之欲求。这么多年来,嫂子一直苦中做乐,一边读书,一边卖书,还一边观察社会的千姿百态,但是现在这种求生存与生活的样态的欲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再加以嫂子觉得孩子和自己的年龄也都大了,自己身体吃不消,孩子也要上学,户口、医疗、教育等等问题都需要解决,未来并不是很确定,综合各种原因,权衡各种因素之后,嫂子决定回家。

回家之后,以嫂子那灵活的头脑,肯定会大干一场。
她用积蓄买了一辆六轮的汽车,和哥哥一块跑运输,做各种生意,物质方面日益优越,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为后来的嫂子自杀埋下了重要的“隐患”。
我自上高中以后就在县城住校,每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会和嫂子聊天,但是有时候时间不一定合适,可能我回家的时候,嫂子不在家。特别是我上了大学以后,在外求学,这种矛盾就愈加凸显。一年中,也就是过年的时候,能见到嫂子一次,但是令我惊讶的是,长时间未见面的我们却如遇故友,相谈甚欢。嫂子虽身在农村,心却早已飞出农村的边界,再加以做生意时的东奔西跑,积累了不少的社会经验,我们的话题越聊越多,真感觉不出嫂子是小学毕业的。嫂子是经历过人生百态之人,你问的问题哪怕是老生常谈,她总是能给出你意外的惊喜,那份答案不是长辈们标准的“答案”,而是带着勇气、创新、惊喜与个性,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着我的大脑皮层。
嫂子回来后,最让我难忘的是嫂子染了一头的黄发。在当时的农村看来根本没有哪个儿媳妇敢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黄毛”,彰显出如此张扬的个性,但是嫂子却做了。有时候回家,也会听到邻居拿嫂子的“黄毛”开玩笑,但是嫂子却玩笑似的回应“玩笑”,就这样一笑而过。我其实知道,嫂子有一颗个性的心,她希望用自己的艺术作品来表达对生活的理解,但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她压抑了自己很多年。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她想逐渐的把自己曾想做的事情一一表达出来,完成自己曾经那份热切的期盼。却不知,农村的环境是一个相对封闭、相对传统、相对世俗的世界,一点新鲜的东西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接受,而且还要牺牲某些莫名的代价。笑声背后除了应付之外,还有不可理解的无奈。

我知道嫂子喝农药自杀是在她去世一个月之后,那时我大三,因为正在准备考试,母亲为了不打扰我准备考试,没有告诉我嫂子因喝农药住院的事情。
考完试,才知道,嫂子已经离世一个多月。说实话,我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怨恨母亲,为何不早点告知我,也许我和嫂子还能见最后一面,也许嫂子还有很多话要和我说。母亲平静的说,嫂子那时候已经因农药的伤害,无法进食,胃部也开始溃烂,不是我们不想告诉你,是你嫂子想保留她在你记忆中的美好形象……我听后,眼泪夺眶而出,又回到了那个数金鱼的中午,不过这次是我摸着嫂子的头,“傻嫂子……”
后来,我无数次的想象,假如我真正见到嫂子最后一面,我会说些什么……
嫂子喜欢嗑瓜子,冬天坐在火炉旁,一手握着瓜子,同时又与另一只手剥着瓜子,一捏,一开,抛向嘴中,动作熟练……愿在天堂延续……
本篇回忆录写于笔者准备考博期间,恰好是嫂子逝世4周年,又因拜读了陈柏峰教授的《价值观变迁背景下的农民自杀问题》,读完之后,在感慨农村自杀率之高以及让人心痛之余,回想了自己的亲人——嫂子的自杀离世,虽已近而立之年,但泪水还是夺眶而出,久久不能平静。虽然早有写文章纪念嫂子的想法,但一直不敢动笔,这次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涌动,提笔急速。但终因几度哽咽而不得不停笔整顿情绪。不知为何,曾经的美好回忆却让泪水更加澎湃。亲人逐渐老去逝去,心中滋味乱绪,特别是一介书生的无能与无力,更是让自己常生责备之情和苍白之感,也许谨以此篇小文纪念嫂子的过去种种,也许从学术原理角度阐释悲剧的缘由,不让现世人悲剧重演,才是吾辈努力和贡献之处。
嫂子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个如此乐观、家境殷实、经验丰富的人怎么就突然间离世了,而且是自杀,让人很摸不着头脑。也正是因此,我在求学的生涯当中,对死亡、自杀抱有长时的思考。
现在农村自杀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城市里的自杀也不亚于农村。对于其原因的探究,大多数答案也是模糊不清或者是老生常谈式的从经济、家庭等因素入手,而没有找到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原因。甚至让我想起了海子、海明威、三毛等著名作家、诗人,他们的自杀多少都是与知识分子的气节、气质有关,那么嫂子的自杀是否也与之有关呢?
▷作者:侯明明,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司法文明理论
▷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
推荐阅读:
你的宿舍住了个什么鬼?
为什么读了很多书,却学不到什么东西?
学术中国研究方法奖助学金(征求意见稿)

诚意推荐 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