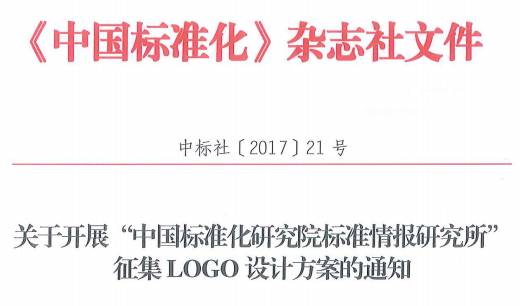城市经济系统区别于乡村经济系统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往往具有架构更加复杂、体量更为巨大的工业生产。对于古代城市来说,这一点也是相似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昊老师通过对于周原云塘制骨作坊的发掘与研究,探明了这座西周王朝最重要的都邑性聚落制骨手工业的规模、技术和运作方式,为我们深入和全面了解西周时期的生产技术、产业体系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古代社会基础经济系统的研究打开窗口。9月12日晚,我们邀请赵昊老师作题为“小本买卖:西周都邑中的骨器经济”的讲座,敬请关注。
城市经济系统区别于乡村经济系统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往往具有架构更加复杂、体量更为巨大的工业生产。对于古代城市来说,这一点也是相似的。即使在以手工生产而非机器生产的古代社会中,一座大型中心性城市内部的手工业产业的规模、技术和效率,也直接反映着这座城市的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水平。因为手工业生产不仅仅涉及技术本身,同时也涉及生产的组织形态、管理机构、协作与竞争等更为复杂的社会过程。因此,对于周原这座西周王朝最为重要的都邑性聚落的手工业体系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更深入和全面了解西周时期生产技术、产业体系等问题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自1976年考古学者展开对周原遗址的科学发掘与研究以来,在周原都城遗址区内,已经发现和确认了一系列的西周时期手工业活动遗迹和遗物。尤其是在周原遗址的核心区,发现了多处生产规模极其庞大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所涉及的生产类型多样,目前已知的生产类型包括铸铜、制瓦、石玦、漆器、角镞等,其中云塘制骨地点也是具有相当规模的重要产业类型之一。
云塘制骨地点位于周原遗址的中部,南距周原齐家村约700米,西南距云塘村约300米。从聚落历时性变迁来看,该地点位于西周早期的周原都城中部偏东,位于西周中晚期都城的中心区。当1976年在周原遗址进行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时,考古队即对该地点进行了尝试性考古调查和发掘。此次发掘所得的考古材料极为丰富,在350平米的发掘范围内,共发现了超过10吨的各类用于制骨生产的动物骨料。这些动物骨料上都带有明显的人工加工的痕迹,反映出云塘地点在西周时期是一处以利用动物骨骼生产骨器为主的手工业作坊。此外,1976年的发掘中还发现了19座西周时期的墓葬以及少量简单的建筑设施残留。可以说,1976年在云塘制骨作坊的考古工作,是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对周原遗址大型手工业作坊类遗存的正式发掘和研究。但是,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这次的发掘以及后续研究中也存留下了不少问题和遗憾。2014年周原考古队对云塘制骨作坊遗址进行了再次勘探和解剖性发掘。在此次20平米的发掘区内,共发现各类动物骨料约2吨以及其他丰富的考古遗存。通过2013-2014年的周原遗址大规模区域调查和钻探,也同时基本明确了制骨作坊区范围内骨料密集堆积范围约在40000万平方米左右,生产的持续年代从西周早期开始,贯穿整个西周王朝时期。
在原料方面,云塘制骨作坊所使用的主要动物骨骼来自于黄牛。黄牛的比例占到了所有动物比例90%以上。主要使用的部位是黄牛的长骨,也就是四肢骨。相比于其他中小型动物,黄牛肢骨的骨壁较厚,骨干较长,有利于生产出更加高质量的骨器。云塘制骨所使用的骨料在年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简化,集中使用2.5-4岁左右的牛骨。动物种属和年龄结构的简化,意味着骨料的形状和尺寸会基本统一起来,因为每一种动物的骨骼一般都是相似的。对于生产者来说,种属的集中等同于原料外形的简化,而年龄范围的缩窄意味着原料尺寸的简化。在生产工具方面,云塘西周制骨作坊所代表的青铜时代骨器制造,最重要的基础技术特征就是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特别是青铜锯的大规模使用。在云塘遗址出土的几乎所有动物骨料上,都能明显地观察到被金属锯加工的痕迹。相比于石器时代加工骨器时常用的石刀以及青铜时代早期所使用的青铜刀斧等工具,青铜锯的应用能够将加工过程的可控性大幅度提高。因为相比于刀斧猛烈的砍砸动作,锯子的运动更为精确和稳定。这使得西周的工匠在制作骨器时能更加准确地控制加工结果,并且保证所生产骨器具有更加平整、干净的表面结构。
云塘制骨作坊的主要产品类型是骨针和骨笄两种。这两种产品的基本形态都是长条形,这也是动物骨骼最适合做成的产品。骨针是西周最常见到地有关制衣缝纫的工具。虽然西周已是青铜时代,但青铜针的使用却很少,人们在缝制衣物时所用的针主要还都是骨质的。可以说,骨针是当时制衣的必须品,具有很大的需求量。另一类主导产品则是骨笄,骨笄是一种安发器物,类似于后世的簪子,主要用来固定发髻和装饰。对于西周时期的人们来说,由于当时人们的发型主要为束发,因此不论男女贵贱,都需要至少一根骨笄来固定发髻,在一些女性墓葬则发现了一次使用多根骨笄进行发型装饰的情况。所以,骨笄对于周人来说,也是一种具有较高需求量的生活必需品。西周社会对这两种产品的稳定需求是大型制骨行业存续的根本动力,而其制骨业的最终衰落和被替代也很可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从考古材料上看,这两种产品从人们的生活中丧失显著地位的时间基本相同,基本都在进入铁器时代后一段时间的公元前300-200年左右。这也与制骨行业整体的衰退同时。从考古发掘品来看,骨针逐渐被铁针所替代,而骨笈则让位于各类金属发簪。高级贵族的选择则全面偏向贵金属和玉,尤其是贵金属发簪。冶铁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以及冶炼其他金属成本的下降(铜、银、金),使得对于骨笄的需求量减少了。最终在汉代以后制骨工业逐渐萎缩为一个以制作工艺品为目的的较小的生产部门。
根据我们对生产流程的复原分析,工匠们在云塘制骨作坊主要进行的工作就是生产以上这两种产品。当一根完整的动物骨骼被运输进入作坊后,工匠首先会锯掉骨骼两端的关节部位。而后,将中间的骨干部分再逐次锯出长条形的坯料来。西周时期骨笄的主要形态,剖面为菱形和圆形两类,而刚刚锯出来的坯料则都是长方体。因此,工匠们会用金属锉将坯料锉成相应的雏形,然后使用磨石将坯料打磨成理想的成品骨笄。在此之后,工匠还会对骨笄进行进一步装饰,主要包括抛光、钻孔、雕刻、镶嵌等。工匠会在一些骨笄上钻孔后,镶嵌极小的绿松石片或金箔,有的骨笄则会被雕刻成更加精美的凤鸟形后再进行绿松石镶嵌。
西周时期周原制骨作坊在生产管理体系上也引入了全新的方式。云塘西周制骨作坊在生产中最鲜明的特点便是开始引入标准化生产模式,从生产工序到产品规格都纳入了一个明确的标准流程之中。工匠在加工动物骨骼时,都在严格遵循统一的生产设计模板和尺寸标准。这一点反映在考古材料中就是特定骨料形态的高度重复性。在发掘的所有骨料中,往往会发现大量外形和尺寸相同的生产废料,其加工的标准偏差一般在10%左右。这个偏差数值在一般不使用精确测量工具的情况下是所能达到的较高的水平。正是由于采用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云塘制骨作坊的产量和效率都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运行。根据我们的统计,2014年发掘中所出土的牛骨至少来自于826头牛,而由于加工流程基本固定,每头牛基本能产出60-70根骨笄,这就意味着工匠可以用这近千头牛的骨骼最终生产出约50000件骨笄。而这些估计仅是在2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所得到的数据。这些庞大的数字显示出云塘制骨作坊巨大的产能,也意味着大型制骨工业在整个周原都城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比重。
作为一个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实体,与任何其他经济部门一样,制骨作坊的正常运作要求它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社会再生产活动进行互动。作坊内部的管理是一个微观系统,相对而言,横向的行业间合作则是制骨作坊(更广义的说,制骨行业)在宏观层面的运行。那么,云塘地点如此巨大规模的生产在宏观层面是如何维持其长期的稳定运行的呢?换句话说,我们如何以考古学角度走出作坊,在更大的城市范围层面来观察制骨工业。制骨业的存续要求一系列的外部支撑,包括可用的原料,适手的工具,以及合理的配套基础设施和流通渠道。在西周这个已经成熟的国家体系下,还需要土地、资源的权利。可以说,作坊存在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也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关联的运作机制,使我们可以通过结合作坊内外的考古遗存,对周原制骨手工业所涉及的整个经济体系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首先,云塘制骨作坊大量地使用牛骨来生产,那么这些牛来自于何处呢?是周原本地饲养的产品,还是从其他地方输送而来?对于动物来源问题的考察可以将制骨工业原料获取追溯到上游的动物畜牧业领域。畜牧业也正是动物经济网络中的最基础元素。为了解答整个疑问,我们尝试了使用锶同位素的手段进行考察,通过分析动物骨骼和牙齿中的锶同位素含量的比值来分析一头动物的饲养地点和死亡地点的差别。一般来说,动物牙齿中的锶同位素能够反映出这头动物的出生和饲养地点,而动物骨骼中的锶同位素则往往反映了动物的死亡地点。如果两者的锶同位素值接近,则表示饲养地点和死亡地点基本相同,反之则代表饲养地点和死亡地点不同,那么就存在迁徙或运输的可能。
我们对云塘地点不同种类的动物的骨骼和牙齿的锶同位素含量分别采样后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动物骨骼中的锶同位素含量都非常接近,这说明它们的最终死亡地点都是相近的,也就是都在周原遗址。而牛的牙齿中的锶同位素则完全与其他不同,都在这个本地值的范围之外,这恰恰说明了云塘制骨作坊所使用的牛,都是从其他地方被运到周原遗址的,而不是在本地生产的。如果我们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周原城市存在这样一个动物经济的体系。它从畜牧业开始,而后进入屠宰阶段出产牛肉。除此之外,牛还带来了大量的多种类型的副产品,如骨,皮,角。从生产链条的角度来看,制骨工业实际上是在使用肉类生产的废料进行再加工。
除了原料之外,维持云塘作坊如此规模的生产,还需要一系列其他工业部门的协作。比如,青铜铸造工业要为云塘的工匠们提供充足的、适手的工具,因为如青铜锯这类工具的损耗是非常快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制骨所用的青铜锯在形态、机械性能方面都不同于加工其他材料的锯子(如木工)。从云塘地点发掘出土的若干青铜锯反映出,青铜铸造业专门为制骨行业设计和生产了特别的青铜锯。为了加工骨骼这类较硬的材料,他们铸造了带有更小的锯齿和更窄的锯身的锯子,这样就能保证青铜锯在制骨工匠的手中能够更顺畅地切割骨料。
周原的繁荣,不仅仅是建立在农业生产扩展的基础上。云塘制骨作坊所生产的产品的最终流向也很可能超出了周原都城本身的范围。云塘制骨作坊的生产在性质上很可能是一种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产业,因为其产量远远超过了作坊本身对于骨笄的需求量,且产品集中在骨笄、骨针等少数几个类别上。这种一般日用品生产的商业化,暗示手工业生产对西周社会财富的生产和流动已经开始起到重要作用。周原这种大型城市正是依靠其庞大的手工业生产能力,发展成为西周时期最繁荣、规模最大的王朝中心。周原作为超地区中心性聚落,并非只是政治和宗教活动的中心,该地点存在多样化的高强度经济活动。就城市经济本身而言,大规模的制造业和相关可能存在的交换活动已经成为维持这些大型城市运作的根本。而在西周时期,王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高度重合,也成为了周王室在庞大的分封体系下能够维持领袖地位的社会基础之一。周原王室直属都城大规模手工业是周王室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它们在西周时期的持续繁荣是王室维持其超越于诸侯力量之上的物质基础之一。虽然王室的直属领地不到西周王朝领土的一半,但中央政府的权威仍得以在长时间内维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构成了周王室被迫东迁后王室权威急速衰落的原因之一。周人的撤离,意味着周王失去的不仅仅是渭河谷地肥沃的农田,也还有大型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完整庞大的城市经济系统。而恢复这一更为复杂的城市经济的系统,其难度是远高于单纯的农业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