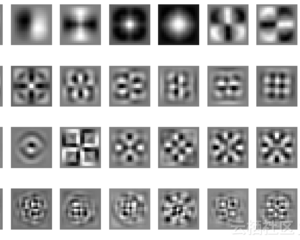王长军
:新公司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无需公司的同意。有观点认为:“如果股东认缴出资期限未届至,也未实际出资,转移股权可能导致出资义务一同转移。此时属于债权债务一起转移,公司不仅有得到通知的权利,而且有同意与否的权利,此时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取得公司的同意。”该观点是否正确?
李建伟
:不能这样理解。
叶林
:在有限责任公司范围内,关于是否是债权债务转移,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林一英处长已经撰文写过,可以参考。对于是否应取得公司同意,我的意见与建伟或许不同,我向来主张,公司意思的加入(非债务加入上的加入)涉及公司对章程及其限制的解释,也涉及变更股东名册。最为典型的是公司章程限制了他人受让股权的约定,理应得到尊重。至于此时是否叫做“公司”同意,在解释上要稍微慎重些。
王长军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有限制,要求取得公司同意,自然按照章程的规定执行。如果章程对此没有限制,还需要公司同意的依据何在呢?
李建伟
:我一直主张,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自由乃是原则,转让后通知公司(股权的义务方)即可,无需公司同意(类似债权转让);即便公司章程设限,股权转让行为(协议)违反之,公司也就是主张转让不对自己生效(比照民法典的债权转让,以及债权转让受限的债权转让),或者对于转让行为(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但都不能理解为股权转让本身需要公司同意。
程浩
:未到期转让的,原股东要承担补充责任。也就是说,无论转让多少次,原股东都不能免除责任,因此,没有必要限制原股东转让股权。
邹宇
:有了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通知公司意义不大,反正初始股东有补充责任。而且,所谓公司反对转让,应作何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依据新公司法第八十四条,其他股东30日内不答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已经无需经过其
P105
他股东同意;公司意志又从何表达?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股东意志通过议事程序才形成公司意志,而不能将法定代表人个人反对股权转让认为是公司意志反对转让。
李志刚
:1.股权转让是跨越组织法与行为法的特殊交易。2.只要明确这一点,就不能简单套用合同法上的债权转让与债务转移的一般规则。3.公司在这个交易中是主体还是客体,还是既是又是、既不是又不是?
我理解,在股权转让交易中,公司的角色是客体。
套用民法上债务转移的观点,不仅没有公司法上的依据(组织法特点),而且可能会陷入一个怪圈。
假如,要求必须经过公司同意,那么,这时候谁代表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吗?股东会吗?董事会吗?如果说绝大多数公司都有控股股东的话,实际上就变成了要经过控股股东同意,因为无论是法定代表人,还是股东会、董事会都是控股股东控制的——他不同意怎么办?永远不能成为股东、永远不能过户、永远干瞪眼吗?
还需要考虑股东购买或者公司购买吗?都不需要。
因为,在这个交易中,公司不是交易主体,是交易客体,交易结果承受者,不是交易结果审批者。否则,就变成了公司(事实上是法定代表人或者控股股东)不同意,合同就永远不生效、履行不能?如果真有这么厉害的效力,那公司法早该写进去了,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应该是公司法立法的重大疏漏。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要高度重视公司法上权利义务的法定性;特别是生成义务与责任的时候,要特别慎重。
另一个问题是,出资义务的完成与股权转让“公司是否同意”,可否捆绑?如果把出资义务理解为法定义务的话(事实上也确实是),可能也无须捆绑。
朱慈蕴
:股权转让与债务转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股权可以自由转让,但债务转让要经债权人同意。
公司同意,由董事会决定,因为这是公司债务转让,与股东无关。公司同意债务转让,可能要负责。股东若要顺利转让股权,最好能先解决该债务问题,比如提前缴资(偿债),或者请受让人承诺届期一定缴资。总之,瑕疵股权转让者要想办法解决债务问题,要让公司接受债务未来可期。现在的瑕疵股权转让以股权转让为借口,完全无视公司这个债权人的意思,违反债权债务对人效力的基本规则。
王长军
:旧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要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而新公司法第八十四条明确废除了其他股东的同意权,旨在减少股权转让的束缚,故转让未届期的股权需取得公司同意的观点,缺乏依据。
黄辉
:同意朱老师将股权转让与债务转让分开的处理思路。就债务转让而言,在民法上,如果债务人在转让债务时为债务提供担保,还需要获得债权人同意吗?如果转让人需要承担补充责任或连带责任,行不行?前面邹法官已经说了,增加了出资主体(转让人加上受让人),对作为债权人的公司还更有利了,可以找更多的人要求出资。因此,从债权人保护的角度看,似乎并不需要公司同意。至于尊重有限公司封闭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等方式解决,这个是股权转让的问题,不是债务转让。
债务转让的问题应该主要是出现在认缴制下,这里的债务就是未缴出资,但是,不能简单地因为这个问题就抛弃认缴制,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类似于因噎废食。认缴制的优势在于给予股东的自由选择权,认缴的股份在转让时确实交易成本会高一些,比如没人愿意购买或要求折价,但认缴股东在选择认缴时会充分考虑这点,如果觉得成本太高,可以选择实缴,这个决定最好交由市场主体去做。
吴建斌
:黄老师意见的立足点似乎假设认缴股东均为理性经济人以及诚实守信人,而我国有限公司包括非公众股份公司,实际营运情况要复杂得多,借假他人名义设立大量无实缴资本、无具体业务、无从业人员的新“三无”公司打“一枪换种玩法”并频繁转让股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往往害得一般债权人无从维权,传导效果势必会阻碍正常交易,同时也约束了正常投资人的投资积极性。虽然实缴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起码能部分改善放任限期认缴制的负效应。
黄辉
:吴老师说的“一般债权人”是指公司债权人吗?如果是的话,认缴的原始股东照样可以玩消失,转让的话,还多了一个受让人,债权人能够维权的对象还更多了,不是更好吗?就认缴股东而言,只需要假设他们是理性经济人,不用假设是诚实守信人。要是都诚实守信,就不需要法律了,法律的出发点就是假设这些人都不诚信,从而通过法律机制去迫使他们遵守规则,比如,转让人的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就是为了防止他们“金蝉脱壳”。
P106
另外,债权人也是理性人,他们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和其他机制保护自己,比如,他们与“三无”公司做交易前不做尽调吗?另外,原来在实缴制下也有大量皮包公司,从债权人保护的角度看,比认缴制下的“三无”公司还厉害,毕竟认缴的资本还可以要求缴付,算是一个保险。
李建伟
:@李志刚 我提出的修正意思主义,就是合同生效并通知公司。后来我又补充公司有异议的权利,因为股权转让合同可能违反了公司章程中关于限制股权转让的规定。新公司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包含了公司异议权,至少是抗辩权。
黄辉
:我前面说的公司同意问题,是指公司是否有权同意更改股东名册,不是同意是否可以转让的问题。
李志刚
:这两者需要分开吗?比如同意转让,但不同意变更名册?或者不同意变更名册但同意转让?
黄辉
:有联系,也有区别。同意转让的问题,主要是章程限制或股东协议限制转让的实体性问题,而同意变更股东名册主要是程序性问题。我提出公司是否有权不同意变更股东名册的问题,就是为了简化问题,聚焦股权转让的程序要件。
前面提到,根据新公司法第八十六条,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不是简单的当事人意思主义,而是需要变更股东名册,那么,这个新规定好不好?各方在变更股东名册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
赵玉
:我同意各位老师的意见。我有一个考虑角度,如果公司是个利益主体,是否要考虑公司是否有成员选择权呢?
李志刚
:在股权转让交易中,公司是主体还是客体,是赵玉老师提出疑问的本质。
葛伟军
:第一步,合同生效,有约定或需批准的除外,份额或股份发生转移。第二步,通知公司后,产生的效力是公司有义务变更股东名册,经变更后,受让人才成为股东,可以主张股东权利。但是,在变更之前,因受让人已取得份额或股份,所以享有财产性权利,但是还没有人身性权利,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股东。
张巍
:股东向另一方转让股份,公司难道不是第三人吗?
李志刚
:差别在于是知晓(配合履行)还是审核同意。
叶林
:股权转让及其在公司法上的效果,就如同一个孩子的出生,需要经历受孕、胚胎、胎儿,才能出生并最终形成完整的股东权利,这是一个渐进展开的过程。其中,转让双方达成转让协议,充其量只是胚胎或胎儿,公司未必知道;股东主张公司办理名册变更,相当于孩子出生,公司知道并接受;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相当于上户口,使得登记事实产生对抗效力。在这个意义上,股权转让并不复杂。如果连这个问题都异常复杂,就不能说我们的市场或法律是好的。
因此,在分析股权转让中,也必须分阶段予以分析,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动产买卖合同。
张巍
:公司有权不给股东办登记吗?当然前提是满足了优先购买权之类的条件。
公司有没有审核权,在新加坡法下,要看章程。
叶林
:公司在收到股东变更的申请时,应当按照公司章程以及优先购买权的规则予以“审查”,除此以外,公司并无审核权。但对于特殊的公司如金融机构,或许必须附加公司意见,才能提交给证监会或金融监管局。如果公司提交的文件不符合监管的要求,就无法获得批准;如果金融监管局等已限制了股权转让,公司也无法获得批准,此时,公司无法简单表示同意与否,往往是必须遵守监管者的意见。但在中国法上,不用“审核权”的概念。
张巍
:叶老师讲的属于特定行业的行政审批了,好比跨境并购会有国家安全审查。
叶林
:是的。
黄辉
:在英联邦法域,公司董事会有权拒绝变更相关登记,正当理由包括股权转让的材料不完整或无效,违反法律和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限制的规定等。当然,董事在行使该拒绝权时需要遵循董事义务,而不能随意拒绝。具体可参见我的绿皮书《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第90页。
通常情况下,股权转让后公司都会配合完成股东名册的变更,公司拒绝权的意义并不在于实体上的最终拒绝,而更多是一个程序性的保护措施。如叶老师所言,让公司可以作一个至少是形式上的审查,在事前避免一些明显的股权转让瑕疵问题,包括违反章程限制的转让,以及一股二卖等。
因此,我支持新公司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
P107
册……公司拒绝或者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转让人、受让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符合国际做法的,既规定了公司的拒绝权,也保障了转让方的诉讼权,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