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送:
2019年01月书单
丨
2019年2月书单&心得
本月读书10本,读得不多,主要读了几本大部头,花的时间和精力都比较大。
读得多不多,吸收得多不多,这条小鱼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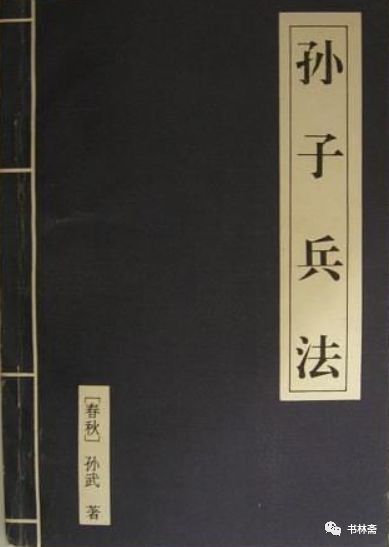
果然,《孙子兵法》是要有经验才能理解,实践产生意识,小学时读的那一次完全没有理解,这次却收获很大。所以未来一定是越有经验越能理解,所以要常根据现实揣摩。
事实上,《孙子兵法》除了第十和十一篇说的是军事地理、第十二和十三篇说的是方法论外,前面九卷讲的都是哲学思想。这样的哲学思想不仅可以用于战争,还可以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制衡。
第一篇说的是意识形态。「
一曰道
」,道在第一,则合法性的共识是必须的,只有它存在在所有人的心中,才能如臂使指,上下齐心,而天时地利和将帅的能力反而在其次。
第二篇说的是钱的问题。打仗是要花钱的,钱是物资、是后勤。上到政治战争,小到两人之间,核心都是钱的问题。这是一切的基础,汉朝最后就算没有卫青和霍去病,也可以耗死游牧民族匈奴,因为汉朝人种地。
第三篇说的是要杀人诛心。杀人还不够,得告诉对方对方是怎么输的、为什么输,让对方从心理上也认同。
第四篇说的是在保住基本盘的时候,再去和对方硬碰硬,然后要抓住对方的主要矛盾。
第五篇说的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外在表现出来的,不一定对;但细节和小心思,一定对。
第六篇说的是要掌握主动权。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找到对方的弱点,但不能让对方看透自己。
第七篇说的是必须上下如一人。
第八篇说的是要扬长避短,不执著于自己的缺点,而尽可能放大自己的有点。
第九篇说的是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拿自己的缺点和对方的优点比。
你看,虽然这只是我粗粗阅读后想到的,一定不完全是孙武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其实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和他人交往时或有意识或无意识使用的,因此在阅读了《孙子兵法》后,我在这些地方与之产生了共鸣。
「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如果你想做一个尽可能不受人制约的人,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小心思被别人一眼看穿,你当多想想你自己和他人。
在此,祝福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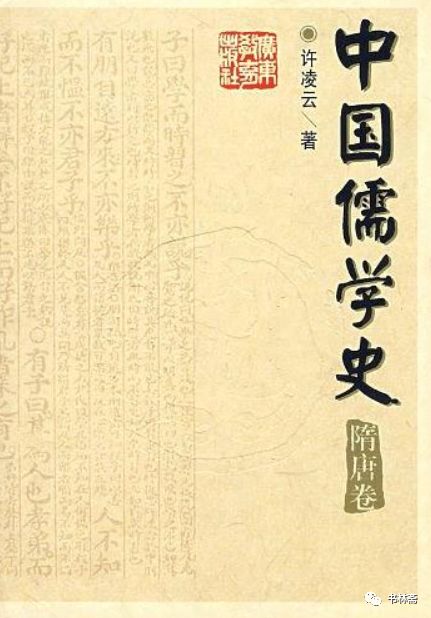
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的思想。
在经历了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乱世后,我们终于迎来了隋唐。可我们迎来的是什么呢?是两汉经学在乱世中的不堪一击,是佛老在残瓯里的艰难生长,等到了大一统的隋唐时,所有人都忽然意识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何以立国?
儒释道互相渗透、互相碰撞了几百年,到隋唐时虽然看似水火不容,但实则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唐王朝尊李耳为祖,武周王朝以佛家为尊,都是为了合法性的建构,而儒家此时犹如一个幽灵,时刻存在着,却时刻不被认为存在着。
直到那件事后。
直到那件改变了唐朝、改变了中国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世界的事情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安史之乱为分界岭,唐朝变了,中国变了,世界也变了。大唐的统一从开放变为保守,南方的地位从落后变为进步,中东的交流从密切变为疏远。于是说小了,杨贵妃死了;说大了,整个世界史变化了。
然后韩愈登场了。韩愈从故纸堆里重新挖掘出了儒家,尽管在此之前,刘焯、刘炫、颜之推、王通、吕才、刘知几、杜佑等都在努力做这件事,但因为大唐的政治经济在那里,儒家并不曾受到极为重视的目光。韩愈赶上了好时候。——当然这也是天下的坏时候。
韩愈开始批判道教和佛教。这时他开始写诗:「
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
」(《谢自然诗》)「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
」(《华山女》)韩愈不仅对道教进行了无情的讥讽和嘲笑,他决定反佛。最出名的就是《论佛骨表》:「
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
虽然韩愈的行为触怒了唐宪宗,但这不重要。因为韩愈找到了他的法宝:道统。他用道统学说构建起了自己的新儒学理论,他对仁、义、道、德进行了新的定义(甚至可能是第一次定义),从而彻底将其与佛老切割开来,紧接着,道统就出现了。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是中华正道,孟轲之后道统就失传了,荀子和扬雄被请走了。而周公以后,道统和君统分离,道统高于君统,于是谁来接着这个道统呢?
「
舍我其谁?
」
但是,佛老毕竟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不再是两汉经学可以横行无阻的时候,必须要想办法容纳它们,此时吸收之就是最好的法子了。李翱提出了复性论。李翱是韩愈的学生,他融合道家复性论,又对佛教禅宗的见性成佛进行吸取,终于完成了道学的基础。
尽管直到最后,唐帝国仍旧未能再现儒家在两汉时的耀眼光芒,因为没钱、因为没权,但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罗隐等人依旧做着不懈的努力。
终于,在唐帝国轰然倒下的那一刻,儒学打响了理学的第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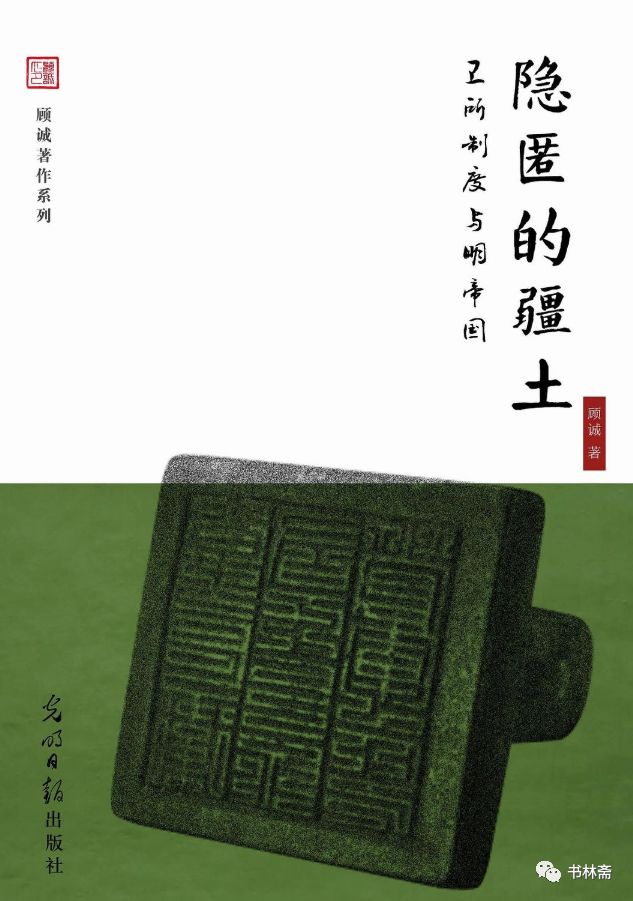
顾诚先生学力惊人,常常在明史的各个领域具有奠定性的作用,如若不是去世得早,他的第三本专著当是关于卫所的,而他之前那两本《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已经成为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即便顾诚先生关于卫所的专著未能写成,但他关于卫所的研究和论文也已经确立了他在明代制度研究史里的地位。这本《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收录了他几篇论文,很久以前翻过,在其中顾诚先生通过对明初期耕地数的差异性矛盾,分析猜测出这是有司和卫所的两套系统在其中的缘故,并构建出了明代卫所的基本模型。
尽管卫所是明代的基本军事单位与地理单位,但由于资料缺乏和年代久远,现如今的研究者们其实对卫所的了解并不多,在研读明代相关财政、社会著作时,会发现作者们对于卫所的表述也同样含糊不清,于是找来了李新峰先生的《明代卫所政区研究》。
在阅读《明代卫所政区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李新峰先生对顾诚先生的卫所模型有一些修正,出于这样的原因,暂且搁下了《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几天,回过头来重读一遍顾诚先生的论文。在这次阅读过程中又有了新的想法,尤其是对于清初卫所的消亡和明代卫籍、卫学的衍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带着顾诚先生的这份奠基基础,接下来打算再次拿起李新峰先生的《明代卫所政区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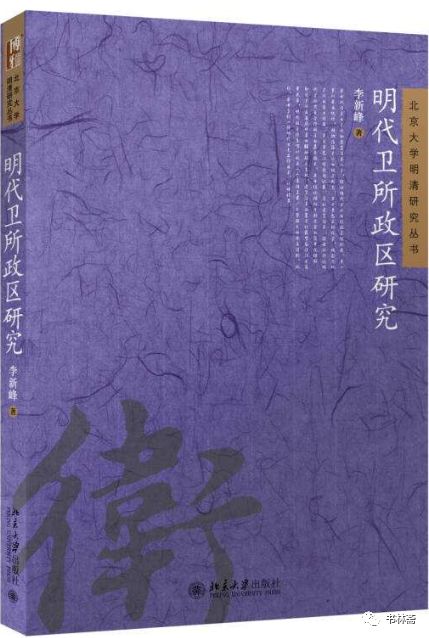
在顾诚先生构建的模型中,卫所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单位,还是一个地理单位,但顾诚先生毕竟没有花上足够的精力在卫所上,二十多年后,关于卫所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进展,李新峰先生的这本《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就更细致、更深入地对卫所的存在进行了构建。
本书的核心是政区,那么问题来了,卫所究竟是不是政区?亦即它有没有独立行政的职责和能力?
本书分三章,前两章分别研究了沿海卫所与边地卫所,通过几个元素如屯田的归属权、民人的管辖权、驿递和防区的分布管理等,用更细致的史料、更深入的分析,反驳了顾诚先生构建的比较粗暴的模型。到了第三章,李新峰先生便在前两章推翻前人论点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构建。
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枯燥的工作。它涉及了从元末到清初三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变化多端;它还涉及了全国各地的方志和历代实录,同时还要对明代的官制、财政、军事有比较深的了解,而且其间很少涉及到事件,因此无论是作者研究起来还是读者阅读起来,其实都没太大趣味。但是当你阅读到最后那个结论时,你会觉得前面的工作(研究工作/阅读工作)都值了,因为那是你第一次系统地审视这个明代疑难杂症问题,并且得到了一个让你满意的结论。
那么李新峰先生在本书中对卫所最后的构建是什么呢?明代的都司卫所系统,是对司府州县系统的辅助政区系统,而非同等级别的政区系统。
此外,在阅读本书中,建议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与郭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一同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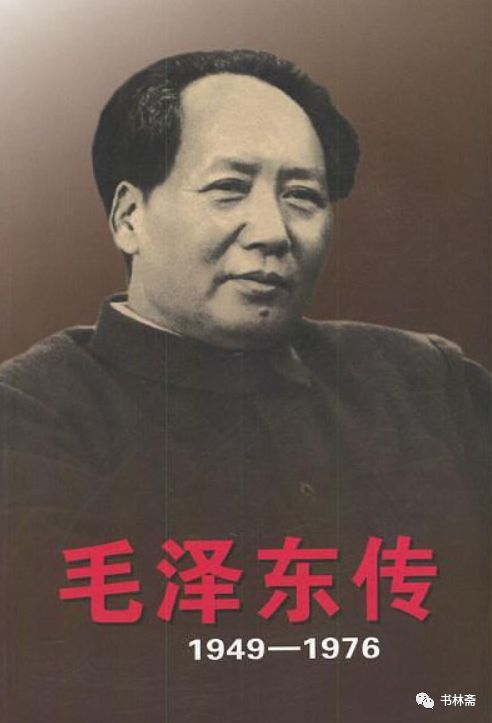
治大国如烹小鲜,手段是手段,目的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现代化。那么如何从建国以来的一穷二白建设成现代化呢?我们一直在探寻。
本书分上下册,上册写到炮击金门,基本上是建国前十年内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些事大家大都知道,但对于细节却知之甚少,只是细节有时也不完全是细节,当我们跳出这些回过头来看它的结果时,你必然会明白我的那句话:「
治大国如烹小鲜,手段是手段,目的是目的。
」
遇到问题,你要怎么操作?是束手无策,还是迎难而上,还是运用策略换牌来打?每一种都会有不同的结果,也会带来不同的评价。所以其实你可能并不能确定地知道这个人的意识形态倾向。我相信这个道理主席是懂的,我更希望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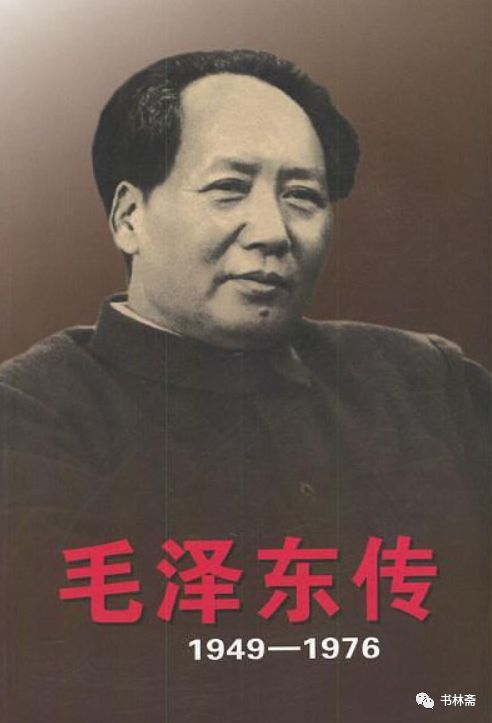
长吁一口气,从02月14日18时07分起,到03月22日23时31分,36天时间,我读完了三本书,足足2784页纸,但每个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那个83岁老人一生中的几个或重要或不重要的片段。
当我写下「
老人
」二字时,不禁在心中打了个问号:他真的是一个老人吗?
1975年12月31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来到中国和这位老人交谈。在交谈中,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老人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
斗争
」的话题却使他又「
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
」,「
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
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他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
他是老年人,他也是年轻人。
右派说他左倾,左派说他右倾。
有人说他太冷,有人说他太热。
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
可以发现的是,金冲及先生其实直到最后都没有给这位老人下评语,他不断引用他人的评述,却没有自己做论断。该怎么说呢?1976年09月09日0时10分,农业中国的最后一位巨人溘然长逝。
巨人,巨人是注定会播撒改变剧本的种子的,也因此只有巨人才能真正理解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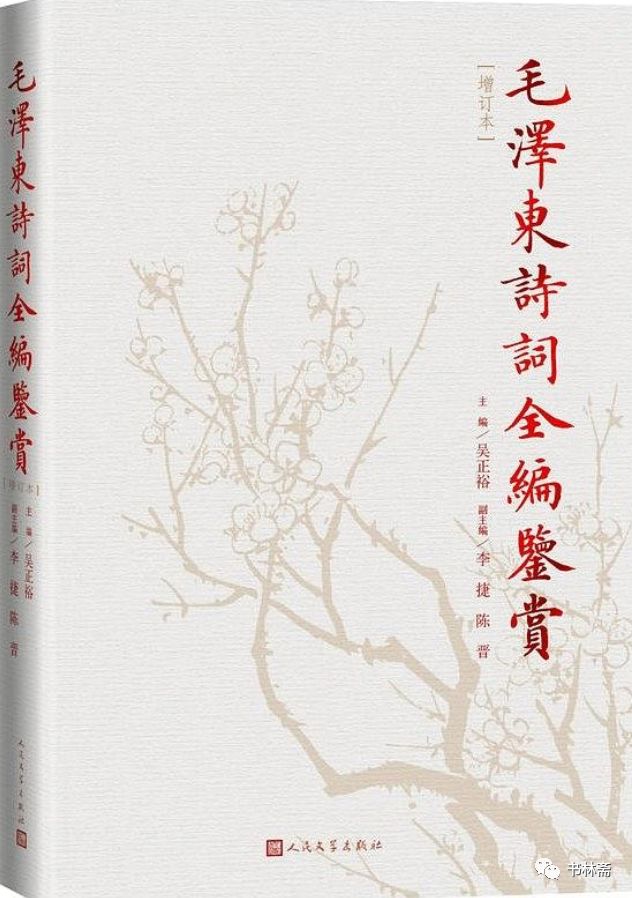
老人和曹操一样,也是一位诗人。
年轻时的老人,纵身一跃,遨游湘江,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激情澎湃地高呼,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后来年轻人长大了,变成了中年人,但时间磨难却没有磨平他的心志,他反而更加豪迈、更加壮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睥睨古今,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中年人也会变老的,但老和老是不一样的。七十岁那年,他放眼望全球,捭阖纵横,与挚友郭沫若齐声笑道,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放话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但如今他已经八十二了,他已经很久不写诗词了,最后一首也是写给郭沫若的,却再不见当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冲天志气,却只剩下了回望两千年的坚定。
「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
这首诗里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孔丘、一个叫嬴政,一个叫孔子、一个叫秦始皇。两千年以来,没有谁比他二人对中国的影响更大了,一儒一法相济,将中国历史往前推了两千年,等历史推到毛泽东面前时,他终于发现,自己也必须面对这两个人了。
是学孔子,高呼仁义,和所有人和睦相处,彼此相安无事走下去?
还是学秦始皇,高高在上将反对的人全部推倒,独自一人站在高台?
都没有。他选的是第三条路——他与人民群众和睦相处,把其他人推倒。也因此在他死后,他必然会成为孔子和秦始皇之外的第三人——具有极大争议和极大影响的第三人。
这是他最后十年留下的面貌,这张面貌必然不会随着他的离去而消散,而会活在很远的未来。
但他不只有这一张面貌,在他大量的诗词里,有一首非常特殊,那是写给他第一任妻子(如果罗氏不算的话)的。
《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
词中的「
骄杨
」,指的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至于为什么是骄傲的骄而不是娇嫩的娇,很久以后他对章士钊说:「
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
是的,杨开慧死了,而且死了很久了,死了很多年了,四十多年前的十月份,杨开慧被军阀何键逮捕,由于坚决不愿屈服,11月14日,她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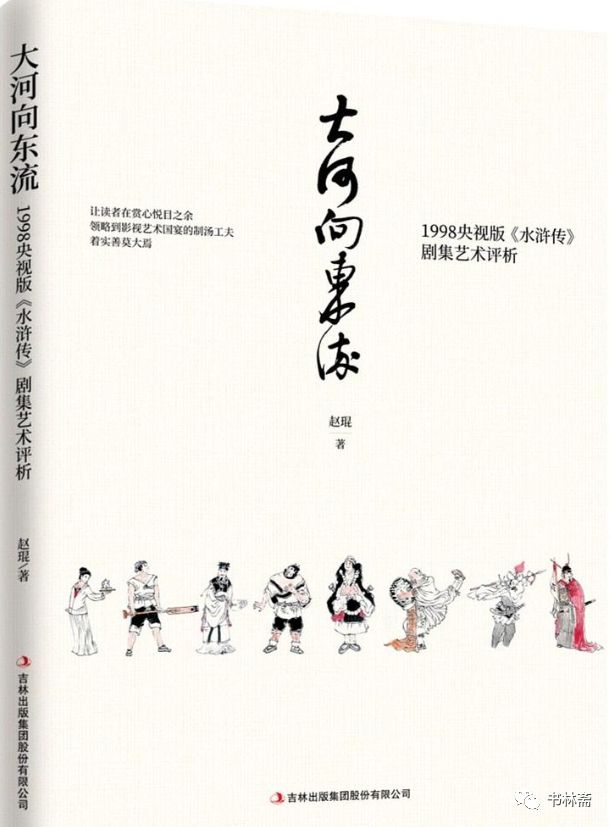
赵琨(荞麦花开)是写剧评时认识的好友。剧评出书殊为不易,首先要读者对这部剧熟悉,其次要读者在阅读中有画面感,这二者就很难了,更何况一般剧评是一文一评,如若出合集,必须大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电视剧。
荞麦这本书则不然,别人图广,他图深,一本书只写了两部剧,其中近九成的篇幅是98版《水浒传》,剩下的夹叙夹议了鲍国安版《水浒传》、《围城》、《我的团长我的团》、《士兵突击》等电视剧,还有各种旁征博引,因此读者只要对98版《水浒传》熟悉即可。——甚至也不需要,试问谁不知道宋江、武松和潘金莲呢?
荞麦本是写陈道明的一把好手,对陈道明的多部影视作品深究到了每一个肢体、每一句台词和每一副表情,也许有过度解读之嫌疑,但论及深度确实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而其行文,颇有古韵,看似有主题,实则四处发散,看似信马由缰,却又很快会回来扣题。喜爱者会受益匪浅,无感者会头昏脑涨。——但这本来便是极私人的写法,自然所获得的是极其强烈的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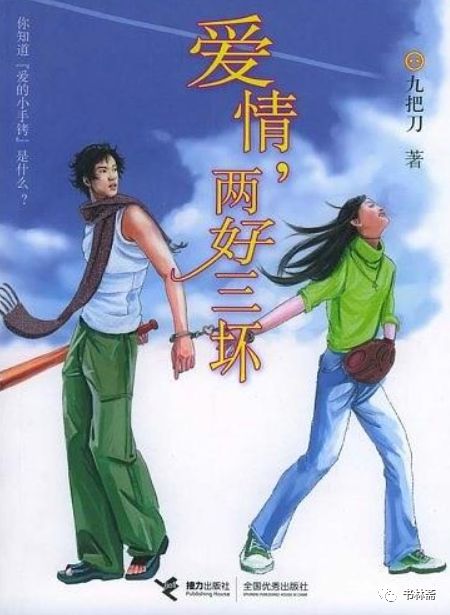
《爱情,两好三坏》是九把刀几乎不用改动结构就可以直接变成剧本的小说,完整的剧本三幕式结构,完整的人物动机,完整的人物弧光,但也因此它显得很俗套,成熟的技巧,成熟的手法,成熟的金句,让整个故事显得平滑无比,不是说它没有起承转合,而是说它的起承转合从起开始就注定了。
一个注定了的结局,读者还爱看吗?一个注定了的结局,观众还爱看吗?
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如果你知道了剧本走向,那你就要去改变它,哪怕最终无法改变,这个过程也是动人的,但如果你就此按照剧本走去起承转合,那它第一次很讨喜,第二次就不讨喜了。
有了周公才有孔子,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玄学和杀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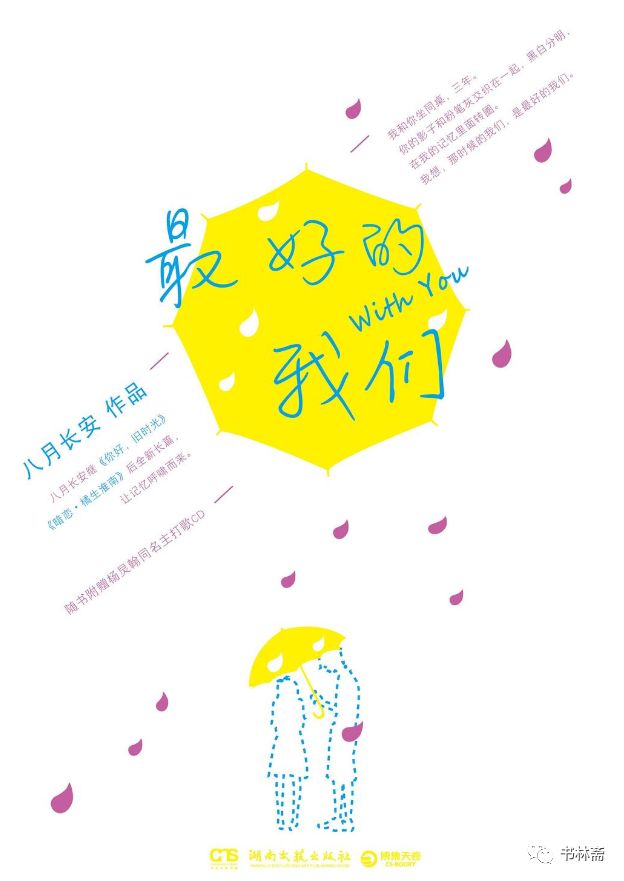
忽然就想来重温一下这部小说,电视剧里的刘昊然和谭松韵演得很符合小说人设了,但总归还差点什么,当时隔数年再次阅读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差了情绪。
电视剧里有很多情节,很多动作,余淮和耿耿之间的关系波折,很好,很套路,但小说可贵在哪里?可贵在无法用剧本呈现的那许许多多的小心思。女主那些细腻的想法通过描写不断呈现给读者,哪怕没有事件,也让读者一步步陷入进去,于是你终于发现,剧本终归是剧本,而情绪是有褶皱的,情绪的褶皱不一定会改变剧本的走向,但它会改变你的感受。
你的感受重要吗?也许对剧本的走向不重要,但对你重要。如果你无法改变剧本,那不妨改变你的感受。
「
这条小鱼在乎。
」
那双情绪汹涌的眼睛,当时我看不懂,此刻回忆起来,心中尖锐地疼。
我没有怀恨在心。因为我懂得他。
他在张平说落榜生张继名满天下时,说成王败寇活在当下;他在顶楼向我小小地展示了自己对竞赛成绩的恐慌后,就立刻大声说「你要继续崇拜我」……这样的余淮,怎么会愿意让我戳破他的谎言。
谎言已经和他的尊严紧密不分。
记忆中的少年余淮越是闪闪发亮,现在这个活在谎言里的男人,就越让我心疼。
我居然还曾经在他面前提张三的近况、李四的新工作、王五的留学生活……
何其残忍。
有些东西,我从来没得到过,所以也不觉得可惜。
他却是实实在在地失去了。
——摘《最好的我们》里最戳我的一段话。这是一个不知做了多少次的噩梦。回想起来,我会在很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决定选择这条弃理从文的路,所需的绝不仅仅是勇气。
阅读原文处可查看文章集锦。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