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城市,有着太快的变异速度,以及吞噬过去、遗忘一切的本能,它在无形中偷走大部分人的人生,而替换成一些千篇一律的片断和定语。
▼ 本文由豆瓣用户@月光粥 授权发布 ▼
那天早晨6点多醒了,并不想起也睡不着,便躺在床上品咂梦的余味。梦里依稀是爷爷。他和我说话,他衰老,委顿在地上变成灰,随风而逝,尘埃飘在我脸上。我不是第一次梦见亲人,但每次他们都是离我而去或死去。我分不清他们的脸,那些脸荒芜得没有意义,仿佛是陌生的面具套着一个个熟悉的灵魂,但我又能清楚地感知他们与我的亲缘,他们的“消失”令我在梦醒后依然心下凄然。
我已习惯在想象或梦境中预习至亲离世:有追悼会,与或熟或生的亲友一一见面,接受他们的吊唁,表情堆满感恩;写悼词,不夸张又煽情地介绍死者平凡的一生,用“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种句子;那些人排着队,自然地画出个圈儿,轮流瞻仰遗体。队伍本身让我联想到黄泉路,默默无言的死者排着队走去投胎。而我却不知去世的是谁,他可以是我至亲的任何一人,又不忍成其为任何一人。
此种排演,始自我少年时。父母体弱多病,相继得过重病,死亡阴影在我家挥之不去,因此我很早就出于预防心理,对自己所畏惧的,先在心里预演一遍,以期真正发生时,不至于被击得粉碎。光阴荏苒,葬礼也参加了不少,我脑中的画面得以不停充实,但排演的频率却低了下去,因为这一天日益临近了。
梦后一瞬的心情,是真实感觉的残留,我无法想象自己直面这场景的时刻,恐怕仍然会被击得粉碎吧。预演只是预演,当死亡带着无与伦比的重量压下来,不会有什么反弹。很多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我在医院里探望弥留之际的爷爷,自从老家动迁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仿佛一瞬间,他就从坐在藤椅里问我话的那个老人变成了病床上的那副皮囊。他嘴巴翕张着,双目紧闭,喉咙里卡着痰,里面嗬嗬有声。我妈说,你爷爷就要没了,你快点喊你爷爷两声吧!口气是在催促。我突然感到语塞。叫在我并不是一个熟悉的行为,我不知该如何叫,是声嘶力竭地叫,还是如常地唤他“阿爹”。我看看周围,别的病人依旧躺在床上,这只是一个普通病房,不是生离死别的地方。我只是在他耳边说:“阿爹,我是××啊。”就像我过年时向他问候一样平静。我重复了几遍,声音如同落入一口枯井。阿爹的喉咙里反馈出几丝气,似乎是他快燃尽的生命的最后几缕烟,透过漫长的气管,穿过浓痰,抵达世间。护士推来吸痰器,我父亲轻轻地摇摇头说,没意思了吧。他觉得爷爷已经撑不了多久了,没必要再受这份罪了。然后我和我母亲就走了,当天我爷爷就去世了,我没有等到被单蒙脸那一刻。
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所发出的其实是呼唤。呼唤一位亲人,呼唤他的一生,呼唤流逝的记忆,呼唤我的前生。我对自己爷爷的了解,仅限于父亲之口。爷爷退休前是在一所小学里面做校工,他是木匠,学校桌椅板凳的维修,多交给他。老屋里的一些桌子板凳,也出自他手。这年数并不算长的正式职工生涯,为他换来一张光荣退休的奖状,他的一生便被概括了。奖状作为一个句点出现,奖状之前的漫长岁月被省略,因为那是体制外的,旧时代的,人人浑浑噩噩,生命朝不保夕,这样的岁月,没有书写的必要。于是,他曾做过些什么,对我而言是一片空白。
于是我只能自己想象:他来自上海浦东的农村,他的家族在他出生之前,已在这片长江淤泥构成的平原上繁衍了不知几代。对岸是作为东方巴黎标志而存在的浦西,而其双生兄弟浦东则长年被历史遗忘。浦东旁观着对岸百余年来明灭的灯火,黄浦江上升落的日头,时间似乎不曾在它身上淌过,直至解放,它仍保留着中国传统农村的一些风俗。例如家族。当地有以我爷爷的姓氏为名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虽然谁也不知祖辈何时来此,但不妨碍后辈尊奉他们。村里有祠堂,香火从未中断。相对拥挤逼仄的浦西,浦东平坦到几近荒芜的广阔则令人无所适从,也正因此,战乱和统治亦将其遗忘。这里的人们不知世间岁月般地活着。我爷爷从小在田埂河间长大,20岁前,他的对外接触,仅限于两三里外的镇上。他在镇里读了小学,然后每月一次将家里积攒下来的废旧瓶罐用黄鱼车拖到镇上卖掉,除此之外便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他在村里跟一位木匠学了些手艺。木匠游荡半生,终于觉得累了倦了,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他教了爷爷一些三脚猫的技艺,爷爷却如获至宝。20岁后的一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为何便突然决定到浦西闯一闯。
可能村里早已有人在浦西落脚,可能不时传来的某某在城里混出个人样的例证刺激了他。总之他义无反顾地走了。当他走出渡口,走出层峦叠嶂的大包行李和鳞次栉比的肩膀,却被更加密密麻麻的人流给惊到了。原来这就是浦西。房子连着房子,人连着人。今天,当我在上海的某个街角看见那些翩然而去的女子时,我就会看到女子的另一边,亦有一束陌生的视线望将过来。这就是我的爷爷,他当年在四马路下了电车,望着同样婷袅的女子踩着雨后湿漉漉的上街沿迤逦而去时,恐怕也是震了一震的。一种陌生的情绪涌到了他的嘴边,我不清楚那是什么,当时的他自己也不清楚,但这无疑是带着一丝希冀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世界转动将带着他一同转动,他为这种步调的偕同而兴奋。然后,他就在街角消失了。多年后,他穿出时间的迷雾坐在我对面的藤椅里时,脸上已全然不见可称为表情的表情。他的思绪和精神,完全沉浸在另一个时空里,而眼前的躯壳,则被身旁的半导体中传出的滑稽戏的笑声所吸引。
我只能猜测,他在上海扛过大包,在工厂里做过活,给酱油店当过伙计,给面馆当过跑堂,一个偶然的机缘,他结识了和他同为乡里的奶奶,一名纺纱女工。结婚之后,他终于想起前半生的至宝——木匠技艺,他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一名木匠,便决定以木匠之名生活下去,尽管那会儿他并没做过什么东西。之后的辛酸很难想象,总之他用实践中磨练出的技艺在这块地方站住了脚。然后,对他来说,极为偶然地,解放了。新旧社会的交替对他来说并不具有必然性,他只是突然地在一夜间发现,马路上睡满了人,城头换了旗子,外国人都不见了。他做校工的那所小学也在一夜之间换了领导,然而更偶然的是,他听说自己翻了身,成了主人,变成了什么阶级的一员,尽管他仍蜗居在小学为他安排的狭小宿舍里。偶然性并未就此终结,他突然有了房子,学校把一位一家不知去向的教师的房子分给了他一部分。那是在上海静安区石库门弄堂里的一座过街楼,有上下两层,上头是带着老虎窗的阁楼。他带着奶奶和刚出生的大儿子(就是我父亲)搬了进去,光阴荏苒,楼上的人家不知何时因什么原因搬走了,学校没让新人入住,于是这座楼便成了爷爷的私产,其合法性因年月日久和无人反对而得到默认。后来,二儿子出生,结婚,便把阁楼用作了新房。再后来,我便在这座楼的楼道里看到了其主人的退休奖状。
哪怕是想象,也仅止于此。
在我的记忆中,我爷爷只有和他的父兄说话时,才会用乡音,既给我一种偷摸之感,又让人觉得他们是在暗地分享独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用浦东土话聊幼年往事、聊乡下的亲戚邻居、聊叔伯辈中所剩无几的几位亲人,而这种口音,我是一点都不熟悉的。我总觉得他们是“背着”人们在说话,这种“偷摸”使我意识到眼前的他们,或许只是活在一个被赐予或被定义的人生中,这定义是社会给出的,是我们旁人给出的,但并不属于他们,而他们真正的人生,只在这乡音中才偶尔流露,如同透过树荫泻下的阳光一样飘忽不定。
上海这城市,有着太快的变异速度,以及吞噬过去、遗忘一切的本能,它在无形中偷走大部分人的人生,而替换成一些千篇一律的片断和定语,每个人活在其中,都像得了失忆症一般,久之,你已不习惯去回想。而当你真的想去寻找一些什么,却发现记忆无从建立,几乎所有可供追忆的物事都被擦去了,于是,你不得不默认,你自己的人生也被偷去了。
人总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走过的时代究竟是怎么回事?而等到这一整代人凋零时,你其实仍然不了解他们。
龙应台曾说“一个社会缺乏历史感的时候,你会对你身边的人漠视、不认识,因而不珍惜。你对你父母、祖父母辈的历史没有兴趣,因为自己的无知。因为无知,所以不知道珍惜。等到你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生命的结构就刚好是他走的时候。”这是何等的令人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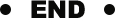
本文版权归 月光粥 所有,
任何形式转载请点击【阅读原文】联系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