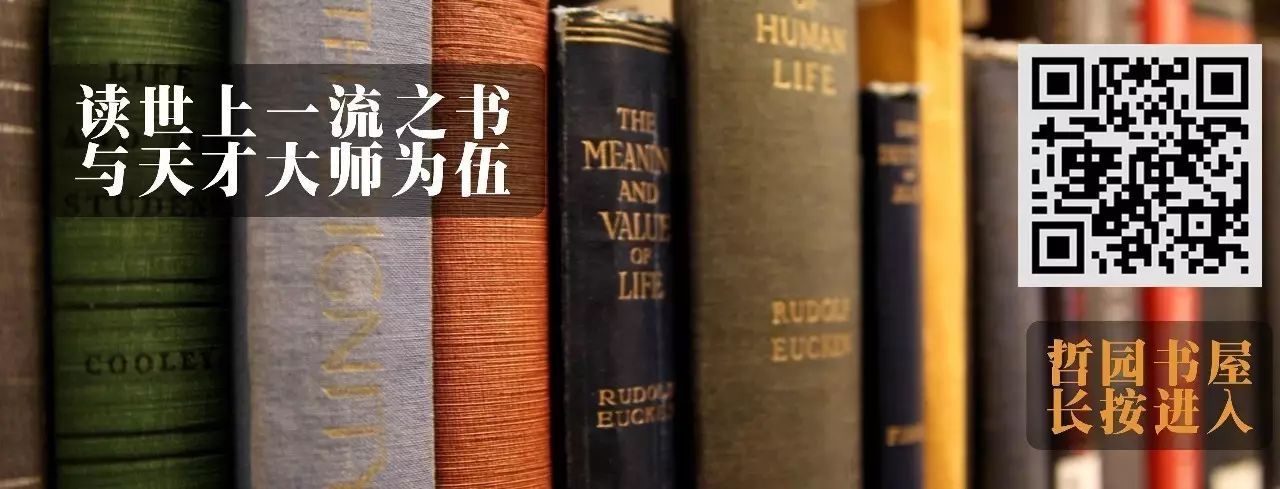置顶哲学园 好文不错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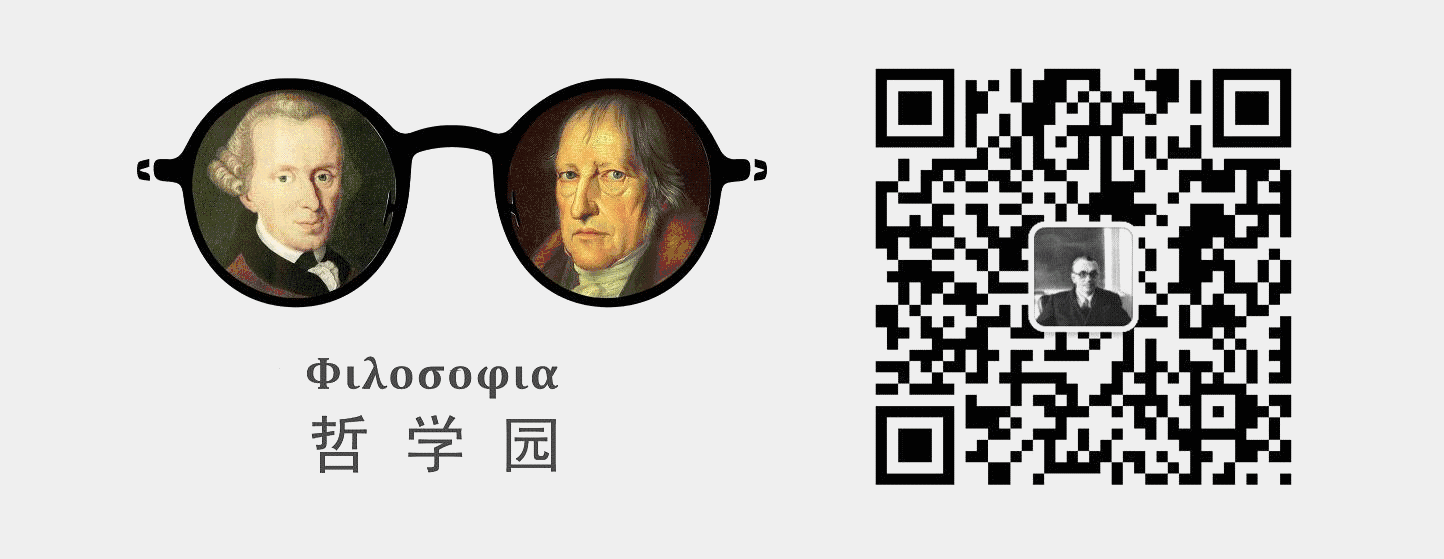
来源:哲学新媒体
https://www.philomedium.com/report/79952
By Lynn
2017 年 5 月 21 日晚间,在 PHDEO (台湾高中哲学教育推广学会)的锦西街聚点,举办了一场「哲学应该普及化吗?」的讲座活动,与谈者有法国《哲学月刊》总编辑 Martin Legros 、两位致力於哲学普及的大学教授——吴丰维(文化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与叶浩(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以及推动高中哲学教育的高中老师林静君、法国高中哲学读本译者梁家瑜,等几位哲学推广者,分别对哲学普及(上半场)和高中哲学教育(下半场)这两个议题来进行经验分享。1此活动吸引了许多关心哲学教育、哲学推广的民眾和媒体参与。
「哲学普及」与「专业哲学」的关係
主持人沉清楷(辅仁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首先谈到,所谓的「哲学普及」可以相对於「哲学专业」来理解,因而会有「肤浅」和「深刻」的对比。然而沉澄清说,他并不认為专业一定是深刻的、普及一定是肤浅的,他指出哲学普及可能会带来更广泛的深刻性,而学院的研究也可能是很深的肤浅。
所以他提醒现场观眾,今天的讨论将从「思想传递」的角度来谈哲学普及。他希望与谈者能将讨论放在他们怎麼看待哲学普及和专业化之间的关係。顺著这个脉络,主持人请 Legros 先谈谈「哲学普及是怎麼开始发展出来的?」。
哲学普及的发展在法国
Legros 从欧洲歷史及知识脉络的三个重要时刻来谈法国的哲学普及的发展。首先是十八世纪末期,基於啟蒙精神,百科全书派的代表哲学家狄德罗提倡哲学普及。他主张,要建立共和与开放的社会,具有思考能力的民眾是必要条件,因此哲思的培养就不能只為学院中少数人所有。
第二阶段则以 1960 年代的哲学家德勒兹為代表,他主张 POP 哲学——流行哲学。这类似於 Andy Warhol 的艺术创作精神,透过将日常生活中毫无特色的事物,譬如金宝汤罐头 ,变成艺术品而赋予了意义。在此观点下,学院中宏大且精緻的哲学理论就无法变成可普及的哲学,因此德勒兹选择从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小东西,譬如一盒香菸,来进行哲学思考。哲学普及在此意义下必须是贴近现实生活的。
哲学普及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法国在二十年前左右兴起的哲学復兴运动,此时的哲学普及结合了狄德罗和德勒兹的想法,為哲学的大眾化找到了新的方法:将学院哲学的概念落实到世界,用以理解生活中的种种现实。
在谈了这麼多关於哲学普及的实质内涵之后,法国的哲学普及又是怎麼进行的呢?Legros 以《哲学月刊》為例做出具体的说明。
他说,《哲学月刊》做的事情有三个部份。其一是在不减哲学深度、不违背思想家原意的条件下做哲学转译的工作,让哲学变得较可亲、引领民眾体验原汁原味的哲学思辨。其次则是处理「存在」(how to live) 的议题,也就是协助读者处理人生在世会面临的问题。举例来说,《哲学月刊》的专题讨论过「為什麼要工作?」、「為什麼要生小孩?」这些具体的生活问题。第三个则是尝试处理政治的问题。Legros 指出,这是著眼於现代民主社会中有许多公共事务的议题是之前的哲学家没有思考过的,因而需要新的讨论和方向,以共同思考出答案。
台湾哲学家的哲学普及
哲学普及的风潮,这几年也席捲至台湾。在台湾进行哲学普及工作的学者,又如何看待「哲学普及」这件事呢?此次座谈会的两位教授,分享了作為专业哲学研究者进行哲学普及的经验。叶浩提到,哲学普及与哲学专业的活动会相互回馈;吴丰维则提出「普普哲学」与「公共哲学」的想法。
叶浩从他的哲学普及经验切入,谈到了哲学普及工作迫使他在专业上更专业化。他说,不管是从学术语言到日常语言、还是把哲学从外文译為汉语,专业哲学与哲学普及之间的关係就是翻译。他以学习外语作為比方:在越来越掌握外语(哲学普及)的过程中,我们会越熟悉中文母语(专业哲学)。因此,為了进行哲学普及,他必须回头再钻研哲学,以更抽象、更精準的方式掌握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哲学文本后,才能转化成一般人可以听懂的解释。
举例来说,他本身关心两个哲学问题:「哲学普及如何可能?」、「跨文化如何理解?又如何转化不同文化的思维?」。他说第一个问题从苏格拉底时期以来就有,因為公民与哲学之间就有冲突。而哲普工作给他的回馈就是,这需要在经验上实际去做才能知道答案。其次,哲普也让他在处理柏拉图、奥古斯丁和圣多玛斯等哲学家如何融合不同文化思维来形构他们的哲学时,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因此,他说哲学普及事实上在各个不同层面上都帮助了他的专业哲学研究。
吴丰维说他很能认同叶浩的观点——专业哲学和哲学普及是相互回馈的关係。他也认為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这裡他举了弥尔、德沃金两位哲学家為例,弥尔从来没有在学院教过哲学,但没有人会说他的著作不是哲学。同样的,德沃金的书是大眾化的,但没有人会质疑他的哲学专业度。因此他说,专业哲学或普及哲学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个假问题,只有越专业化才能普及。
他也提到说,从台湾哲学社群的发展来看,从事专业哲学的研究者只有约 200 人2,他建议学者们不要故步自封,应该要勇敢走出去。他也鼓励台湾的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有信心,因為专业哲学其实有相当的公共性。
延续著前述的想法,吴丰维认為,哲学普及的意义就是让哲学走出学院。他说普普哲学, POP Philosophy ,就跟普普艺术一样,具有某种颠覆性。如同艺术品不应锁在美术馆、哲学也不应该只放在学院中;哲普的另一个面向,对他来说是公共哲学——哲学的公共应用。他认為把哲学的理论和框架带入公共讨论中,可让哲学扮演强大的功能,并不会因此减损其哲学专业性。
哲学普及的实务操作
藉由对「哲学普及」这个概念的澄清,三位与谈者都很能认同「哲学普及」的意义,但实务上怎麼做呢?有具体的方法吗?
Legros 以汉娜·鄂兰為例,提到她正是去了纳粹审判的法庭之后才发展出「恶的平庸性」这个哲学概念。鄂兰的例子很类似《哲学月刊》的经验,身為主编的他也曾请哲学家亲自去法庭之后再回来写有关「正义」的哲学概念。就是透过这种具体的方式而可以把哲学家带入真正的人世间,而非只是关在房间裡做哲学。不过,Legros 提到,现实观察者的作法也有把哲学家带入危险境地的风险,因為哲学论述通常违背主流价值,因而可能使哲学家被公审,就像当年被处死的苏格拉底一样。
台湾的哲普工作者又是怎麼实践哲普呢?叶浩提到,他尝试在广播中从电影的角度来谈一点哲学、也在电视节目《哲学谈,浅浅地》中用浅显的方式讲哲学,不过他说这都不算是相当满意的作法。他预计在下一季的电视节目中邀请哲学教授来谈他们自己的研究和所相信的东西,目的是将哲学家推入一般大眾之中。
吴丰维则从几个在台湾推广哲学所面临到的困难切入这个主题。他提到,在台湾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哲学,以為算命、玄虚的东西就是哲学,但这些其实都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并不是哲学;另一个极端则是仰望大师,将哲学供奉在学院中。他认為把哲学庸俗化或是神圣化都不是理想的推广方式。对他来说,哲学其实就是一个探求真理的过程,因此假如在推广的过程中缺乏对话、没有挑战,那就没有哲学了。
神话般的法国哲学教育及其隐忧
法国高中哲学会考考题,每每成為台湾教育新闻版面的头条。到底為什麼法国人会发展出高中哲学教育的制度呢?下半场的主题就是高中哲学教育,与谈人是在南港高中推哲学实验班的高中老师林静君、翻译法国高中哲学读本的译者梁家瑜,以及 Legros 。
Legros 从身為比利时人的外来观察者角度来看法国的高中哲学教育。他提到说,法国高中哲学教育是伴随於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link is external)而来。為了完成革命,具有修辞、论述以及在诸多价值中做出判断的这些能力,是成為公民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產生了延续至今的高中哲学教育制度。
纵然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目的——培养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公民——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并没有改变,然而教育对象却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这是因為早先高中教育属於精英教育,因此高中生皆拥有良好的法文能力,哲学教育可说是在知识养成之最后阶段的锦上添花。然而随著高中成為普及教育后,并不是每个高中生都很好地掌握法文,因此高三这年的哲学教育反而显现了法国教育的问题,突显其教育制度的残破景象。
现今法国哲学教育透过两种方式来建立哲学素养:研读约五十位哲学作家的作品、从哲学的观点来学习一些重要概念,如国家、自由等等。而用来检验高中生哲学能力的方式就是哲学会考——论说文写作和哲学文本分析,也规定了如何作答的一些形式规则。Legros 提到会考的申论题目都是非常夸张的,譬如「為什麼要工作?」、「真理」,4这除了非常考验高中生的语文能力外,也挑战高中是否具有独立作答的能力。他认為法国的高中哲学会考,是相当吓人的一件事,但另一方面也是很刺激的,简直像是神话。
整个欧洲都重视哲学教育
法国能够实施这样的哲学教育,不禁让人纳闷,难道是因為法国人独厚哲学,还是法国高中生天赋非常异稟?
Legros 说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高中都教哲学5、过去多强调哲学和理性的关联。然而现今欧洲面临许多艰困的当代处境——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等——促使欧洲高中哲学教育朝道德讨论、宗教歷史(不同宗教的演变和由来)的新方向开拓:著重於不同信念之冲突的思辨上,以及对宗教、信仰和思辨的反省。这一定程度可解决现今社会冲突、新的信仰兴起的种种困境。
台湾虽然没有将哲学纳入高中教育,但近年来逐渐开始重视。譬如 PHEDO 就与南港高中教师林静君(现為PHEDO副理事长)合作推出哲学实验班,今年(2017 夏)已有了第一届的毕业生。这个实验班的成果如何?
哲学实验班的初步成果
担任高中老师多年的林老师分享说,她发现高中生在谈论公共议题时无法进行论述也没有自己的看法,这让她意识到台湾公民的危机,因而兴起了将哲学引入高中的契机。这个哲学实验班的教学方式并非直接谈论像是「道德」这类严肃的伦理学概念,而是将其包装成「对与错」、「美与丑」、「自由与责任」这些相对概念的讨论,让教师比较容易引导学生进入相关讨论。
哲学教育造成的改变非常立即,林老师说大约一个月后她就发现学生变得比较有自信。这种自信来自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什麼、如何為自己的想法辩护、如何与人对话等等的面向上。学生也能反省自己的想法在哪些地方有所欠缺、自己要的是什麼、不易将就妥协。除此之外,学生也开始关心学校的公共事务,能够独立处理许多事情。
教哲学这麼难的东西有意义吗?
哲学教育刚起步的台湾,要如何开始在高中教哲学呢?有鑑於此,PHEDO 开始尝试翻译法国高中生哲学读本作為参考。有看过这套书的读者会知道其中涉及了许多哲学经典。用这种连大学教授都不见得看懂的文本学哲学,对高中生来说不会太难吗?
译者之一的梁家瑜从他之前带读书会讨论的经验和举办哲学营的经验指出说,哲学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联。从参加读书会的业餘读者所展现的对知识的兴趣、以及给予思考空间后高中生的表现来看,他认為哲学教育的困难可能并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教法的问题。举例来说,法国的哲学读本虽然要读一些哲学原典,但其用意是希望读者去反省这段说法哪边有问题,亦即不是要学生去背诵这段文字,而是去想。
他强调说,法国教科书的教育精神是指出事情可以想、可以讲。他认為正是同样的精神让哲学实验班的学生能够培养出成為公民的良好基础。
哲学课作為成年礼
听闻了法国几乎不可思议的哲学教育体制后,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这麼美好呢?
现场有另一位嘉宾, Myriam Palin ,以道地法国人和现役法国高中老师的身份现身说法。她说从她个人的经验来说,由於高三本来就已承受毕业会考的压力,再加上哲学课,真的是一非常可怕的事情。虽然说现在哲学会考的形式规定已经简化,然而她认為这个改变并没有让作答变得比较轻鬆。这是由於虽然教学内容并不强调强记博闻,但实际上学生仍然需要对於哲学著作和概念有明确的具体掌握、熟练引用哲学家的观点才能较好地呈现出自己的论述。
她认為在此情况下,高三生在短短八个月内必须要知道的哲学内容与负担还是太多,要获得好成绩仍是过於不切实际。因此,她认為这个考试制度可以看成是「成年礼」,一个培养良好写作能力的过程。而身為道德与公民老师,她也感嘆,由於学制上高三已不要求法语能力,因此批改哲学作文已沦為错字修正与修辞精进的工作了。
Legros 则指出,哲学在欧洲好像已经衰老、令人疲累。反观台湾,从这几天所听闻的,他感受到台湾正在注入哲学的新生命,好像哲学又重新被发明了一样令人振奋。
说真的,哲学普及在台湾真的可行吗?
虽然几位与谈人都肯定哲学普及在社会上的价值,也都实际去操作了,但哲学普及有这麼容易吗?
讲座最后有三位与会者都对此提出疑问。哲学新媒体的记者问到,在缺乏稳定资金的投入、学院哲学家与社会保持距离的现实挑战下,学院哲学与哲学普及之间如何能达到上述的正向循环?
Palin 也质疑,所谓的哲学普及难道只是将哲学行话翻译成一般人可以懂的就好吗?哲学家是否有可能做
到实际去倾听一般大眾的渴望然后做出回答呢?
另一位提问者则问说,以非营利组织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推广是无效率的,但若以商业力量来推动哲普可以吗?譬如目前台湾就有哲学新媒体、朱家安、人生学校 (The School of Life Taipei) 等组织和个人在做哲学推广。这又会对学院和一般民眾造成什麼影响呢?
真理与价格的关係
Legros 认為这些问题很大部份是「经济的哲学」的问题。他以苏格拉底对辩士学派 (link is external)的批评為例,过去我们认為不涉及金钱的传授才是真理的给予,但到了现代,真理与价格的关係已经改变了。哲学传播者作為拥有著作权利的作者,能获得合理报酬是重要的,譬如佛洛伊德的付费诊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再以《哲学月刊》為例,他说虽然此杂誌是由一位喜爱哲学的银行家所资助创立,但并非慈善事业,至少是以损益两平為营运目标,若有盈餘,那麼对哲学推广来说会更有利。台湾的《哲学月刊》如何可能?他认為需要透过持续在社会中创造与实践哲学的需求、保持这样的活力,未来营利事业单位参与哲学推广不是梦。
吴丰维回应说,哲学推广与学院哲学教育的目标不大相同,把学院语言平民化只是基础的门槛,他认為哲学普及更重要的目标是刺激年轻人思考、享受思考的乐趣,让一般人有机会用哲学的视角和理论来了解切身的议题。他也认為由於台湾目前对哲学仍有许多误解,因此现阶段的哲学普及工作比较像是奠定基础和培养需求的阶段,未来有望能创造出哲学市场。当市场需求出现之后,他认為就能营造出让社会与学院之间建立出良性的常态连结,让哲普工作者也能边精进哲学专业、边做哲学推广。
叶浩也同意其他与谈者的看法,他认為哲学普及是在培养喜爱哲学的人,而非培养专业哲学家。不过由於哲学本身是一种反思,所以当一般人有反省的意识时,就成為沟通与相互学习的对象,因此他认為这些人与学者之间并无明确界定。至於商业化的哲普,他个人一开始是抗拒的,但為了避免一般人以為知识免费,他开始到人生学校授课。这个经验也让他发现付费的哲学课可以让他接触到以往碰不到的大眾,同时也帮助他更认真準备课程来符合学员的需求。这些经验颠覆了他之前对有价哲学的想法。
哲学的成熟市场来了吗?
「哲学应该普及化吗?」,几位与谈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不管从法国的哲学教育、《哲学月刊》的成功、还是当前正经歷哲学復兴的台湾来说,哲学普及的意义很大一部份在於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也就是哲学对社会的价值在於「培养合格公民」;然而,要发挥哲学在这方面的功用,却需要专业哲学工作者的积极介入才有可能,也就是哲学普及须建立在学院哲学与社会的良好生态圈上。
吊诡的是,学院哲学的良好发展必须获得一般大眾的支持才可能运行。问题是,对哲学还有许多刻版印象、甚至误解的台湾民眾,以及相关决策者是否有看到哲学的价值?他们是否了解专业哲学工作者可以提供协助?
哈佛哲学教授桑德尔每每来台演讲,总是盛况空前、一票难求。但一些教育制度的主事者却因為认為哲学没有对应的职业类别,而关闭哲学系6。这突显了一般民眾或许偏好仰望哲学大师,却不见得喜欢或有意深入了解哲学。在目前学院哲学无法获得够多的社会支持和肯定的情况下,台湾从上到下似乎都难以建立良好的哲学生态环境。
突破恶性循环的一个可能方式或许是商业化的哲学普及。法国实施了几百年的高中哲学教育后出现了自给自足的《哲学月刊》等诸多哲学媒体;英国靠著艾伦.狄波顿的才子魅力扶植了人生学校。台湾是否能追随国外的成功脚步,透过持续且稳定的营运方式,完成哲学普及的理想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